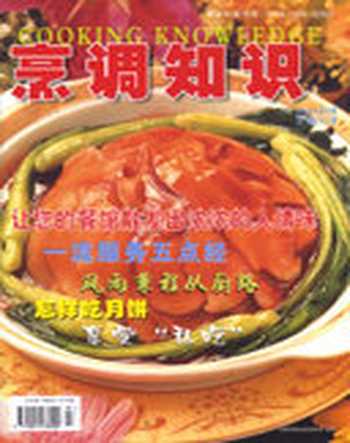茶事多多有东坡
范 凡
苏东坡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书画家和政治家。原名苏轼,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宋代“三苏”,有“苏氏文章擅天下”美誉。苏轼为何叫东坡,这与他宦海沉浮有关,所以茶事也正是这种经历的折射反映。宋神宗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指控讽刺新法而下狱,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风)团练副使,此时,好友马正卿送他几十亩营地,苏轼把这块营地称作东坡,称自己为东坡居士,苏东坡名字由此而得。
东坡茶事,从他的生平中可以窥出诸多轶闻趣事;从他的著述中可以读到大量的茶文、茶诗、茶词、茶联、茶话。这些茶事并不完全是专为消闲享受,而融入了他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升华有他的思想境界与政治抱负,尤其是忧国忧民、疾腐恨贪的鲜明态度。
苏东坡是典型的茶的崇拜者,他终身喜欢饮茶。在某种意义上说,茶伴东坡一生,此话并不为过。
四川眉山是东坡故里,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从小就受到茶的滋养与熏陶。眉山所处的蜀中,是我国茶的发源地,植茶、饮茶的历史均发端于此。产于这里及周边的名茶就有峨蕊茶、蒙顶茶,就近的双江镇在汉代,就是蜀中的茶叶集散地。在茶叶世界中长大成人的苏东坡,不能不对茶有着特殊的情结。而后步入宦海后,所任地方知州以下官职多在产茶之地,又多产名茶。如曾任职多年的杭州,有龙井等;安徽颖州时,安徽名茶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本溪绿茶、松萝茶、祁门红茶、涌溪火青、敬亭绿雪等等都有接触;在江苏,曾任扬州知州,而碧螺春与之有染;就是福建武夷山岩茶、江西庐山云雾茶、湖南君山银针茶等等,都同他有着解不开的瓜葛。
东坡一生亲农亲民,常常深入到茶区调查,亲历茶农茶事,并仔细观察、体验,从采茶、制茶、品茶到斗茶,都有独到的研究。有首词中集中了他的这一成果:“已过几番雨,前夜一声雷,枪旗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结就紫云堆。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尖埃。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 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你看,这是不是可以与茶圣陆羽的《茶经》相媲美了。寥寥不足百字,可抵万字经书,它本身就是一篇精彩的茶经。采茶时节、采茶地点、采茶方法、制茶工艺、品茶技艺、饮茶效果跃然纸上。茶事写实写意,写景写情,有史有典,静动相加,虚实相衬,词中有我,我中有词,展示开来,活脱脱又似一幅民俗风情画卷,可见东坡的力透纸背的写作功力,及对茶事的熟知程度。
嗜茶如命的东坡先生,不可一日无茶,在任密州知州时,一年暮春时候,登密州城超然台,被这里的美好风光所吸引,写下了《望江南·超然合作》词一首。词中记述了他返回时急切饮茶的情景。因那时正是寒食、清时节禁火3天之日,过后的第一天,民俗中可以起火煮食热食了,但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煮茶喝。于是写下了“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的名句,以此“超然”物外,排解忧愁。密州在今山东诸城县。他在徐州知州任上时,写过四首《浣溪沙》组词,记述在村野的见闻与感受。其中“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在他行程中,由于走得太累,加上天热又喝了几杯酒,意倦口渴时,首先想到是喝一碗清茶消暑解渴该有多好啊!于是“敲门试向野人家”,去向老百姓求茶。
他所到过的茶地,见到的茶叶,不少已录于诗词文章中。浙江省余杭、临安交界处的径山所产中国名茶径山茶。取径山龙井之水,泡径山之茶,可谓锦上添花,非同凡响。苏东坡慕名朝游径山茶地,品龙井茶水,有感而发写下了《游径山寺》一首:“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途中勒破千里足,金鞍玉镫相回旋。人言山佳水亦佳,下有万古蛟龙渊。道人天眼识王气,结茅宴座荒山巅。”元丰七年,东坡由扬州赴泗州(江苏盱眙东北)舟行经邵伯镇时到梵行寺赏茶,写有《邵伯梵行寺山茶》诗:“山茶相对阿谁栽,细雨无人我独来。说似与君君不会,烂红如火雪中开。”赞美山茶之壮美、品质之高雅。
所有品茶大家都很讲究用水。好茶需好水既莫例外。东坡是深得此道的。但也有教训之例,不是处于无知,而是出于疏忽,但却成为文坛一段佳话。
因在丞相府续诗得罪王安石被贬官黄州,临行时,王安石托办一事,即将瞿塘中峡水带来一瓶作煎药用。因东坡不满王的报复,将此事忘之脑后。后认识到自己错了,想找机会进京赔罪又忆起此事。马太守马正卿出主意,在冬至节派东坡进京贺表赔罪,顺便带瞿塘中峡水。于是他便告假借送病中夫人回四川眉山县,返回时取水敬献。回程乘船顺流而下时水势浩大一泻千里,加上船中文思兴起,触景构思《三峡赋》不觉船已到下峡。情急中请教岸上村夫,告之他三峡相连,水皆一样。于是用瓷瓶灌了一瓶下峡水带给了王安石。王用瓶中水煮开泡了阳羡茶叶,许久才有茶色。王安石问东坡是否中峡之水,答曰:是。王说:“你骗老夫,这是下峡水。”东坡如实相告。王安石解释说,《水经注》里有说明:上峡水性急,下峡水性缓,只有中峡不急不缓。用这水煮阳羡茶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不浓不淡,正好。我看到茶色老半天才出来,所以知道不是瞿塘中峡水,而是下峡水。东坡听后连连谢罪。此事表明茶之用水的差异,影响茶饮之质量。元符三年,东坡在儋州细致地描写了用流动的江水煮茶所产生的奇效。此诗名曰:《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诗中的雪乳,形容浓茶。脚即茶脚。上半首写东坡亲自到钓石上汲取深处的江水,用旺水烧开江中活水的情景;下半首却为煮茶饮茶时的情形:煎处已翻雪乳脚,泻时忽作松风声,深更畅饮美茶,其乐无穷。
斗茶之风起于唐而兴于宋。斗茶是品评比赛各自茶之好坏,“胜若登山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苏东坡从另一个角度看斗茶。绍圣二年,在惠州写下《荔枝叹》。他由惠州的名产荔枝,联想到汉唐两代进贡荔枝的弊害。借晋国公丁谓,梅建漕使蔡襄以粟粒茶争新买宠的典故,写道:“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东坡对当时以茶附权贵,看人上茶的势利之茶风,疾恶如仇,讽讥有加。就连普渡众生、慈悲为怀的僧人和以一片净土,超凡脱俗的寺院也不例外,他们以来客的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上上等茶、好茶与次茶。一则流传甚广的东坡茶联故事,正是鞭笞这种不良风气的例证。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大学士苏东坡微服出游来到一个山寺。寺中主事的老道,见来者衣着简朴,便冷冷地说了句:“坐。”并对道童说:“茶。”还不待东坡坐定,两人对过几句话,老道见来人谈吐举止不凡,就请东坡进入大殿便客气地说:“请坐!”又招呼道童:“敬茶!”当老道请教客人姓名时,东坡道:“杭州通判,苏轼是也。”道士一听,马上满脸堆笑,慌忙起身把东坡让进雅静的客厅,恭敬地说:“请上坐。”又高声呼喊道童:“敬香茶。”临别时,老道请东坡题词留迹,东坡挥笔书成一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道士看后尴尬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