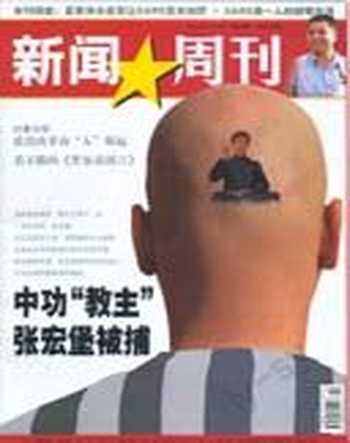民刊的2003
粲 然
在2003年,诗歌民刊开始有了刊号,开始讨论赚钱;另一方面,网络在抢夺民刊的另一部分功能。这是要宣告民刊的终结吗?
2003年的5月,诗歌民刊《下半身》主编沈浩波、主将尹丽川接到了荷兰Het Trage Vuur杂志的邀请信,希望他们前去举办诗歌朗诵等系列活动。实际上,在今年初,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柯雷先生关于“下半身”诗歌流派研究所撰写的论文公开发表,已经引起了荷、英、美等国汉学研究者的广泛兴趣。所以,才有了这5月的邀请。
“下半身”作为近期反响最大的中国诗歌流派,之所以能迅速广为人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刊物《下半身》在海内外的宣传得力。这份装帧精美、题目极具噱头的刊物,实际上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不下万种的各类诗歌民刊中的一份子。
诗歌界的“接头暗号”
1983年一个夏天的晚上,在福建东部一个小山村里,14岁的张海峰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到了一本印满诗歌、装订得歪歪扭扭、上面还带有各种来路不明指印的小册子,这本的舒婷的《双桅船》给他带来巨大的震撼。“主要是因为里面的诗太好了;其次是因为拿到了地下出版物,觉得很神秘”,即使是上厕所、睡觉,张海峰都要把它卷好,随身带着。后来,他买了个本子,用工整的小楷把舒婷的诗都誊写下来,又把那本小册子转送给其他同学。张海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之所以把它送出去,是觉得这样的刊物都是“长腿的”,它能跑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就应该继续跑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也许是受那本小册子的影响,张海峰高中时就开始写诗,一直到了今天。后来他的诗歌,也多次出现在各路民刊上。
让我们看看以下这几组数据:张海峰,从事诗歌写作时间将近20年,写作诗歌200余首,在正式期刊上发表诗歌18首;符马活,从事诗歌写作时间十余年,写作诗歌2000余首,在正式期刊上发表诗歌20余首;曾宏,从事诗歌写作20余年,写作诗歌上千首,在正式期刊上发表诗歌30首;程剑平,从事诗歌写作近20年,写作诗歌900余首,发表诗歌近百首……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正规刊物并没有给诗人展示和交流提供多少空间。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经典的诗歌和重要的诗人,都率先在民刊亮相。这些此起彼伏如接力棒般延续着的民刊,无私地提供给一切诗歌爱好者以“现场”。诗人们说,要是你在上世纪末没有读过民刊,你就根本没有掌握诗歌界的“接头暗号”。
时间翻过近20年。2000年5月17日,诗人沈浩波、李红旗、朵渔专门在北京小西天的小旅馆开了个简陋的小房间,三人绞尽脑汁,终于为他们刊物定名为《下半身》。于是,又一本民刊诞生了。
比起它的前辈们,《下半身》可以说相当幸运。作为自费编印的民刊,它出现在21世纪初,这时的制作者们经济条件已相当宽松、文化出版业遍地开花。《下半身》得以采用双胶纸做内页,封面则为铜版纸附光膜,看上去大方精美。沈浩波语调轻松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人出500,凑齐5000元,就把这事给结了。”
相对于这个诗刊新贵的大手笔,当年的诗歌民刊创刊史显得既寒碜又悲壮:1985年南京的《他们》第一期印刷完成,韩东和几个朋友好容易凑齐1000块钱,在当时已经是极大的一笔投入;1990年,为了《诗参考》的面世,中岛险些砸锅卖铁;1994年,以百晓生为首的几个北大学生为创办《偏移》,每个人从为数不多的生活费里“抠”出50元钱;1998年,广东符马活创办《诗文本》,第一期全部成本为1200元……
诗歌也可卖好价?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刊几乎都是以自留、交换、分发和寄赠的形式进行传播。在那时制作民刊绝对是“公益事业”。1992年,诗歌民刊《葵》第二期封底附《敬告同仁》:“由于从第二期起《葵》送交打字社打印,故请诸君自下期始,随稿附寄50元印刷邮寄费,此后不另行通知。”后来主编徐江在回忆此事时感慨地写道:“理想之高远,存活之困窘,两者的天地差异,从来都是诗歌民刊所要直接面对的。”
也是在1992年,福建诗人张海峰收到《葵》的通知,告知他的诗稿被采用,迫于《葵》再度面临经济压力,希望他能出资帮助云云。由于当时生活拮据,张海峰并没有向自己的同窗师兄兼好友徐江汇去钱款。
然而从2000年底到2001年初,以《下半身》亮相诗坛为标志,弥散在民刊之间捉襟见肘的经济裂缝似乎有了改善的预兆。首先,《下半身》流散出去的几百本刊物被广州、云南等地小书贩所获,在小书摊上一夜之间抢购一空;其次,中岛得到消息,海外的汉学家向当地华人购买《诗参考》,“一般是60欧元,在香港则卖300~400元。”他形容自己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但语气之间却掩饰不住得意。
于是,2001年底,网络上出现了“我要出民刊!谁知道怎么制作赚钱的诗歌民刊?”“谁做民刊谁发财”之流的言论,网上私下售卖民刊的站点还打出“凸现底层有志者坚定追求与苦难历程”、“与民间文学力量和思想激情同行”之类广告词。一向标榜“绝非赢利”、体现“诗歌纯洁性”的民刊们在无孔不入的商业浪潮冲洗下,一时间处境尴尬。
此外,由于图书管理的日渐宽松和出版业的发展,不少民刊得以以合法书号公开出版,它们不隐讳自己对市场的追求;一部分民刊编印者们认为至少收支持平才能维持刊物的基本运作,赢利也是刊物的受欢迎程度的一种具体体现。很多固执捍卫民刊“纯净性”和“神圣性”的诗人颓丧地发现,与以往民刊“民间化”、“自由化”,标榜“跨越一切秩序”的特质相悖,民刊本身制作越来越精美,越来越像一本正规的书,好多人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印刷刊物。对比起当年诗人为反对诗坛陈腐霸权话语而创办的民间刊物——那些艺术上不妥协的产物——民刊的制作很可能演变为艺术投机行为。
刊物的价格是否体现诗歌的价值?民刊要“高标独隐”还是“商业运作”?对于诗人们,这是个始终说不清、想不明的问题。
蜕变亦或终结?
然而,在2003年,诗歌民刊自身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是否定价以及如何定价。网络时代的完全到来才是要宣告它的终结。
1999年,张海峰购买电脑并上了网。在同龄诗人当中,张海峰自信上网并不算晚,但在2000年5月,在一次玩笑般使用google搜索自己名字时,他惊讶地发现,已经好几个站点收录了他的诗歌,但他竟然毫不知情。
1999年底,中国国内第一个专业诗歌站点“灵石岛”成立;2000年元旦,国内迄今为止最大建设最全面的诗歌站点“诗生活”成立。在此后的两年里,诗歌站点风起云涌席卷而来。诗人们突然意识到,以前孜孜以求的交流展示平台现在仅仅需要复制和粘贴便能瞬间完成。他们开始在论坛上发帖争吵、用e-mail交流意见、建设自己的个人主页……
这一切,当然也席卷着民刊的制作者们,他们很清楚地感觉到,作为发表渠道和交流平台,诗歌的载体在悄然变化。《下半身》主编沈浩波就认为“很快网络出现了,对民刊的依托没那么强烈了”,制作民刊成了“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很自由”的事情。《葵》和许多民刊一样开始在网上接收与阅读稿件,主编徐江还兼负责“个”论坛“诗歌现场”网刊选辑工作。
虽然对于诗歌民刊是否最终消亡的意见不一,但诗人们众口一词地认为2003年绝对不是“民刊终结年”。正在转而投入长篇小说创作的韩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诗歌评论界一向对网络诗歌站点缺乏热心;而媒体对诗坛的关注则更为可疑,他们仅仅关心“爱情与死亡”,多年来拿着海子的自杀和顾城的三角恋津津乐道——这种外部社会对诗歌界“不自觉的合谋”是民刊作为诗歌界的独立“喉舌”必须坚持维系下去的主要原因。
到今天,中岛依然对现在一些民刊制作者千方百计为自己的刊物“搞书号”、制作“网上电子版”的行为颇不以为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刊有了刊号是“错误、不合规则的”,网络虽然“有优势,却类似游戏”。他说,无论时代如何前进,他都会把民刊好好办下去,刊物的终结就是他的终结,他的终结才会是刊物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