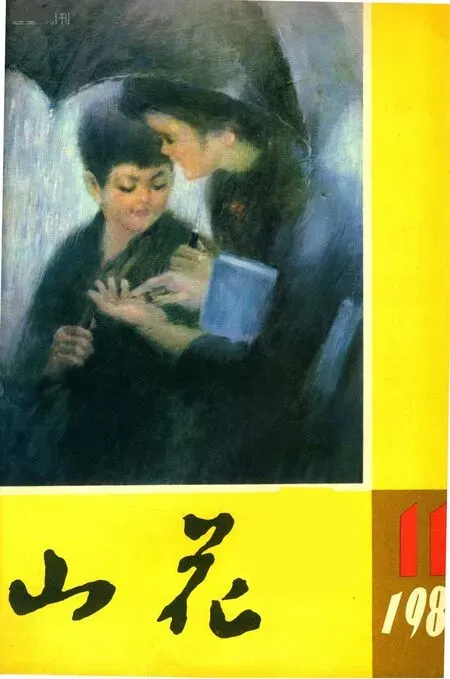户口
聂鑫森
申由走出汽锤声渐渐稀落的锻造车间时,正是上午十点。1968年的这个初秋的日子,阳光薄如金箔,而空气凉润如水。那些红红绿绿的标语、横幅密密麻麻地贴在厂区大道两边。往常,他看到这些红红绿绿的东西,心上总会覆上一层阴悒和委屈,立刻联想到他两百里之外的乡下老家,还有那个“富农”的家庭成份,以至他在十年前招工到红旗机械厂时,猛一下就分配到了锻造车间,做一个乡下人称之为“铁匠”的人物,天天与汽锤与烟火相厮守,因这个成份这个工种又使他一直没有找到女朋友。尽管他的父母在他参加工作后,都相继病故。而和他同时进厂的方万,也是高中毕业,可出身好,一进厂就分到人事保卫科,坐办公室,喝茶读报纸,然后很快就有了女朋友。方万的女朋友是厂财务室的会计,叫田兰,比他大了整四岁,人瘦高,脸又窄长,样子没人敢恭维。但在这阳盛阴衰的重工业单位,田兰简直就是白雪公主,城市户口再加上一份坐办公室的工资,气焰上就比方万高出一长截,动不动就说:“我们可以分开过,你这样的角色我闭着眼睛随便抓!”
申由散漫而潇洒地走向厂办公大楼,这一刻他的心情好极了。两边的横幅标语,红红绿绿如同无数花朵和叶子,有如漫山遍野光景如醉。按规定,现在还不是上午下班的时候,那要到准十二点。但现在确实没有多少人在上班,都“抓革命”去了,开批判会,写大字报,头头们一个个被批得灰头土脸,谁也不敢以生产来压制革命,只好听之任之。但申由有一个原则,他这个出身绝对不能去参加什么“大批判小组”和“揭批战斗队”,他照常上班,老老实实干点儿活,然后早早下班,赚点儿时间而已。他心目中最大的任务,就是已经三十岁了,得赶快找一个女朋友,得赶快成一个家。人家方万已经结婚四年了,都有了两个孩子。他看到田兰时,觉得她更瘦了,像一根风中的芦苇,脸更窄更长,如一把扁长的菜刀。可田兰的脾气却是见长,仿佛还是一个身份赫赫的红花闺女。方万告诉申由,夜里他有时想和田兰亲热,田兰“嗯呀嗯”地半天也不同意,非得悄声地讲一箩筐好话,才施舍似地松开抓住裤头的双手。方万咬牙切齿地说:“她把这事当作粮食和肉食的供应了,严格定量!”
能讲这种隐私的人,关系当然非同一般。申由和方万确实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拿现在的话讲,是铁哥们。他们是进厂后才认识的,严格地说是到了厂篮球队之后。
红旗机械厂在这个工业城市株洲,并不怎么显眼,地点在城郊,产品是拖拉机配件,人数不过近两千,但却有一支男子篮球队闻名遐迩。方万是城里人,个头一米八,脸色白净,身材颀长,曾是市中学篮球代表队的中锋。申由个头一米七八,粗壮如铁塔,脸膛黝黑,虎背熊腰,是县中学代表队的主力后卫。他们是被这个厂人事保卫科的负责人明查暗访后,再招进工厂的,并立即选入了球队。对于申由来说,不亚于天上掉下了一个馅饼,喜不自禁,什么条件也没说就来了。方万却知道自己的价值,有几个万人企业都表示了对他的欢迎,他有资格“待价而沽”,他便提出了不下车间当工人的要求,红旗机械厂豪不犹豫地应允了他。这个厂的球队原本就不错,再加上这两个主力,如虎添翼,风头更健。在他们加盟球队的1958年,全市正好举行职工男子篮球大赛,奇迹出现了,从过去的排行老七,一下子跃居第二,只是输给了一家铁道部所管的万人大厂。
在这场争夺冠军赛的大战中,对方见方万连连得分,恨得牙根痒痒的。当方万三步切入投篮时,对方的“5号”,使出一个绊子,让方万凌空跌下,伤了脚,不得不一拐一拐下了场。这些都看在申由眼里,他在拿到球后,突然大步运球上篮,直朝对方的“5号”撞去。“5号”个子单瘦,居然迎上来拦截。申由是早有准备并憋足了一身力气的,快接触到“5号”时,拼命向前一蹿,跳起投篮,在一刹那间,“5号”被撞出几米开外,仰面倒下后,身体迅速朝球架滑去,头“砰”地撞在球架上,立刻见了血。裁判哨子一响,判“5号”阻挡犯规!坐在球场边的方万惊大了一双眼睛,他知道申由在为他“报仇”,心里也就暖暖的。假如对方个子高大,而且有准备,申由也有负伤的可能。不但方万觉得解气,红旗机械厂的职工也感到心里痛快,这些大厂总有一种篾视小厂的气概,杀一杀他们的威风也好。这场球赛红旗机械厂仅以三分之差败北,但全厂上下比得了冠军还振奋人心!
申由和方万从此成了好朋友。
方万和田兰为申由介绍过好几个对象,有环卫处的工人,有商场的营业员,但都没成。她们看不中申由的理由有三:一是成份,二是工种,三是过于粗黑。也有一个例外,姑娘的脸上有几颗麻子,虽说答应了,但人挺牛气,申由却反过来没同意。他在那一刻想起了田兰,“十麻九怪”,将来日子更没法过了。于是,申由暗下决心,我不找城市姑娘,找一个乡下姑娘又如何?年轻一点,漂亮一点,老实一点,也不致太亏了自己。
申由走进了办公大楼,顺着木楼梯,重重地走到了三楼方万的办公室里。
方万正在看着一张套红的《人民日报》,听见脚步声,报纸依旧高高地遮住了脸,从报纸后传出不耐烦的声音:“有什么事?”
申由哈哈一笑:“我的副科长,打什么官腔?难道连我也要喊‘报告了?”
方万连忙放下报纸,说:“进来了连哼都不哼一声!快坐,快坐。哎呀呀,也不去洗个澡,一身工装油晃晃的,这样子连头母猪都会吓跑的,活该还是打光棍。”
申由坐下来,说:“石头也有翻身的一天,我申由也该成个家了。”
方万一愣,说:“几时谈的?怎么没听你说过?”
“三天前定下的,是我师傅介绍的,一见面就定下了。”
“这么快!人漂亮吗?”
“说得过去,应该可用上‘漂亮二字。”
“年纪呢?”
“二十二岁。名字也好,叫杜若。”
“好呀,小了这么多,老牛吃嫩草,你什么时候摊上这份艳福了?”方万心里突然有些酸,脸上的肌肉扯了几扯,笑得有些不自然。
方万忙给申由泡了一杯茶,又问:“她在哪个单位工作?”
“地球车间,翻泥巴的干活,是个农村户口。”
方万松了一口气,说:“农村姑娘有什么不好?你也该知足了。”
“那是的。见面时,她家可有条件,第一,她要住到城里来;第二,将来要给她办个城市户口。我想好了,准备在厂子附近租两间农民的房子安顿她,这就算住到城里了。至于第二个条件,你们人事保卫科兼管申报户口的事,往后想请老兄多多帮忙。”
方万拍拍胸脯,说:“只要我做得到,我肯定帮忙,你放心。”
他的心里却说这个事我恐怕帮不了忙。
在那个年代,有了城市户口,就意味着有了粮食、煤炭、食油、布票以及豆腐、南粉等等物资的计划供应,就可以在城里参加工作。而要把一个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工厂里有不少工人的家属都在农村,一年也办不了几个转城的户口。基本条件是有一方伤残了或长期卧床不起,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才有可能享受这种待遇。当然此中也有“特殊”情况,用一连串的假证明做手脚,顺顺当当办成了事的,但那绝对是有“背景”的人。
申由走后,方万再无心看报,他想起申由所讲到的未来的妻子杜若,年轻恐怕不假,漂亮就未必可信,一个打铁的,整天看见的是黑糊糊的工件,那眼光好不到哪里去,说不定还是个残疾人,要不他怎么特意提出办理城市户口问题呢?方万用手指轻叩桌子,自言自语:“申由呀,你又何必吹这个牛呢?能找个母的,就该满足了,没人笑话你”!
当年方万结婚时,申由领着一帮球队的哥们,为他打扫、粉刷、布置新房、为他的厨房打灶、砌水泥缸,忙了十几个夜晚。但这次申由要结婚了,却没有惊动球队的人,是锻造车间的一伙人去帮着收拾借租的那两间旧房子的。这个“家”离工厂不远,环境蛮不错,一排竹篱围着几间杉皮瓦的房子,房子后面有几块菜土,竹篱门前面是一个不小的池塘,杨柳依依,碧波粼粼,时不时地有鱼跃水的声音传来。申由之所以没惊动球队里的哥们,其实是怕惊动方万。他想:这些小事何必让方万费力气呢,将来办户口还要麻烦人家哩。但到了申由正式结婚的那一天,方万却主动找到申由,要跟着他这个新郎官一起去“接亲”,申由很感动地答应了。
申由的岳家在离株洲市四十里外的株洲县的乡下,厂里特别照顾拨出了一辆货车,去接新娘和嫁妆。申由坐在驾驶室里,方万和另外三个男女青年站在货车车厢里。待到接回新娘后,就在那竹篱小院里摆上几桌酒席,厨师和招待员都是一帮锻工朋友,方万之所以要参加这次“接亲”活动,心理很微妙,他想尽早一睹那个杜若的风采!
汽车跑了一个多小时,就到杜若的家门口了。申由和大家都下了车,先是放起了爆竹,爆竹声中方万领头准备进门,门却突然关了,任他怎样喊也不开门。申由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红纸包封,每个包封里包着一两元钱,从门缝里塞进去,接着门就开了。方万心里说:乡下人,俗!
申由立刻去拜见厅堂里的岳父岳母,递过一只很大的包封,里面放着折合嫁妆的钱,方万连忙和大家抬进一个大食盒,里面放着有两桌酒席份量的鱼、肉、鸡、鸭、粉丝、香干、海带等原料。就在这时候,方万看见从里面房间走出一个年轻的女子来,个子高高挑挑,不胖也不瘦,白衬衣蓝长裤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身上的线条;脸是杏子脸,白里透着红,眼亮、鼻高、嘴小,竟是绝色!方万惊得张开的嘴再也合不上去,想不到杜若不但不是残疾人,而且是个尤物,这个黑包公似的申由,居然有这等艳福。假若田兰站在杜若身边,那只会使人想起白天鹅和癞蛤蟆。
杜若走到申由跟前,大大方方地说:“从今天起,我就是你屋里的人了,我的城市户口你要尽快办,要不我嫁给你做什么?”
申由说:“我的好朋友方万会帮我想办法的,你们放心。”
方万这才回过神来,是呀,田兰是城市户口,是拿工资的人,杜若怎么能比!
汽车往回开的时候,杜若坐在驾驶室里,申由和方万他们几个,分别站靠在车厢里的两边。杜若的嫁妆很可怜的摆在车厢的中央,两个红漆木箱、两床被子、一个脚盆、一个马桶。方万看着这些土里土气的东西,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申由说:“这对于她家来说,已经不容易了。方万,杜若的户口我就指望你了。”
“我会尽力的——当然困难重重。讨了这样漂亮的老婆,有不有户口无所谓。”
“不!她怎么就不能有一个城市户口呢?”
方万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
临近中午的时候,汽车开回了申由的家。
院子里已经摆开几张借来的八仙桌,坐的多半是锻造车间和球队的人。
当爆竹轰响起来后,新郎新娘入了席,一大碗一大碗很粗糙的菜,飞快地摆到各个桌子上,廉价的谷酒倒满了一只只小瓷碗。
新郎新娘开始一桌一桌地敬酒,粗鲁的笑骂声此起彼伏。当他们走到方万这一桌时,先和所有的人同干了一碗,然后杜若又单独向方万敬酒。
“方大哥,我知道你是申由的好朋友,我单敬你一杯,以后请你多多关照。”
方万端起酒碗,痴痴地望着杜若。喝过酒的杜若,脸色艳若桃花,那双眼睛媚媚的,勾人。“谢谢你称我为大哥,这样漂亮的弟媳,我能不帮忙不关照吗?喝了!”
申由的嘴角扯了几扯,但没有作声。
方万直喝得踉踉跄跄,才由人扶了回去。
晚上方万没有来参加申由简单的结婚仪式,没有来闹洞房,他身上酒力未消,软软地躺在床上。
田兰说:“人家结婚,你哪里这么大的兴头,好像是你当新郎官。一个乡下姑娘,值得你这么去捧场。”
“我们是好朋友。”
“朋友妻,不能欺,你莫哪里喝醉了酒,钻到人家的被窝里去了。”
“胡说。”
话一出口,方万的心一跳,浑身便火烧火燎的,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
申由非常热情地邀请方万和田兰第二天到他家去玩,钓钓鱼,吃中饭。因为明天是星期天,秋高气爽的。
田兰说:“谢谢你和杜若,明天——我要回爹妈家去,帮他们洗洗被子,让方万去吧,他爱钓鱼,老吹嘘自己是钓鱼高手,只是别空手而归。”
方万说:“我的钓竿不行……”
申由说:“我早给你备好了,还有钓饵,你只管来就是。”
第二天方万去了申由家,不过是临近中午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去的。他当然想早点去,但田兰先让他陪着去了她娘家,让他帮着拆洗被子,然后才挥了挥手:“去吧。”
方万一走进这个竹篱小院,就发现杜若是个既勤快又爱美的人,屋后几块荒了的菜土都翻挖了,栽上了翠绿的秋白菜;竹篱边栽上了不知从哪里挖来的牵牛花,叶蔓满满的攀在竹篱上,开着红色、蓝色、白色的花朵,像一只只小喇叭,向天吹着热烈的乐曲。
申由问:“嫂夫人到这时候才放行?”
“有个老工人来家里,催问他家属的户口批下来了没有,田兰哪敢管我的事。”
“我们先喝酒吃饭,再去钓鱼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