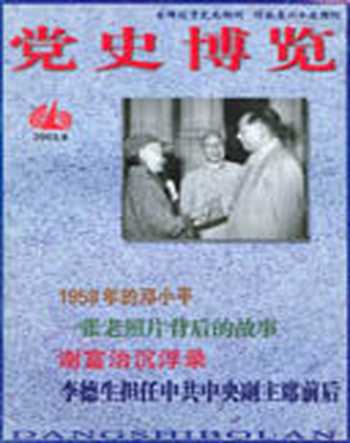博览之窗
刘伯承情系战友
1949年12月31日,二野司令部进驻重庆后不久,为了探询朱德等几位老同志的家庭情况,刘伯承亲笔给二野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章安翔写了一纸短笺,要他处理此事:
凡关于各区来的电报,必须重视,要回电,不要拖沓给以不理的态度。前次我托你查问给粟裕为其母到南京之复电即此意。现陈毅、尚昆均有来电,必须回。而荣臻家庭情况,也须通知(要程子健),望你专为我们作检查之事。即此,勿忘!再总司令家在仪陇,总司令也托我探询,这是要川北区党委办的。
刘伯承
便笺中提到的“给粟裕为其母到南京之复电”事,其原委是:二野五兵团进军贵州靠南边的一路部队经过粟裕的家乡湖南会同时,派人看望了他的母亲,老人家想去南京看看儿子,五兵团来电要求转告粟裕。由于当时部队正在向西南进军作战,忙不过来,处理慢了,刘伯承为此曾严肃批评过有关人员,这次重提是再次告诫之意。
章安翔接到刘伯承的手书后,立即按照指示,派人迅速将了解到的上述同志的家庭状况报告给二野司令部,并要求派人前去看望。任务完成后,章安翔向刘伯承作了汇报。刘伯承听后很高兴,特意将章安翔留下作了一番谈话,并讲了自己与信中提到的几位老战友的情谊:
“这些同志,半辈子奔走革命,离乡背井,出生入死。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多少人牺牲了,使我们想起来很难过。我们这些幸存者现在到了四川,到了西南,要为牺牲的烈士树碑立传,永远纪念。上述几位同志都远在中央、华北、华东,工作都很忙,我们来到了他们的家门口,理应把他们的家庭状况及早地告诉他们,并应帮助解决困难,何况他们都向我们打过招呼呢!好,现在电报都已发出去了,我的心也踏实了。”
(摘编自《世纪》2003.1余春水文)
毛泽东严格要求家人读史
1947年9月,毛泽东给从苏联学习回国,正在农村接受锻炼的长子毛岸英写信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朝以前的笔记不必多看)。”他想以此使自己的孩子加深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的了解。
毛岸英的爱人刘思齐在读书时,有段时间历史学得不好,对朝代、年代总是记不清,常常发生混淆,把这个年代的事说成那个年代的。毛泽东开玩笑地批评她说:“你一下子就把历史抹掉几百年。”他耐心地教导刘思齐要重视学习历史,并亲自为她开列了学习书目,指点她从《资治通鉴》、《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开始学起。
对于和长子一样在苏联读过书的次子毛岸青,毛泽东也常常叮嘱他多读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多了解一下中国国情。
有一次,毛岸青的爱人邵华高兴地告诉毛泽东,她的中国通史这门课的考试成绩很好。于是,毛泽东便让她讲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邵华就按课本上的内容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对这些回答并不满意,他说:“这是死记硬背,只能算知道点历史的皮毛;学历史得融会贯通,得很好地理解才行;要多读史料,多想想,能把‘为什么说清楚,才算学懂了。”
(摘编自《纵横》2003.3于保政文)
《人民日报》初登雷锋事迹所遇到的压力
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放开版面,同时在一版、二版编发了关于雷锋的文章和雷锋日记摘抄。一时间,雷锋成了人们的一个重要话题。《人民日报》的长篇报道,进一步推动了学雷锋活动的开展。
其实,以两个版面刊登雷锋事迹,在当时面临着很大的争论和压力。据《人民日报》负责此事宣传的连云山于1994年发表的文章披露:按照惯例,凡社论和重大宣传,都须送给有关单位审查。但这个稿子连云山没有送审。他当时认为,雷锋事迹的稿子特殊,一般单位审不了,因为他们不了解或不甚了解情况。总政治部一位副部长对连云山说,你这个报道是错误的,雷锋的死不能和黄继光的死相比。黄继光的死不过两千字的通讯,而对于一个被砸死的战士,我们却拿出两个版面宣传,如果再发生战争,再出现“黄继光”,你拿出8个版面来宣传吗?你本来是把关的,不仅不把关,还支持,你这是失职行为。
连云山回答说:“黄继光的事迹发生在战争年代,现在全国没有战争,上哪儿去堵敌人的枪眼?我认为在和平时期,雷锋的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献身精神,爱护人民的精神,应该是现时期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的发扬,是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人物中间的一种。宣传他不是错误,不是失职,你这个批评我想不通,我没有做错。”
没过多久,在总政小会议室召开了由首都各新闻单位参加的会议。当时,总政向人民日报社提出要调动连云山的工作并给他处分的建议。《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张潮当场表示,我们签了字,当然是我们的责任,你们没有权力给连云山处分。《人民日报》副总编李庄对连云山说,你不要有顾虑,好好工作,一切由我们负责。由于人民日报社对连云山的坚决保护,总政提出的对连云山的撤职和处分都没有实行。
(摘编自《中华儿女》2003.3常家树文)
陈海松: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级干部
陈海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一个贫农家庭。1930年,16岁的他背着家人,参加了由徐向前领导的红军。
1931年春,陈海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他作战勇敢,表现突出,很快被提升为机枪连指导员,当时他只有18岁。由于他工作能力强,深受官兵的爱戴,不久又被提升为营政委、团政委。1933年6月底,陈海松因出色的军事才能升任红二十五师师政委,师长为许世友。
1934年,在与川军的战斗中,陈海松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提升为红九军政委。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毛泽东见到陈海松,得知他只有21岁时,惊讶地说:“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也年轻,但还没有年轻到这种程度的。”
陈海松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却非常平易近人,经常到连队跟战士们聊天、拉家常。他个子不高,胖墩墩的,战士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小胖政委”。
1936年10月,红军开始西征。在大古浪战斗中,红九军被敌军包围,陈海松指挥若定,率部奋力突出重围。1937年3月12日,西路军大部队进入了梨园口。红九军奉命扼守山口,掩护总部和兄弟部队安全转移。在战斗中,陈海松身中8弹,壮烈牺牲。一位年轻有为的军事天才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更多的抱负就这样长眠于河西走廊了。
后来,朱德曾多次对人说:“陈海松是四方面军里最年轻有为的指挥员,可惜牺牲得太早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编自《军事史林》2003.5韩东文)
华蓥山游击队历史曾遭错误对待
长篇小说《红岩》中,华蓥山游击队和“双枪老太婆”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支队伍却曾遭受过误解和不公平的对待。现供职于渝州大学中文系的傅德岷教授历经30余年,写出了《魂荡华蓥》一书,真实地再现了这支队伍的风雨历程。
当年威震川北华蓥山地区的“双枪老太婆”名叫陈联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联诗和丈夫廖玉璧变卖家产,购买枪支,根据中共岳池特支指令,正式组建了华蓥山游击队,廖玉璧担任了队长。后因叛徒出卖,廖玉璧牺牲。当时,中共岳池特支与华蓥山游击队是单线联系,联系人就是廖玉璧。廖遇难后,游击队与党组织的联系便中断了。在军阀的围困下,游击队只得隐伏下来,由原来的公开武装斗争转为地下行动,有时迫于生存,甚至以灰色的方式出现。
1948年,在党的领导下,游击队重新崛起,并配合大西南解放举行了武装暴动。解放初期,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人民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匪反霸”运动。由于当时有排斥地下党、地方游击队的不正之风,加之又有国民党反动宣传留下的“后遗症”,华蓥山游击队被认为“成分复杂”,甚至有人说其是“土匪武装”,因而不少游击队员被打成“土匪”类人物。1960年,陈联诗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文革”开始后,江青诬蔑“华蓥山游击队都是土匪、叛徒,没有一个好人”。
1981年10月,傅德岷重新到华蓥山地区搜集材料,采访当事人。他利用拜访当地党政领导的机会,多次替那些解放后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游击队员申诉。1982年,华蓥山游击队终于获得平反。1991年6月,《魂荡华蓥》作为建党70周年献礼作品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摘编自《文史精华》2003.2陈启兵文)
黄克诚建议恢复八路军政治委员制度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撤到五台山地区进行休整。此时,驻在五台县南茹村的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派总政治部组织部长黄克诚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情况。
经过半个月的调查研究,黄克诚发现,红军虽然刚改编不久,但部队作风却有了很大变化,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这主要是由于红军改编时,受国民党的干涉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显著削弱所致。
黄克诚同聂荣臻等师首长商量时,提出建议:为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应恢复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对军阀主义的斗争。聂荣臻等人一致赞同。黄克诚返回总政治部驻地后,向任弼时作了汇报。任弼时当即指示黄克诚,将他在部队检查、了解到的情况和他的建议,起草一份报告上报中共中央。黄克诚很快写成电报送任弼时审阅。1937年10月19日,这份报告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名义上报中共中央。
报告发出后三天,中共中央便给朱、彭、任发来回电,批准了在全军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下令恢复人民军队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
不久,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报告会上说:“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
(摘编自《军事历史》2002.5阎稚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