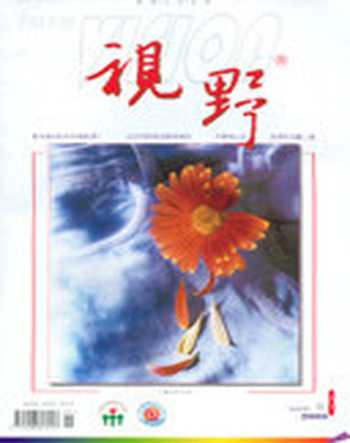后饥锇年代
秋 高
每每忆起当年那段高中生活就忍不住鼻子一阵阵发酸。
我是1993年上的高中。那所中学虽然在一个小县城,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被列为了省级重点。
学生都是下面各个乡镇考上来的尖子生,大多住校。
食堂离宿舍和教室都很远,得斜穿整个校园,出校门,过一条马路,沿着居民区里的一条巷子往里走六七分钟才能到。食堂大厅里有两排大圆桌,也没椅凳,吃饭时都得站着。有一个打扫卫生的老大爷会在每次开饭前扫地时顺便用那把大扫帚扫一下桌子,就算做了清洁,所以桌子脏得很难辨出原来是什么颜色。
饭菜比桌子要干净,只是里面经常能吃出一些有机或无机的杂物,虫子苍蝇还好,权当补充蛋白质了,有时遇上铁丝玻璃片就不免会有些后怕。校体训队的受不了,经常跟窗口里的人打架,还领导过几次“罢饭”,但都因为没有太多人响应,也就不了了之了。
食堂不卖早点,多数人的早点就是前一天打的一个冷馒头加一杯白开水。我也一样。虽然如此,宿舍里的几个弟兄都是第三节课开始才勒紧腰带,我却第二节课还没下课就饿得两眼冒花了(我始终都怀疑他们有小动作,虽然他们一直不承认)。第四节课上到一半时大家的手就都放到了桌洞里的饭盒上,铃声响起时的场景有点像中长跑比赛的发令枪响起,几乎是一路跑着穿过校园、马路,穿过那条小巷,然后在食堂大厅那两扇掉光了漆的木门前挤作一团。隔着玻璃看老大爷打扫卫生收拾桌子,一边不耐烦地敲着饭盒,一边把门上那把大链锁摇得哗哗作响。门终于开了,便又在打菜窗口前挤作一团。虽然窗口里摆着的只是几盆白菜、土豆、茄子,可每次如果动作慢点儿是会打不着的,所以只能这么挤。很多人用的都是我用的那种长方形铝饭盒,很薄,有时从人堆里钻出来时饭盒已经变了形,像一只破皮鞋。在电视里看到的非洲难民领救济粮的情景,比我们当初,他们要显得从容得多。
女生是不敢参与这些“暴力”活动的,一般都从家里带些咸菜,开饭半小时后才到主食窗口打几个馒头,带回宿舍姐妹们一人一个就解决问题了。馒头总是充足供应的。
走入社会之后大小餐馆进过无数,南北菜肴也尝过不少,但至今都认为最香的食品还是那时食堂卖的机制馒头。
为了省钱,那时很多同学都是两人合打一份菜,填饱肚子全靠馒头。和我合伙的兄弟很仗义,我们从来都是让着吃菜,他一顿两个馒头,我一顿最少三个。那种馒头好像太不瓷实,虚得跟面包似的,所以有时候吃四五个也不觉得撑肚子。
每年的运动会是班主任们最头疼的一件事,上体育课跑几圈都会晕倒,谁还有力气为争个暖瓶钢笔之类的奖品拼命。最后只好赶鸭子上架,拽几个眼皮耷拉得不太厉害的上去撑撑场面。为了制造气氛,看台上也不准空着,班长每天都要点名。
记得高二那年的运动会我在看台上读的是路遥的中短篇小说集,读完了《人生》还只是心里有点难受,当读到《在困难的日子里》主人公偷偷跑到学校附近收过的田里捡土豆躲到破窑里烧着吃,为了减少能量消耗趴在课堂上一动不敢动这些情节时,我都忍不住偷偷抹眼泪,我伤心,为那小主人公,也为我和我周围的兄弟姐妹们。
我吃饭一直慢不下来,同时吃一碗拉面,别人加了醋,放点辣油,搅和一下,挑起来吹吹,刚嚼两口说出一声“不错”,我已经在喝汤了。回家吃饭为这经常挨老母亲骂,就是慢不下来。和朋友出去吃饭,谁爱点什么点什么,没有我不吃的,只要没有什么重要人物,从始至终我都筷不离手,最后还不忘打扫战场。这些全都是站着吃那三年落下的后遗症。
父母亲从小就给我们讲他们在60年代那三年吃什么,感叹我们生在了面缸里,可他们不知道我那面缸里的生活也有三年是勒着腰带过来的。那些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当然,也永远不会跟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