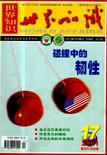袁士槟外交官出身的教授
逆 水

立秋翌日上午,暑气犹存,记者按约赶到了位于西城区的外交学院。与袁教授见面后,我作为他的“电视学生”,便开始了这场非常亲切的交谈。
用双语为国家领导人当翻译
“我一生无大建树,但自觉还丰富多彩。”袁教授一开头就介绍他自己说。“1950年,当抗美援朝运动席卷祖国大地时,正在念高三的我居然瞒着父母,放弃了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志愿,毅然报名参了军。经过第三野战军,最后被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学英语。1953年,曾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团的英语翻译入朝工作了五个多月。1954年,还没来得及做毕业鉴定就被调入外交部。接着,就被借到当时的经贸部,赴当时尚未建交的叙利亚,参加大马士革世博会,在那儿工作了近半年。回部后,连板凳还没坐热,1955年5月又被外交部选派至印度留学。”这是我国首次向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国家派遣留学生。他学的是印地语和印度学(包括历史、政情和文化等课程),成绩出众,获硕士学位。1959年初,他被留在我驻印使馆工作。
袁教授回忆说,在50年代的大半个时期,中印两国关系相当密切,官方和民间的交往频繁,“印地—秦尼帕依帕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在两国几乎家喻户晓。但在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事件和边界纠纷之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1960年,周恩来总理亲赴新德里就边界问题同尼赫鲁总理会谈,中方为争取公平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而做出的努力未得到印方响应。1962年10月,印方在边境不断越过实际控制线、蚕食中方领土并向中国发动进攻,我方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两国友好往来中断。
伴随中印两国关系的恶化,我驻印使馆于1960年逐步进行精简,从原有的100多人减至20来人。当时,28岁的袁士槟通晓英语和印地语,就被留了下来,曾先后为潘自力大使和陈肇源临时代办当翻译兼秘书。1960年周总理访印时,他充当翻译,主要用印地语,也用英语,较圆满地完成了工作任务。1964年,他奉调回国时已在印度整整呆了九年。回国后,他被分配到亚洲司印度处。后来,他还曾多次为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陈毅及主管亚洲事务的韩念龙副部长当翻译。

用英语教授“多边外交——联合国”
70年代初,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及中美关系僵局的打破,我国的外交事业蓬勃发展。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外交部从全国各地调进大批干部,而他们中的多数需经过外语培训才能投入工作,因此外语培训班就在原外交学院院址开办起来。1973年,袁士槟从江西“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开始了他的教学历程。70年代末,他还数次应邀临时前往联合国,为大会或专业会议担当同声传译。后来,他把做同声传译的经验加以总结,形成一门课程,专为英语双学位班上口译课。当时,其他院校英语专业的一些教师闻讯前来听课,他们对这门紧密结合“实战”的课程及讲授的内容,评价甚高。
有位老大使曾向我介绍说,袁士槟的英语和印地语造诣都很高,他有学习语言的天分。对此,他本人如是说:“天分谈不上,主要还是勤奋加机遇吧!我在上海,八、九岁就开始学英语。在南京参加军干校后,又被分到北外。那里有全国最好的英语老师。到了印度,又是通过英语来学习印地语。印、英两语都是官方语言,那儿学习语言的环境很好,应该抓紧时机学好两语。我的近视眼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当然勤奋很重要。开始教学时,我已40岁出头了,自行编写教材,工作起来并不轻松。尤其是在联合国干同声传译,开始很感吃力,但我还是拿了下来,靠的是一股拼劲。”
1980年,外交学院恢复。袁老师面临着两条出路:一条是回外交部亚洲司印度处,因中印关系已有所松动,有工作可干;另一条是留在外交学院继续教学。他说:“当时,我对教学工作已产生了感情,认识到为外交事业培养有用人才是件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再说数年的教学实践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因此就选择了后者。”从此,他的教学生涯便正式开始,并担任了英语教研室主任。1984年,他陪同刘春院长赴美国参观访问,考察了十几所大学,收效颇丰。他深有感触地说:“访美归来,我们参照美国外交学院的做法,也考虑在外交专业课程中开设双边外交课程,如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等。当时,我曾提出应开设有关联合国的课程,但因条件尚不具备而未果。”
1986年~1990年,袁教授被派往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任参赞兼新闻发言人。其间,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同时对联合国内部机制及其运作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并注意收集有关联合国的各种资料。工作之余,他成了以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命名的图书馆的常客,并把书中有用的资料复印下来。回国后,他对这些资料整理加工,在外交学院为英语专业研究生班开创了一门新课——“多边外交——联合国”,并完全用英语授课。据说,用英语讲授联合国,在全国高校中仅此一家,是该院的“拳头”课程之一。他组织过两次模拟联合国活动(邀请北京高校会讲英语的学生和北京国际学校高年级的学生参加,让其分别代表某个国家或地区,围绕某个专题发言或辩论),为学生提供了难得的锻炼机会。当时,中国联合国协会的代表也出席了这两次活动,他们认为办得很成功。

英译《孙子兵法》受到美军方的青睐
几年前,记者曾从香港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内地袁士槟先生翻译的《孙子兵法概论》在美国再版,西点军校的师生人手一册。对此,我顺便提及。袁答:“《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史上久负盛名,被西方推崇为‘兵学圣典。据我所知,西点军校确实开有《孙子兵法》课程。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防部还向参战的基层军官散发了我翻译的那本书。”他接着介绍说,此书是陶汉章将军编著的《孙子兵法概论》(主要是记述他在战争实践中运用《孙子兵法》的体会)的英译本,1987年在美国首次出版,后曾多次再版,在世界上流传很广。
接着,我又问了他对人生的感悟。他稍加思索后说:“自己工作了50年,一半在外交部,一半在外交学院。虽未对外交事业做出多少突出贡献,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我不论是在美国当客座教授,还是在联合国总部工作,抑或去欧洲旅行、参加国际问题研讨会,走在大街上,常会听到‘袁老师,您好!的招呼声,其中多数素不相识,但对方却说‘我认识你——英语启蒙老师。”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这一景象是再恰当不过了。且不说通过电视节目、录相带学习英语的人,单说他直接教过的外交学院的各类毕业生,就难以计数。
最后,我问及他对外交学院前景的看法及本人的打算。他说:“近些年来,我院不论在教学规模上还是质量上都健康地往前发展,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立场坚定、精于业务、通晓外语的外事干部。我认为,我院必须坚持外语与外交业务的结合,教员应该具备一些外交实践经验。目前,我们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主要有二:一是经费不足,有的教学和科研项目难以开展;二是师资力量不足,尤其是资深教授有断档的危险。至于本人,我已于前年办理退休手续,现仍被返聘,承担一些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任务。将来,我拟把‘多边外交——联合国讲义整理加工成正式教材出版,留给后人参考。”
访谈结束,骄阳高照。在归途,我边擦汗边思忖:外交学院的规模的确不大,但它毕竟是堂堂中华外交官的摇篮,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随着我国外交事业不断发展,它的地位会愈显重要。如何把它办得更好,袁教授指出的那两点还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