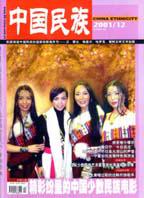西藏散记
聂 冷
洁白的哈达
当飞机从1.2万米高度小心翼翼地开始下降时,茫茫云海终于被一道曲折的“大陆岸线”迎面截住。从机窗看出去,由这道“岸线”标出的黄褐色的陆地上,山峦连绵起伏;白日经空,江河行地,皑皑的雪峰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上蜿蜒挺拔、雄姿勃发,极目不尽。20分钟后,飞机降落在贡嘎机场,皑皑雪峰由脚底升上了苍穹,仍是那样蜿蜒连绵,极目不尽,而愈见其雄奇挺拔。
走下飞机舷梯,脚踏上坚实的大地,就正式进入西藏了。
这片大地号称“世界屋脊”,或曰“地球的第三极”。的确,对于探险家们来说,要想登上这片大地上那数不胜数的雪峰,其难度绝不会亚于步入南北极点。科学显示,这儿的雪峰不仅有着南北极一样严酷的气象,而且有着远胜于南北极的险峻,以及南北极所没有的缺氧困境。然而,这儿的几乎每一座雪山下都有人居住。这是一个久经严酷的环境考验而顽强地适应了“极地”生存的民族;这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热情好客的民族。他们欢迎客人的方式是向客人敬献上一条洁白的丝巾——也就是他们所谓之“哈达”。
果然,一到机场出站口,就有许多幸运的客人受到了早已迎候在那儿的热情的地主敬献哈达的礼遇,令人羡艳。
唯我是一名不速之客,在众人的欢声笑语之中领略自身的落寞,我的心头不由得浮上了一丝孤独感。但我并不失意,因为我一走出机场,就看见了广场前树立着的西藏人民欢迎五洲四海观光旅游者的巨幅广告牌,众多的大巴、中巴以及出租车主一个个笑容可掬地争揽顾客。一个开放的西藏的倩影已在我眼前晃动;虽然个对个地说来,我暂时还没有受到一个明确具体的人员的接待,但笼统地说来,我也是这座雪域高原所真诚欢迎的客人之一。我觉得那些欢迎远客光临的广告牌和宣传画,就都向我表达了这层意思;而那在明丽的阳光下蜿蜒连绵、熠熠生辉的雪山,就是全体藏族同胞献给我的一条凌空飘舞的大哈达。特别是头顶上那碧蓝如洗的净空,则使我体验到了一种出世般的脱俗感。滚滚红尘已远离我而去,万千的尘累和烦恼都已抛却,进入这世界,我已经受到了雪域高原的第一番洗礼。我只想剥去所谓文明的虚伪外壳,袒露出本性的率真。这使我的孤独获得了报偿。
满眼都是白,抬头就是雪,由万千座雪峰孕育而出的雅鲁藏布江水清澈透亮,波光粼粼,没有一丝杂质,我想,如此清冽的一江冰雪玉液,恐怕连微生物也很难混迹其间吧!这真是一个纯洁无比的世界。蓦地,我便顿悟了为什么藏族同胞献给客人的见面礼会是一条哈达。显然,洁白的哈达代表了雪域高原的本色,代表了真纯,代表了藏族同胞的心地。对于主人来说,敬献哈达就是敬献雪一样纯洁无暇的诚心;对于客人来说,接受哈达,就是领受雪域高原的本色的洗礼。
从贡嘎机场到拉萨还有100公里路程。当我登上拉萨民航局的中巴,沿着雪山倒影憧憧的雅鲁藏布江驰往拉萨时,我的心里已经透亮。藏族司机旺堆一边开车,一边用纯熟的汉语热情地给我介绍西藏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业情况,进一步印证了我的感受——西藏已不再封闭,每一个向往纯真、向往善良、向往大美,或者说每一个尊重哈达的人,在这片雪域高原上,都会受到真诚的欢迎;不必拘泥于具体的接待仪式,那在湛蓝的净空中蜿蜒连绵的雪峰,就是一条欢迎你的大哈达。
色季拉山和南迦巴瓦峰
近些年来,登山运动逾来逾引人入胜。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旁边就有登山器材专卖店,为各地登山爱好者提供装备。在青藏高原上,海拔高度7000米以上的雪峰足有好几十座,它们都是人类发泄征服欲和冒险挑战生命极限的理想场所,其中有多座已经被人类踩在了脚下。但在林芝境内有一座海拔7760多米的南迦巴瓦峰,仍傲然挺立在人们的头顶上,它那恒古不化的积雪,已经埋葬了两批胆敢以身相试的日本登山运动员,迄未被人征服。据说由于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南迦巴瓦峰通常隐没在云雾中,人们很难得一睹她的芳姿。可是,这一天,当我跟随友人从林芝出发,沿着川藏公路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色季拉山时,我们却非常幸运地在一片蓝天丽日下瞧见了遥遥相对的南迦巴瓦峰的清晰面容。色季拉山位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北岸,印度洋暖湿气流通过大峡谷呼呼贯入,使该地区形成明显的海洋性气候,植物沿山势自下而上成垂直带分布。谷底为热带雨林,其上为亚热带、温带针、落叶混交林,再上为草地,再上为寒带针叶林,再上为苔藓,再上为冰雪。同一经纬点上分布多种不同气候和植被带,是为天下奇观。色季拉山的山势比较平缓,相对易于攀援,是观赏这一奇观的极佳所在。但当日我们所到达的地方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故只看到积雪覆盖的山顶、苔藓带以及草地和寒带针叶林的过渡带。
时值初夏,然该山海拔4000米以上诸高处,仍皆为积雪所覆盖。皑皑的雪峰气势磅礴,在烁烁的阳光下散发着凛凛寒气,锋芒逼人,耀得人睁不开眼。雪薄的地段,可以看见积雪溶出的一汪汪水洼,洼沿生长着苔藓和些许细微草丝。其下即为莽莽苍苍的雪杉林带,给高原带来一派绿色的生机。色季拉山公路两旁的雪杉林地,残留着许多合抱粗细的大树桩,显示出曾被人类大规模砍伐的痕迹。但现在,路边不时可见保护森林的标语牌,则又表明了人类的进步。站在色季拉山口经幡猎猎的马尼堆旁遥望正前方,南迦巴瓦峰犹如一名冷艳少女,迎面披纱伫立于湛蓝的天宇之下的雅鲁藏布江南岸。她脚踏一片雪原,横空出世,峻峭飘逸,长袖飞舞,令人心仪神往。然而她又超然物外,清雅高洁,至纯至净,凛不可犯,令人敬若神明。大自然的原始之美,实乃通世之至真至美。面对这至真至美的天地之造化,我有一种融入本真、融入圣洁而无物无我的溶化感。我愿化为一缕云烟缭绕其侧,我愿化为一片飞雪飘临其身;我愿陪伴她默然沉思悠悠恒古,我愿追随她翘首天际解读未来……
谁忍心搅扰她深沉的哲思?谁忍心打破她宁静的菩提心境?谁忍心践污她圣洁的银纱?谁忍心以冒犯她的尊严为荣耀来虚饰人世之浮华?
珠穆朗玛峰上的登山垃圾已经引起环境学界的严重关注。不难想象,如果人们再将包括南迦巴瓦峰在内的所有雪峰都插遍五颜六色的万国旗,并且扔遍破背兜烂帐篷,那将是对大自然何等轻蔑的亵渎?感谢我国政府英明决策,断然宣布南迦巴瓦峰为青藏高原上的登山禁区之一,从此严禁人类再度涉足,刹住人们永无止境的征服欲,给世界留下几座至真至美的原始净山。是的,人类已经过于强悍。强悍的人类需要反思,需要哲理,需要净心菩提。面对色季拉山上保护森林的告示牌和正在复兴的植被,面对国法保护下安然伫立的南迦巴瓦峰,我终于看到了人类理性的希望之光。
米拉山牧民
米拉山与色季拉山遥相呼应,它是西北边的拉萨河水系与东南面的尼羊河水系的分水岭,也是林芝地区海洋性气候与拉萨地区内陆性气候的自然分野。与色季拉山相比,米拉山具有更为显著的地理分界意义。从林芝出发,溯尼羊河向西北上行,可以明显看出土地越来越旱瘠,植被越来越稀疏矮小。到工布江达县西北的尼羊河上游流域,已很难见到树木。科学解释说,青藏高原是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剧烈碰撞,致使地壳拱曲而隆起的一座巨岩。亿斯万年以来,裸露的岩体历经日月星晖,冰雪涨缩,风雨侵蚀,被剥落成块,碾磨成沙,化解为土。于是,皇天后土孕育万物,滋养了人类。但是,在雪山上,微细的土末都要被流水冲刷到主要河道的中、下游河谷地带,才能沉积下来形成农耕意义上的土壤,而山顶、山脊和山梁上,则一律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黄沙,由此构成了整个高原内陆气候区的典型地貌。米拉山也不例外,它的岩层深深地风化变质,山体破碎,表层沙化,戴着雪帽的山顶已被大自然的伟力磨削成平缓光溜的“馒头”状,雪帽下裸露的沙层上滋生着苔藓和些许草丝,表示着生命的存在。惟尼羊河两岸的沙洲和较滋润的坡地上,才稀稀拉拉瘌痢头似的长有些勉强能被牛羊啮起的草棵和一丛丛沙棘,据说要20公顷以上的地面生长的牧草,才能养活一头羊。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地段,也有人居住。这便是我所见到的米拉山区的牧民。严格地说来,我并不能表明我对这些牧民有多少确切的了解。汽车一路匆匆驰过,望眼所及处,时而可见草坡上扎着几顶黑黑的帐篷,帐篷边垛着一两堆干牛粪饼,为数不多的马、羊和牦牛,零零星星地自由散落在远远近近的沙洲或山坡上,坚韧不拔地寻觅和啃啮着永远喂不饱肚的草棵。几个满面沧桑的女人蹲在尼羊河边漂洗衣物,身后的卵石滩上铺晒着刚洗出的衣衫,显示着她们与大自然的亲近及其简朴自然的生活方式;孩子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转着滴溜溜的眼睛,向往来过客友好地挥手致意,间或有汽车停下,他们便会怯生生地凑上来向游客伸出一只乌黑的小手……
毫无疑问,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自身努力之下,西藏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显著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条件已和发达地区没有什么区别。但就米拉山牧民的情形来看,我却可以猜想,他们的日子准定还很贫困;他们远离市镇,没有电灯电话,一切靠电能驱动的现代玩意儿都与他们无缘,因而他们生活上也肯定会有诸多不便。他们只能用还算锋利的藏刀割食生牛羊肉,喝牛粪饼烧热的奶茶,点酥油灯照明;他们的全部家当也许只要一头牦牛就可以驮走,惟一称得上财富的东西,便是那差可糊口的几头活牛羊。用现代社会经济学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不过是一种简单的生存而已,想要他们在这人类生命的极限区靠放牧致富,几乎可以说无从谈起。可是,他们能在这海拔4000多米近似荒漠的山地上战胜干旱,战胜贫瘠,战胜风雪,战胜严寒,战胜缺氧,战胜山崩地裂的地层运动,战胜紫外线和各种高能粒子流的轰击,顽强地生息繁衍,一代又一代绵延不绝,这本身就是一部显示人类生存能力的伟大史诗。他们在世世代代对大自然的奋斗与亲和中,充分地展示了人类生存的伟大智慧和力量。我并不想粉饰落后。米拉山的牧民无疑也需要文明世界的帮助和提挈,但他们那一派俯仰天地,吐纳日月的胸襟和豪气,和他们身上所蕴藏的那股忍受人间奇苦,于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得生存的顽强毅力,却不能不令我倾倒。我先后掏出了10块零钱,分别献给了5只伸在我眼前的乌黑的小手。我很惭愧。我知道,正是这些孩子的历代先人,以他们无比顽强的生存膂力,为我们中华民族开拓并镇守了这一方纯洁无瑕的银色宝地。他们还将世世代代继续在这里坚守图强,谋求发展与进步,我所能报偿他们的实在太少,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