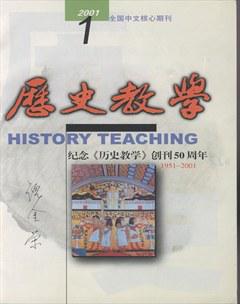略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
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过去一百年了。这场发端于山东与直隶边界、以华北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展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特有的反抗方式和斗争精神,具有正义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自发性、分散性和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也由于各省区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学界迄今对运动发展阶段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一些专著虽然详尽地论述了各地义和团运动的兴衰,但缺乏做全局性的阶段划分;有关专题论文寥寥无几,且存在着意见分歧。还有些论文仅从某一省区运动发展的角度进行划分,或者仅论述运动发展的某个阶段,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对运动全局的宏观把握和审视。
综观以往对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有三分法和二分法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运动可划分为运动的兴起发展时期、运动的高潮时期和运动的低潮时期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作了较为详尽精到的论述。但其划分的一些时间界限值得商榷①。还有的以口号作主要依据,认为运动可划分为“反清复明”、“扶清灭洋”和“扫清灭洋”三个阶段。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存在“反清复明”和“扫清灭洋”阶段,应当以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发布“宣战”上谕为界,划分为“扶清灭洋”和“奉旨灭洋”两个阶段②。愚以为,划分运动发展阶段除了要考察口号的转换之外,更应追寻运动自身发展的轨迹,结合斗争的内容和统治者相关决策的变化来确定;还应以运动的主流来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据此,义和团运动大抵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8年山东、直隶拳民正式聚众起义到1899年春夏之交,这是运动兴起和早期斗争阶段。早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前,直隶威县、曲周、永年和山东的冠县、临清等地便有各路拳民亮拳比武之风。直隶大名府还发生了两名天主教神甫被当地大刀会员杀死一案,以及大刀会贴出号召爱国志士约期“屠戮西人,焚毁其居”的揭帖③。民教冲突屡屡发生并走向激化。1898年10月,直隶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山东红拳首领阎书勤等率领山东、直隶拳民数百人,在山东冠县蒋家庄(今河北威县)宣告起义。他们举起“助清灭洋”旗帜,攻打教堂,开展反洋教斗争。各地拳民纷纷响应,队伍逐渐发展到千余人。这一事件点燃了直隶、山东边界地区反洋教斗争的烈火。其后,以“赵三多为头领,啸聚数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威大振”④。劳乃宣曾言:“义和团之扰,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冠县仇教之案。”⑤可见,它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此后,山东的冠县、临清、高唐、恩县、茌平、平原、德州一带和直隶的威县、曲周、清河、枣强、大名府、开州、东明等地的梅花拳、红拳、神拳、大刀会等纷纷聚众立坛。直隶枣强县人王庆一迎师铺坛,树“助清灭洋”旗帜,练“五祖神拳”,率众攻打萧张镇教堂,成为当地著名义和团首领。山东长清义和拳首领朱红灯,以行医卖药为生,设场练习神拳,1898年率众攻打本县教堂。次年初转移到茌平、高唐、平原一带活动,并结识了另一义和拳首领心诚和尚,广招拳众,产生了很大影响。面对义和拳运动的日益发展,清政府十分恐慌,急令直隶总督裕禄、山东巡抚张汝梅及继任毓贤前往镇压,致使姚文起等人被捕遇害。
这一阶段运动的特点是:拳民以攻打、焚烧教堂,逐杀传教士为主要斗争目标,同时也抗击前来镇压的清军。拳民虽然以农村分散斗争为主,但已突破省、县畛域,开展了松散的联合斗争和相互支援。各类拳民的宗教信仰及仪式各不相同。以赵三多、阎书勤为首的义和拳,专练武术,没有画符念咒、烧香请神的仪式,迷信色彩比较淡薄⑥。朱红灯等人的义和拳,则继承了神拳的传统,有画符念咒、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宗教仪式。大刀会作为民间教门与金钟罩(亦称铁布衫)功夫相结合的民间武术团体,也有较浓的迷信色彩,其宗教仪式与神拳相类似。清政府视各路拳民为“拳匪”、“邪教”,一些地方官认为“义和拳符咒治病与汉张角同”⑦,把它与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等量齐观。清政府对其采取的政策是饬令清军和地方官“弹压解散”。但镇压政策不仅没有消弭拳民的斗争,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抗浪潮。新任山东巡抚毓贤无力镇压义和拳,转而采取剿抚兼施,先抚后剿的政策。直隶义和拳首领朱九斌、刘化龙等率众进入直隶中部地区活动,促使义和团运动迅速蔓延到直隶中部地区。
第二阶段从1899年初夏义和拳陆续改为义和团,活动范围大大扩展,到1900年5月义和团占据控制第一座州城———涿州为止。这是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也是运动的重心由直、东边界转移到直隶中部地区的阶段。从山东来看,1899年4月11日,清政府谕令山东巡抚毓贤“督饬地方官,随时多方开导,务令民教相安”⑧。这已初步透露了招抚之意。加上毓贤本怀有仇外情绪,故转而承认义和拳为民间合法团练,并正式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也就在此间改称义和团,并走向公开斗争的。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又涌现出王立言、王玉振、徐福和、李长水、高元祥、李传和等重要首领。同年10月,以朱红灯为首的义和团在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和森罗殿先后击败前来镇压的清军,使义和团声威大振,震动了山东官府。慑于义和团的声势和威力,毓贤更倾向于招抚义和团,遂奏请清政府将镇压义和团的署平原知县蒋楷“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将统兵镇压团民的袁世凯“撤去统带”,并建议“发交袁世凯随营历练,以观后效”⑨,最后清政府传旨将蒋楷和袁世敦一并革职。这一决定客观上有利于山东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此后,朱红灯分兵攻打茌平、博平、清平、高唐、恩县、禹城等地教堂和惩罚教会势力,使鲁西北的义和团运动掀起高潮。
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大为恐慌和不满,美、法等国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要求撤换毓贤和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得已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毓贤在离任前为讨好帝国主义,竟于1899年12月逮捕并杀害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继而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采取查禁镇压政策,使山东义和团运动转入低潮。
与此同时,直隶义和团运动则迅速蔓延到直隶中部地区。1899年5月17日,赵三多、刘化龙、朱九斌等义和团首领以佛爷生日烧香为名,在正定大佛寺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大家认为要改变办法。有一个姓李的河间人提议,“现时静海、青县、东光、南皮各县,在红门暗里秘密吃符念咒,练的叫铁布衫,枪刀不入,能以避火,不怕洋枪大炮”,老百姓很信他们,“不妨我们凑他一步,我们学那个办法”(10)。这一建议得到各路首领的赞同,于是决定学习直隶中部地区广为流传的铁布衫(金钟罩)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之术,并把直隶中部地区作为活动的重点地区。会后,深州、河间、顺德、正定、保定、天津、顺天、易州乃至北京等地,纷纷迎师设坛练拳,涌现出张德成、曹福田、武修、王成德、李来中、周老昆等重要义和团首领。因此,正定大佛寺会议决策向清朝统治的腹心地区发展,应是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这一阶段总的情况与特点:一是各地义和团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相互“拜团”之风颇盛,促使各省、各地区、各拳种之间走向相互融合和渗透。二是团民逐渐由农村向城市进军,使城市的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三是义和团的口号、旗帜、宗教仪式逐渐趋同,“扶清灭洋”的口号和画符念咒、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宗教仪式越来越得到广大义和团民众和基层社会的普遍认同。四是运动的日益发展使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主抚、主剿两派的意见纷争。慈禧太后态度犹豫,对义和团时而剿抚兼施,时而感到剿抚两难。清廷的这种态度造成了各地地方官无所适从和各省区之间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如山东自从朱红灯和心诚和尚被杀害和袁世凯继任山东巡抚采取查禁镇压政策后,又屠杀了一批义和团,致使运动一度低落。但从全局来看,义和团运动是在清政府政策不定、剿抚两难的空隙中抗官灭洋,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
还值得注意的是,直隶、山东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对其他省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1900年夏天,东北“奉属锦州、宁远、新民、广宁沿边一带,时有拳民出没,勾结土著良民之曾受教民欺凌者,一唱百和,妇孺皆起”(11)。毗连直隶的河南省彰德府之武安县,也出现了“焚烧高村教堂,困逐教士”的事件;“新乡、获嘉均有教民被掠之事”(12)。1900年春夏之交,毓贤就任山西巡抚后,发现“山西地方亦有拳民”(13)。可见,庚子年夏,义和团运动已在华北乃至东北等地广泛发展起来。
第三阶段从1900年5月27日义和团占据涿州到同年9月7日慈禧西逃途中发布剿团命令时止。这是各省义和团运动全面高涨和抗击八国联军的阶段。这一阶段义和团运动除波及范围广和参加人数多之外,还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一是大批团民纷纷从农村涌向城市,使义和团的活动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数万团民占领并控制涿州城,吹响了向城市进军的号角。此后,直隶团民纷纷进入京、津、保等中心城市,自6月中旬起,大批团民进入北京,“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继而团民“不分昼夜,鱼贯而来……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到清廷发布“宣战”上谕时,进京团民约有十余万人(14)。在天津,有安次义和团首领杨寿臣,静海、盐山一带著名首领曹福田,霸州、雄县、文安等地义和团首领王成德和独流“天下第一团”首领张德成先后率众进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对他们优礼有加、引为上宾,以致义和团公然“在道、府、县大堂设坛”(15)。天津的局势几为义和团所控制。英国领事贾礼士说:“天津城已实际掌握在义和拳和暴徒们手中,他们焚毁了礼拜堂,并在街上强迫中国官员们下轿。”(16)直隶省城保定也团民充斥,驻保外籍教士及各类工程技术人员惊恐万状,只好请求由官方派兵护送逃往天津。团民扬言某日举事烧天主堂,并杀三名大员,即直隶布政使廷杰、直隶督标中军副将张士翰和莲池书院主讲吴挚甫。他们还声称将有万名义和团赴都勤王,由保定南门径城而过,以耀神威(17)。团民大量进城(特别是进入京城)有力地促使清廷于6月21日发布“宣战”上谕。
而清廷的“宣战”,又极大地激励了团民的“灭洋”斗争。在直隶团民进城斗争的影响下,山东德州团民进攻德州城,济南团民焚烧教堂与铲平传教士坟墓,其他各县也有不少团民“声言非入城不可”,有的“竟敢窜入县城,挟制官长,勒索粮银等项”(18)。山西各地义和团也相率进入省城太原,使太原成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河南发生了大规模围攻南阳靳岗教堂的斗争。在东北沈阳,义和团首领刘喜禄率领团民焚烧耶稣教堂,冲击沙俄设立的铁路工程公司,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帝斗争。这些都说明,义和团的活动重心已转移到城市。
二是团民与清军相配合,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斗争手段,参加了攻击外国侵略据点、抗击八国联军进犯和保卫天津、北京的战争。1900年5月2日直隶义和团占据涿州后,为了斗争之需要(阻止清军运兵进剿义和团和狙击西摩尔联军进犯)和自身的生存(铁路修成后许多原先水手、纤夫和驿站工人失了业),直隶一些团民采用了毁铁道、砍电杆、烧车站、抢洋行等斗争方式,因为“铁路向归洋人经理,是时义和团烧铁路、毁车站、坏电线,专与洋教为难”(19)。可见他们把它们作为一种斗争手段。这一斗争方式也影响到山东、奉天、吉林乃至黑龙江等地。这样做一方面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另一方面也使运动带有笼统排外倾向。
三是清政府实行招团御侮政策,令载勋、刚毅等统率义和团。他们一面令团民到庄王府和各地官府注册挂号,并酌发粮米、武器奖励团民,使之成为“奉旨义和团”。一面派人持令旗至京外招团民进京、津抗敌前线助战。如庄王曾派人持令旗到直隶新城、定兴招团民近万名赴京(20)。又有天津拳民王玉书,持直隶总督裕禄令箭,带领140名团民赴山东德州招收团民,限12日回津,共打大沽洋人(21)。在清政府的倡导奖赏下,怀抱不同目的的各阶层人士纷纷设坛练拳。柴萼云:“设坛一事,初唯匪徒为之,继则身家殷实者亦然。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22)义和团的组织成分也由此变得复杂和不纯,并在一定程度上酿成了奉旨团民与“假团”的互斗。
第四阶段从1900年9月7日清廷下令剿杀义和团到1902年景廷宾起义和邓莱峰拒洋会社斗争失败为止。这是清政府公开改抚为剿,义和团运动转入低潮以及复起斗争和失败的阶段。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后,伴随着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义和团运动迅速低落。9月7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将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说什么“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令直隶等地痛加剿杀,要“严行查办,务净根诛”(23)。之所以要以这次上谕作为划分阶段的分界,是因为从此义和团遭到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运动迅速低落和分化,高潮时期一哄而起设坛练拳的地主官绅和王公贵族迅速撤坛而销声匿迹;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团民,除一部分留在城市周围坚持抗击侵略联军的斗争,力图恢复被侵略军占领的城市外,大多都散归乡里,原先的“扶清”已不复存在,运动迅速走向低潮。
血的教训使许多团民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面目。自1901年9月7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后,便将巨额的对外赔款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人民群众不堪重负,以联庄会形式发动了抗洋捐斗争,一些义和团民又重新汇入这一斗争之中。早在1900年10月,朝阳反洋教首领邓莱峰以联庄会形式组织拒洋会社,不仅多次打败外国教会势力的武装进攻,也拒绝清直隶提督马玉山昆的劝降和抵抗其武装镇压,举起“反清灭洋”旗帜,坚持了两年多才最后失败。1902年,直隶广宗县联庄会总团长景廷宾因反对将“小赔款”摊派民间,与官府多次交涉未果,反被官方通缉。景廷宾组织联庄会与清军发生武装冲突。4月23日,景廷宾与原义和团首领赵三多、郝振邦等高举“扫清灭洋”、“官逼民反”的大旗,在直隶巨鹿县厦头寺发动武装起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的义和团民、联庄会众及流民纷纷响应参加,队伍发展到数万人。他们与清军总兵段祺瑞等展开了多次战斗,直至同年7月失败。与此同时,四川人民也举起了“灭清剿洋兴汉”的旗帜开展斗争;东北人民则组成了忠义军、六合拳等进行抗俄反清斗争。虽然这些起义最终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但他们不仅坚持反帝、反洋捐斗争的大方略,而且加进了“反清”、“扫清”、“灭清”的新内容。这表明,他们通过血与火的洗礼后,已将反帝和反封建结合起来,不仅为义和团运动谱写了悲壮而光辉的结局,使帝国主义列强不敢轻言瓜分中国,也为20世纪初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了一定的铺垫,其历史意义不容否定。
① 戚其章:《试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4期。
② 参见欧阳跃峰:《从“扶清灭洋”到“奉旨灭洋”》。《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
③ 吴宣易:《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正中书局民国三十六年版,第7~8页。
④ 《杂录志纪变》。《冠县志》卷10,1935年修。 ⑤ 《庚子奉禁义和拳汇录跋》。《义和团》(四),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486页。
⑥ 路遥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65~267页。
⑦2022 《义和团》(一),第354、464、306页。 ⑧⑨13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36、181、161页。
10 郭栋臣:《义和团的缘起》。《河北文史集粹》社会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49页。
12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34页。
14 仲芳氏:《庚子纪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2~14页。
15 《义和团》(二),第143页。
16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页。
1719 《义和团史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0、161页。
18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4~35页。
21 《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23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53页。
(黎仁凯,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代表著作有《动荡中的历史抉择———近代知识分子的追求》、《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张之洞与近代中国》(合著)等,发表论文近80篇,曾在《历史教学》发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等多篇论文。)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