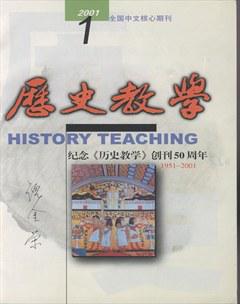创建有我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
新的21世纪已经到来。中共中央“十五”规划的建议鼓舞人心。我们世界史学科的工作者们在新世纪如何创新、开拓和振兴学科,是人人关注、值得探研的问题。
首先,应回顾我们的收获和不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年间,我们的主要成绩和特点是:(1)唯物史观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流;(2)理性精神有所发扬,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同时,注意汲取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3)初步建立了我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和分支,组成了各个专业的全国性学会,有了一支初具规模的队伍;(4)加强了基础教材和资料的建设,涌现了一系列新著述;(5)在某些国别史(如对美、日、英、德、法、俄、加等)的研究上有所进展,中外对比和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开始起步;(6)走出去,请进来,参加了第15~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等,加强了对外交流。世界史学科二十年来虽然有明显的发展,但是同拥有12亿人民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和要求来看,同国外同行相比,我们仍有差距。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1)世界史学科工作者的队伍,从数量和质量上看尚较弱,而且年轻的骨干不稳定,老专家的作用发挥不够。迄今某些国别史方面还有空缺点。对北欧史、对西欧的意大利和西、葡,甚至对相邻大国印度、印尼的研究亦较弱。(2)世界史范围学术价值大、现实意义强的精品或多卷本力作不多。研究涉猎的领域和问题还不够宽广。(3)对世界上历次科技革命的背景、对历史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等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尚未展开深入研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选题的视角欠新,史学转轨的力度不够。(4)“欧风美雨”冲击较大。对有些人,马克思主义对学科的指导作用有所忽视;部分人员中出现了过分推崇西方学术理念的现象。
其次,我们对国际上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与现状,应当重视和加强了解。
许多国家有重视历史科学的传统,历史学派颇为广泛,如:兰克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形态史观、年鉴学派、新史学、结构主义学派、边疆学派等。
史学理论与方法多样化。一系列新的交叉学科、跨学科、多学科(与自然科学结合)研究普遍,如:历史文化学、历史旅游学、历史社会学、历史经济学等。
研究领域拓宽,课题多元化。以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00年8月在奥斯陆举行)的专题和圆桌议题为例,有环境史、自杀史、疾病史、同性恋史、旅游史等。
“信息时代”下,各国人民、学者联系颇繁,运用电脑等现代化手段开展研究与交流。历史档案的解密,“禁区”逐渐缩小,均有利于活跃学术。
国际间科技竞争加剧,世界史学领域中的竞争亦激烈。我目睹过1995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第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间台前幕后的斗争,围绕我国申办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一些国家遏制中国的政策和手法。
国际上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仍笼罩着世界史学界,近些年“欧洲中心论”的变型是“欧美中心”。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历届的组成,以及活动的导向和科研选题等等的剖析来看,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不被重视,是十分明显的。
新世纪到来之初,我们必须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振兴和改革而奋斗!我们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要上新水平、要有新超越,关键是要走自己的路,要创建有我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
第一,必须充分发挥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尤其是世界史学科的重要性,在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这本是一句老话。但当前重申和强调它,是有具体针对性的。近些年,我国“重理轻文”、“历史无用论”的现象明显存在。我们从事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学习历史科学可以使人们了解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政治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历来特别强调历史科学的重要性。法兰西斯·培根指出:“读史使人明智。”中国许多名人总结道:“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毛泽东同志分析道:“没有历史知识想取得革命胜利不可能。”邓小平同志说过:“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江泽民同志多次号召:“开放要吸取国际经验”,“为了适应国际交往,更好地借鉴各国长处,要了解世界的历史”。我们认为:历史学是提高政治觉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主课。
历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是个老问题。我们不同意摘引马、恩、列和毛泽东的个别词句贴标签式地作立论根据,反对“两个凡是”,反对时时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也不同意目前一部分人中贬低马克思主义,把它只作为“许多方法论中之一种”的观点。我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去研究历史学,乃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史学的特色和长处。在世界史的研究中,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影响,以及关于历史的主体与客体、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等等重大问题的论析上均有所依据。我们认为:人类自奴隶制社会以来,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客观存在,正确掌握政治学的方法和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乃应有之义。这正是我们同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根本分歧。
第二,要继承祖国悠久的史学研究的传统、经验和方法,发扬我国自古便重视外国史的长处。
中国是一个有治史传统的文明古国。我国史学典籍之丰富,其生命力之久远,内涵之独特和丰富,在世界文明史中是罕见的。早在19世纪初,黑格尔通过对各国历史著作的分析对比之后,曾写道:“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而尤其使人惊叹的,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①以我国著名的第一部史书《史记》为例,这是一部上下约三千年的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曾坦言撰著《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强调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所说的“天下”,不只是中国,而是包括了中国以外的诸邻国。可见早在司马迁时代,便重视了边疆以外的世界史。我国《二十四史》中,历朝修史多在《外国传》中记述着邻国的情况。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记载了自周至五代上下1362年的编年体通史。他的目的是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资治通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记叙详尽,而且参用杂史、传记、奏议等资料多达三百余种。史料价值和应用效果极高。
世界各国的规律是社会上升、发展繁荣时代,或纷乱多事、矛盾复杂时期,史学最为发达,出了许多大史学家。下面以中国的著名史家及其宏著为例加以说明。我国汉武时代出了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而司马迁死后约一百三十年,东汉时出了《汉书》的作者班固(公元32—92年)。东汉末《汉纪》(30卷)的作者是荀悦(148—209年),他写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继他之后近40年出了《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年)。唐代盛世史学理论家刘知几(661—721年)所著《史通》、吴兢(670—749年)所著政论性历史文献《贞观政要》和“安史之乱”后杜佑(735—812年)著的经世致用的《通典》,都曾享誉中外。著名史家,11世纪有欧阳修、司马光。《新唐书》中纪、志、表出自欧阳修(1007—1072年)之手。12世纪,郑樵(1104—
1162年)完成了200卷纪传宏篇《通志》。李焘(1115—1184年)作《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并考订了北宋九朝168年史事。朱熹(1130—1200年)的59卷《资治通鉴纲目》,创建了新的纲目史体。马端临(1254—1323年)所著《文献通考》是一部典章制度专史。查继佐(1601—1676年)撰写的《罪惟录》是经世济国的断代史。王夫之(1619—1692年)著的30卷本《读通鉴论》乃引古鉴今的力作。顾祖禹(1631—1692年)的《读史方舆纪要》是详述中国历史地理沿革的名著。黄宗羲(1610—1695年)的《明儒学案》是完备的一部学案体系名著。
18、19世纪中国著名史家尤多。如著《宋元学案》的全祖望,撰《十七史商榷》的王鸣盛,著《廿二史札记》的赵翼,撰述《廿二史考异》的钱大昕、写《续资治通鉴》的毕沅,尤其是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乃“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开创了方志学,对史学理论有重大贡献。魏源的《圣武记》,特别是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100卷本的《海国图志》,迄今仍值得借鉴。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是关于我国西北边疆和中俄关系的巨著。夏燮用纪事本末体著的《中西纪事》是国内最早的国际关系史和列强侵华史。20世纪上半叶,我国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垣、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名家辈出;下半叶,五大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并立。
综上所述,中国史籍浩繁、博大精深,乃世界之最。梁启超等倡导的史家必备“四长”(指刘知几提倡的“史识、史学、史才”,加上章学诚所倡的“史德”)等都是我国史学特有的精华。
第三,要结合中国实际,不囿于传统题目和陈旧视角,要拓宽研究领域,在“新”字上下功夫。
在世界各国的历史当中,以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最长,封建专制的流毒也最广。邓小平曾指出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②我们在世界中世纪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应结合中外历史深入批判封建主义,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各种流毒,这是我们建国以来重视不够的问题。我们应当总结文艺复兴前与后,中国同西欧历史发展的差距。14世纪前,我国的科技水平在世界上一直是领先的,明清以后中国才逐渐落后了。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四化”。鉴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世界中世纪史和近代史领域应重点研讨各国工业化的道路和经验,十分重视对科技问题的研究。因为科技实际是当代国际竞争实力的砝码,也是分析世界未来走向的重要指标,而世界上历次科技革命都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有规律可循,其经验尚待深入总结。世界史学科对此责无旁贷。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很有必要从世界历史的浩瀚经验中找到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绝不能放松精神文明。但是我国迄今还没有一本关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的较有分量的力作,这是重大缺陷。应及时补缺,负起历史重任。
在世界史学科中,应重视新选题,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如人口史学、生态史学、历史经济学等。根据我国的基础、资料积累状况和特长,找准科研的“突破口”、“切入点”,勇于开拓。凡涉及别国的历史,应以对象国的第一手史料为依据展开研究。我国属于第三世界发展中的大国,除对欧美发达国家继续重点研究外,要逐步弥补“空白工程”,对亚非拉,特别是把南非、南美和阿拉伯世界纳入重点,有计划地逐步建立我国全方位的世界史学科体系。
第四,要充分挖掘世界史的学术“资源”,发挥世界史学科的生命力,对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的研究两手都要过硬。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不容讳言的是史学成果也以商品形式在市场经济中提供交换和发挥作用。既要维护科学品位,又不能脱离市场所需。近年来,为什么出现“史学危机”?为什么历史科学渐被一些人们所忽视?其关键之一是人们把历史当成死知识,当成若干年前的“大事志要”,只要对它死记硬背就能得满分。这样一来,史学变成同当前国计民生无关、无用的死学科,走进了死胡同。
我们认为世界史学科涵盖了浩瀚的活知识,急待开发、探研。我们对许多基础性问题仍有必要用新资料、新方法、新观点继续钻研,但今天必须强调把应用史学的研究开展起来。应用史学同实用主义史学不可混淆。
“文革”动乱时期,“四人帮”大搞影射比附、“批儒评法”等实用主义史学有其险恶用心。我们提倡的应用史学是以唯物史观、辩证方法为基础,精选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利用世界史的原始史料去研究。例如,综合性的大题目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苏联模式的教训、东欧剧变的历史根源、各国不同时期的社会转型问题、民族分离主义思潮、国际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人权与主权的关系等。专门史、专题史中的题目如:各国灾荒史、人口史、金融证券史、交通史、城镇的发展、水土资源、各国文明习俗比较等。此类题目同“四化”有关,又是人们喜欢乐见的。
第五,必须通过“百家争鸣”以活跃学术氛围,还应旗帜鲜明地投入史学战线的斗争。
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学术思想活跃、争鸣的时代,社会就大飞跃,学术必然大繁荣。春秋战国时如此,1978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时更是如此。近几年我国史学界出现学术上“少交锋、少争鸣”的现象,这不利于史学的前进。我国建国以来,在“革命大批判”口号下,有过许多严重失误。如《武训传》的讨论、批判胡风、批判《海瑞罢官》等等,都是事实。但不能因噎废食。凡是人民内部的学术讨论都应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允许学术上的批评和反批评。在报刊上应允许和支持不同学派并存和保留各自的学术观点。学术问题上争鸣促进发展,强调“舆论一致”违背科学,不符实际。
历史学,包括世界史是阶级性很强的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今天不应笼统地提倡史学批判,但不等于对史学评论持取消主义。过去对于汤因比的“白种人的负担论”,最近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声音甚弱。联想起1985年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教训,大会的主题之一是讨论马克斯·韦伯的史学理论,但我们事前信息不灵、准备不够,以致我们在会上没能投入热烈的争论。我们对国际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史观,不能置之不理。例如,日本右翼分子叫嚣的“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东史郎案”,还有关于靖国神社参拜问题等年年都碰到。我们必须根据史实,揭露真相,批驳谬论。以日本的“参拜靖国神社”为例,日本某些政客扬言靖国神社中都是为日本国而牺牲的“英灵”,例行参拜乃“爱国之举”。这完全是蓄意混淆视听。实际上靖国神社中祭祀的明治维新时西南战争的战死者是极少数。而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死亡的官兵二百多万人(包括战犯东条英机的牌位在内)均在供奉之列。参拜“英灵”,是美化侵略战争,为复活军国主义招魂。
在史学战线上分清大是大非是必要的。我们的世界史学科不应泛提同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接轨”,不能跟在西方史学后面爬行。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新体系。
21世纪里,我国继经济建设高潮到来之后,文化建设的高潮必将伴随而来。世界史学科也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和繁荣。我们必须开拓、拼搏和创新,才能在国际充满竞争、挑战的学术前沿,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够圆史学前辈们多年的梦,才能真正振兴和腾飞,让我们以时代的责任感和迫切感,完成应尽的历史使命吧!
① 《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1、1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刘明翰,湖南师大教授。曾任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常务编委,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主任、校图书馆馆长,共青团中央高级职称评委,德国弗赖堡大学讲座教授。现兼任中国世界中世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曾著《罗马教皇列传》、《美洲印第安人史略》,主编《世界史·中世纪史》(高校统编教材)等著作共24部,专业论文8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是世界中世史、中外关系和世界文明史。)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