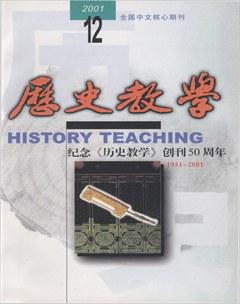浅议明代中后期治理黄河的“两难”
吕天佑
在永乐迁都北京以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明王朝的政治、军事重地一直在北方。为维持北京作为首善之地粮米什物的供给,从江南向北京运粮遂成为维系明王朝命脉的根本性经济问题。几经权衡筹措后,开通运河运送漕粮成为最佳选择。但漕运所资之运河在航道上却要借黄通漕,这就使治河受到“保漕”这个事关明王朝根本利益的经济问题的影响,在此原则基础上明代治河重北轻南,北部筑堤以使黄河南流,同时又要保持漕运所需的水位。
与“保漕”的经济战略相应,明代治黄又面临着在南面“护陵”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籍在凤阳,祖在泗淮之地,黄河南流夺淮入海,势必屡淹淮泗之地,威胁泗州、凤阳安危,这直接关系到明王朝凤阳皇陵、泗水祖陵的安危。
因此,明代治河就不仅仅是单纯治理黄河水患的河政、河工的问题,它还关乎维系国家经济命脉的漕运问题,关乎陵寝安危的政治问题。这样,黄河治理就在既要治理河患,又要南防侵陵、北防淤运道的两难境地中艰难而行,治河措施受到较大掣肘。故支大纶说:“河之难治如此,其在今日则资其利,而又畏其害。利不可弃,则害不可蠲也,其难则十倍于汉矣。河自汴而合淮,故决在汴。汴幸无决,而东危汶泗,北危清济间,又决而危丰沛矣。即幸旦夕无恙,而又虞其绝北而厄吾漕。幸漕利矣,而合淮会泗,激而横溢,淮凤泗以侵祖陵。纵之则陵危,决之而运道危。愈积愈高,则徐邳之生民危,顾不甚难哉!”①
一、明代漕运与黄河治理
明初,太祖建都南京,京师所需粮食多来自附近地区,南北漕运未成重大政治任务与经济问题。为支援当时的对蒙元战争,大将徐达曾开鱼台塌场口,济宁耐牢坡,引河水入泗以济运,“通漕以饷梁晋”,另还曾“由开封运粟,?河达渭,以给陕西;用海运以饷辽卒”②。至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南粮北调的任务日益加重。永乐元年(1403年),“纳户部尚书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陈州颖歧口跌坡,别以巨舟入黄河抵八柳树,车运赴卫河输北平,与海运相参”③。永乐四年,“成祖命平江伯陈王宣督转运,一仍由海,而一则浮淮入河,至阳武,陆挽百七十里抵卫辉,浮于卫,所谓陆海兼运者也。海运多险,陆挽亦艰。九年二月乃用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言”④,改建会通河,疏浚南北大运河之议遂起。
会通河是元朝至元年间开通的,时在?城筑坝,逼汶水入氵光河,流到济宁后,使汶水南北分流。但因济宁地势北高南低,往北行水困难,加之河道“岸狭水浅,不任重载”⑤,会通河一直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决原武,漫安山湖而东,会通河尽淤。永乐初,为了解决南粮北运问题,不断有人提出疏浚会通河的建议。永乐九年(1411年),济宁同知潘叔正上书,进一步陈述了开会通河的必要与可能,并指出:“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至淤塞者三之一,漫而通之,非唯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⑥永乐帝纳其言,决定修浚会通河,并命工部尚书宋礼、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等主持这一工程。
宋礼等接受了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在汶水下游东平戴村筑新坝,拦截汶水全部流至济宁以北的南旺。因这里地势最高,被称为“南北之脊”。分水处从济宁移至南旺后,使水分流南北,“南流接徐、邳者十之四,北流达临清者十之六”⑦,从而解决了元代行水不利的问题。为了使会通河水有所控制,便于行船,宋礼等在元人旧闸的基础上,“相地置闸,以时蓄洪”,新建、改建了一些闸门,使会通河节节蓄水,适应了通航的需要。
会通河开浚不久,宋礼等又在山东境内“又开新河,自上袁家口左徙五十里至寿张之沙湾,以接旧河”;在河南境内,疏浚祥符鱼王口至中滦下二十余里黄河故道,自封丘金龙口,引河水“下鱼台塌场,会汶水,经徐、吕二洪南入于淮”⑧,以接济运河水量。在整治会通河和黄河以后,主持漕运的平江伯陈王宣又采纳地方故老的建议,“自淮安城西管家湖凿渠二十里,为清江浦,导湖水入淮,筑四闸以时宣泄”。又“缘湖堤十里筑堤引舟”⑨,使南来漕船经由湖水直接入淮,避免了陆运之艰辛。以后,他又陆续“浚仪真、瓜州河以通江湖,凿吕梁、百步二洪石以平水势,开泰州白塔河以达大江。筑高邮河堤,堤内凿渠四十里。久之,复置吕梁石闸,并筑宝应、汜光、白马诸湖堤,堤皆置涵洞,互相灌注。是时淮上、徐州、济宁、临清、德州皆建仓转输。……又设徐、沛、沽头、金沟、谷亭、鲁桥等闸”。经过这一番大的整顿,“自是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10。至此,南北大运河全线畅通,它南起杭州,通过江南运河、淮扬诸湖、黄河、会通河、卫河、白河、大通河,北达京师以东通州大通桥,全长三千余里。通过这条运河,大量粮米百货源源北上,维系京师所需,此运河遂成为此后二百余年明王朝的生命线。
但是,在南北大运河沟通后,由于徐州北至临清一段往往受黄河北决冲淤,徐州南至清河一段又以黄河为运道,漕运常受黄河水患干扰,时通时塞。故终明一代,治河、治运纠缠在一起,河、运结下了不解之缘。
面对河、运交叉的形势,明人既害怕黄河冲毁或淤塞运道,又希望利用黄河之水以补充运河,即既想“遏黄保运”,又想“引黄济运”。如正德、嘉靖年间的王车兀指出:“圣朝建都于西北,而转漕于东南。运道自南而达北,黄河自西而趋东。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而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11嘉靖末、隆庆初督理河漕的工部尚书朱衡也说:“古之治河惟欲避害,而今之治河又欲资其利。故河流出境山以北则闸河淤,出徐州以南则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桥四十余里间,乃两利而无害。”12明人正是根据这种避黄、用黄的双重愿望,一方面竭力防止黄河侵犯运河,特别是防止黄河北犯会通河,冲毁运道;另一方面又要不使黄河主流脱离徐州以南的运道,引黄河水以济运河。朱衡所谓“茶城以北,当防黄河之决而入;茶城以南,当防黄河之决而出”13,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明人的治河、治运实践证明,无论遏黄保运或引黄济运,都没有获得完全成功。景泰年间,徐有贞的治理沙湾,弘治年间白昂、刘大厦的治理张秋,都是由于黄河从河南境内改道北犯沙湾、张秋一带,冲毁会通河,阻断了漕运而引起的。为此,徐有贞指出,“必分黄河水,合运河,则可去其害而取其利。……开成广济河一道,下穿濮阳博陵二泊及旧沙河二十余里”,另用原有金堤、梁山泊的形势,以“使黄河水大,不至泛滥为害,小亦不至干浅,以阻漕运”14。对于保漕运道,潘季驯则认为:“为今之计,惟有修复平江伯之故业,高筑南北两堤,以灌两河之内灌,而淮扬昏垫之苦可免。”然后再采取措施保持淮南、淮北运道无虞,以使“黄淮二河既无旁决,并驱入海,则沙随水刷,海口自复”15。经过他们的先后治理,黄河北岸陆续修起了长堤,防止黄河北犯的目的基本上实现,但如何防止黄河冲毁徐州上下的运道,又不使徐州以南的运道因缺水而受阻,采取措施后没有多大效果,一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嘉靖以后,河患集中于徐州附近,运道不是为凶暴的黄河冲毁,就是黄河脱离了运河。“运道淤阻”,“徐吕浅涩”,“粮艘阻不进”等词在《明史·河渠志》中屡屡出现。治河者忙得焦头烂额,修堤防、堵决口、浚河道,下了许多功夫,但一直到明末,运河受阻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运河常受黄河干扰、破坏的事实,使明人逐渐认识到,另开新的河道,避开黄河,可能是保持漕运的一个办法,于是出现了另开新运道以避黄河之险的主张。
明嘉靖六年(1527年)黄河决于曹、单、城武等县,“冲入鸡鸣台,夺运河,沛地填淤七八里,粮艘阻不进”。当时,左都御史胡世宁鉴于河水“漫入昭阳湖,以致流缓沙淤”的情况,提出于“(昭阳)湖东滕、沛、鱼台、邹县间独山、新安社地别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过百余里。厚筑西岸以为湖障,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为河流散漫之区”的建议。七年正月,总河盛应期奏请朝廷采纳了胡世宁的主张,决定于昭阳湖东另开一条新运河。这条运河位于湖东丘陵边缘,地势较高,可避黄河冲淤之害。可是,工程只进行了一半,因旱灾,“言者请罢新河之役”,中途下马。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七月,黄河大决于沛县,“漫昭阳湖,由沙河至二洪,浩渺无际,运道淤塞百余里”。四十五年春,督理河漕的朱衡查勘河道,见“盛应期所凿新河故迹尚在,地高,河决至昭阳湖不能复东”,乃决计继续开凿,并“身为督工,重惩不用命者”。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新河成,西去旧河三十里”。“新河自留城(沛县境)而北,经马家桥、西柳庄、满家桥、夏镇、杨庄、珠梅、利建七闸,至南阳闸合旧河,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鲇鱼诸泉及薛河、沙河注其中,而设坝于三河之口”,“浚旧河自留城以下,抵境山、茶城五十余里,由此与黄河会”,“筑马家堤三万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遏河之出飞云桥者,趋秦沟以入洪。于是,黄水不东侵,漕道通而沛流断矣”16。这段运道后称“南阳新河”或“夏镇新河”。
新运河竣工以后不久,大批漕船即进入新河顺利北上,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据隆庆三年(1569年),出任总河的翁大立说:“新河之成胜于旧河者,其利有五:地形稍仰,黄水难冲,一也;津泉安流,无事堤防,二也;旧河陡峻,今皆无之,三也;泉地既虚,黍稷可艺,四也;舟楫利涉,不烦牵挽,五也。”17因为新运河好处很大,当隆庆三年七月黄河再决沛县,“茶城淤阻,粮艘二千余皆阻邳州时”,翁大立又提出开氵加河避开徐州上下黄河之险的新建议。但“黄落漕通”这一建议未付诸实施。万历三年(1575年)二月,总河都御史傅希挚再度提出“请开河以避黄险”的主张,也未实现。万历二十一年,总河尚书舒应龙在韩庄(山东峄县西南)开河,将茶城以北诸湖之水泄入彭河,下接氵加河。万历二十七年以后,总河刘东星继续整理氵加河,并在万家庄、台家庄、侯家湾、良城等“山岗高阜”之处,“力凿成河”;在韩庄以北“傍(微山)湖开支河四十五里”,工程进行了两年,以“地多砂(礓)石,工艰未就”18。不久,刘东星死去,万历三十年工程又停了下来。
在这一时期,周之龙对开氵加河以避黄通运进行了详细论述,他指出:“至氵加之役,亦自不可废者,按氵加河自邳州抵夏镇,凡二百三十里,中有微湖,北接汶泗诸水,南达沂沭诸河而诸泉夹注,原(源)远流长,实为徐邳木朵钥,且岸高土坚,又能束其流,无令滋漫。诚引泉水以达吕湖,引湖水以入氵加河,由宿迁出口与淮流接,可避黄涛之险,似于天造地设,当与故道并存。隆庆中,朱公衡建议请共廷臣熟计,嗣经言官屡疏下部覆得报可。会舒公应龙创开韩庄渠,分泄湖流,继以刘公东星督率诸臣,并力疏辟,业有成河矣,连年粮艘鳞次,多由往来,安可诧氵加无救於运?只缘河身所挑尚狭而浅,中有微山,攻凿未竟,正宜乘此未竟,殚力挑通。又开黄泥湾支渠,节缩湖流,筑塞旧漕,使水专一而不分。建竖坝闸,使水储蓄而不泄。倘不必借资黄水,而运道亦有备乎?顷者在廷诸臣,多韪其议,而或以为不可。盖诚见水衡日虚,河势孔亟,未免顾此失彼。且虑沙砾巨石,湖底版石,人力难施,是或一道。不知开韩庄山礓,不过数十里,凿梁城山渠,不过十数里,费金钱不过十数万。惮此数十里开凿之艰,而日与数千里黄河为难。惜此十数万之费,而岁置十百万于洪涛漭浪中。试一度之,难易自见。况设闸必须用石开凿,亦非虚糜。俟工有次第,或移利国驿于新开闸口。设司道官以综理沿河,乘时酌宜,经制备用氵加之役,毋亦运道便计乎!人有难于湖不可堤者,不知湖滨生地可循也。人有难于石不可泓者,不知泄水故渠可因也。人有难于水不易储者,不知节宣数闸可恃也。旧称六难,此捕风蹑影之难,非实见得难也。惟氵加一成,漕向滕峄郯沭而背徐邳桃宿,向者日渐纷华,则辗然喜,背者日渐寥落,则穆然嗟。以故勘氵加者,非溺于桑梓之其利,即移于编列之共灾,未臻厥成,惧者众矣。窃尝度之,胪为三策,有全弃黄河而创为新漕者,上也,浚氵加河是也。有半藉黄河而规复旧漕者,中也,闸正河是也。有从黄河之决而权为目前之漕者,下也,开徐之城南泄水支河是也。舍此三者,引河挽河无策矣。”19周氏此言道出了明末治河与治运者的共识,故不久就被实践所肯定。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河大决单县苏家庄及曹县楼堤,又冲沛县四铺口太行堤,灌昭阳湖,入夏镇,横冲运道”,进一步危及了漕运。刚出任总河的李化龙鉴于形势严重,主张继续大开氵加河,以竟前功。在李化龙的主持下,从万历三十二年开始,“上开李家港,凿郗山石,下开邳州直河口,挑田家庄”,经半年多的“殚力经营”,到八月即全线基本竣工。未完的尾工由后任总河曹时聘于万历三十三年完成。从此,又一条运河新线终于通航,“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余里,尽避黄河之险”,“运道由此大通”20。万历三十二年,漕船由氵加河新运道通过的已占2/3,万历三十三年通过氵加河的漕船达八千多艘。正如李化龙在分析氵加河新运道的优点时所说:“河开而运不借河(指黄河),有水无水听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氵加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善二;运不借河,则我为政,得以熟察机宜而治之,善三;估费二十万金,开二百六十里,比朱尚书新河事半功倍,善四;开河必行召募,春荒役兴,麦熟人散,富民不苦赔,穷民得以养,善五。”21经过这次改建,漕运状况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但是,明人避黄行运的目的直到明末也未完全实现,仍有近二百里的途程需要以河代运。大约过了八十余年,到了清康熙年间,在邳州以下开挖了中运河,再避黄河之险一百八十余里,除黄、淮、运交汇处外,黄河和运河基本脱离,以黄代运的局面才最终结束。
二、治理黄河与陵寝安危
明代治河除受到“保漕”这个最高原则的制约,要求既遏黄保运又引黄济运,从而在运借河道的情况下造成治河与治运交织在一起,加大治河复杂性以外,治河还受到“护陵”原则的影响。
朱明王朝的奠基者出生安徽凤阳,祖在淮泗,明皇陵在凤阳,祖陵在泗州。由于在明代绝大部分时间里,黄河借淮入海,故处于淮泗之间的泗州祖陵及淮泗以南的凤阳皇陵就常处于黄河频繁水害的威胁下。但是,在明前半期(洪武至弘治时期)因河患大多发生在河南开封附近,河患对归德、徐州以南的淮泗地区威胁不是很大,故在正德、嘉靖以前罕有提及保护陵寝事者。
弘治年间,黄河在河南境内的北岸、南岸堤防相继修成,加之黄河由颖入淮的河道又于嘉靖初逐渐淤塞,黄河河患发生于河南的已较少,而多移至山东和南直隶境内,黄河在归德以下、徐州以上多道分流,屡多决溢,淮泗之地逐渐成河患威胁重灾区。这样,自正德、嘉靖始保护徐州以南淮泗之地的泗州祖陵、寿春王陵、凤阳皇陵不受河患洪水冲溢就成为明代中后期治河的重大政治问题,“护陵”和“保漕”成为明代中后期治河的两大原则。但是,由于护陵要确保黄河南流不能过远,保漕要求黄河要在不淤塞运道的前提下济运通漕,这一南一北的两大限制使治河陷入政治、经济两大问题的苑囿之中,治河与治运、保漕紧密联系在一起,治河回旋余地狭小,腾挪空间不大,治河成效大打折扣。对这种情形,徐光启曾说:“夫漕之用河,河之梗漕,百年之前无有也。河稍南而遽以为伤地脉,虞祖陵,数十年以前无有也。”这就造成“今者绝河之中道,则河穷;又使之北避运,则河又穷;又使之南而远避祖陵,则河又益穷。河所由者,舍徐邳间三道安往哉?水穷则溢,何得不累岁决也?”22明人谢肇氵制在《北河纪》中说:“今之治水者既惧伤田庐,又恐惊陵寝;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钱”,“上护陵寝,恐其满而溢;中护运道,恐其泄而淤;下护城郭人民,恐其湮汩而生谤怨”。
受河患影响的凤阳皇陵、泗州祖陵和寿春王陵中,因“孙家渡、涡河二支俱出怀远,会淮流至凤阳,经皇陵及寿春王陵至泗州,经祖陵。皇陵地高无虑,祖陵则三面距河,寿春王陵尤迫近”23。实际上也是如此,祖陵、寿春王陵遭河患可能性大得多。“祖陵在泗州城东北相距一十三里,西北二面,土岗联属,水莫无虞,其南面山岗之外,即俯临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汇于此沙。湖之南为淮河,自西而来,环绕东流。去祖陵一十三里,惟东面冈势止处,俯临平地,有汴河一道,远自东北而来,上有塔影、芦湖、龟山、韩家、柯家等湖及陵北冈后沱沟之水,俱入于汴河。但遇夏秋淮水泛涨,则西由黄冈口,东由直河口,弥漫浸溢,与前项湖河诸水通连会合,间若蔞及冈足,及下马桥边”24。正因泗州祖陵、寿春王陵所处的这种地理环境,故屡有受淹之虞,而明代治河之“护陵”原则实是护祖陵、王陵为主,“至于凤阳皇陵,则尤居高阜,地势悬绝,二百余年,未闻有议及者矣。(潘季)驯谓不必虑者如此”25。正德十二年(1517年),大水异常,涨至泗州祖陵陵门,“遂浸墀陛,则旷百年而一见也”。这次水冲祖陵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陵寝安危被当作事关社稷的根本大政,明代治河由此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过去的“保漕”为主转而为“护陵”、“保漕”并重。从嘉靖朝开始为“护陵”而进行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将黄河于野鸡岗上流李景高等口开挑支河三道,借引水利,又卷埽筑坝一道,逼水东注以济二洪,以杀南奔之势。其泗州祖陵,再筑墙垣,凤阳白塔、寿春等王坟,重筑土堤,并填实李家沟,别引龙子河浅水入淮……于祖陵东面出水之地,筑堤为闸,因时启闭”;又于白塔王坟、寿春王坟“增筑石堤,补栽荆柳”等26。经过大规模整治,陵寝安全性大为提高,但提幅地黄河屡决于淮泗,陵寝安危未从根本上得到解除。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河决丰县、孟津、夏邑,“及野鸡岗之决地,凤阳沿淮州县多水患,乃议徙五河、蒙城避之。而临淮当祖陵形胜不可徙”。为解除对祖陵的威胁,乃“浚砀山河道,引入二洪,以杀南注之势”。此后河患一直威胁陵寝,但整个嘉靖时期没有直接冲溢陵寝。到万历时,陵寝则屡遭直接威胁与冲害。万历十九年(1591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淹三尺,居民沉溺十九,没及祖陵”。二十年(1592年)三月,“水势横溃,徐、泗、淮、扬间无岁不受患,祖陵被水”,“泗城如水上浮盂,盂中之水复满,祖陵自神路至三桥、丹墀,无一不被水”。到了万历二十二(1594年)年,祖陵外的二湖堤尽筑塞,而黄水大涨,清口沙垫,淮水不能东下,于是挟上源阜陵诸湖与山溪之水,暴浸祖陵,泗城淹没,从而酿成明代水利史上的一大灾难27。这次泗州城及祖陵被水淹的情况周之龙叙述说:“河复大为患,决汶上,决鱼台,决济宁巨野,决邳州宿迁高邮,泛涨泗州几成鱼鳖之乡。祖陵松柏,槁于水过半”,以致“郁郁祖陵,蛟龙将驰”。为此万历帝赫然震怒,屡易河臣,“河臣刘公东星竟以忧殒,上复赫然震怒,切责大司空”28,并连简河臣李顺、鲁如春抓紧治河保陵安全。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分黄导淮之议而起。
万历二十三年(1593年),总理河道的杨一魁与礼科给事中张企程共同提出“分杀黄流以纵淮,别疏海口以导黄”的建议,然后施工,“分泄黄水入海”,“分泄淮水东经里下河地区入海”。“于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扬安矣”29。与此同时,有些大臣则提出:“于今计,与其先事于杀淮,则不若先事于分黄;与其分黄于既合淮之下,则不若分黄于未合淮之上;与其暂分而使之复合,则不若永分而听其自去;与其仅分其支流,则又不若全分大河而使之各入于海。至论分黄于未合之地,则又不当就其远且难者,而当就其近且易者,庶几内不病陵,外不病漕,而中不病役。”30分黄导淮的方案实施以后,暂时解除了对祖陵的威胁,但由于黄河泥沙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泗州祖陵受淹仍是不可避免的事。万历时给事中吴应明言:“先因黄河迁徙无常,设遥、缕二堤束水归漕,及水过沙停,河身日高,徐、邳以下居民尽在水底。今清口外则黄流阻遏,清口内则淤沙横截,强河横灌上流约百里许,淮水仅出沙上之浮流,而渚蓄于盱、泗者遂为祖陵患矣。”31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秋,河涨商丘赵家园,淤塞断流,决萧家口,全河奔溃入淮,势及陵寝。“帝以一魁不塞黄土固口,致冲祖陵,斥为民”32。陵寝安危直到开运河新道,使运河不再完全借黄通运后才有好转,“氵加河成,则他工可徐图,第毋纵河入淮。淮利则洪泽水减,而陵自安矣”33。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通过氵加河的运河工程全部完之后,不再完全借黄济运,治河受漕运制约较小,回旋余地增加不少,这就为治黄与治淮留下了空间,而氵加河开后河水北流增加,减少了入淮水量,对陵寝安危具决定影响的淮泗之水害大为减轻。这样直到明亡,虽然水害频频,陵寝没有受到直接冲毁。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黄河决口,“伏水大涨,故道沙滩壅涸者刷深数丈,河之大势尽归于东,运道已通,陵园无恙”34。明代中后期治河深受“护陵”这一政治原则的影响,为此统治阶级不惜采取筑堤、分流泄洪、建闸坝,乃至为保陵寝而逼水淹别处的一系列做法,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这些措施基本上保证了一百三十余年时间里陵寝少受水患冲击,客观上有利于淮、泗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实现了明王朝的政治利益。但是,“护陵”原则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们治河的能动性与客观性,不利于从全局把握以获取较大利益,减少损失。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根治也不太可能根治黄河泥沙问题,护陵的措施多是应对措施,疲于应付,鲜有科学的创新性的工作,当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有较大效果,运河新河开通基本解决陵寝安危时,明王朝已病入膏肓,回天乏力了。总之,明代“护陵”政治因素制约了治河,得不偿失,明王朝中后期的治理黄河始终也没有跳出“保漕”与“护陵”的两难窘境。
① 《明经世文编》引《支华平先生集》。
②④⑧101316182023272931323334《明史·河渠志》。
③ 《明史·食货三》。
⑤⑦ 《明史·宋礼传》。
⑥ 《行水金鉴》引《明太宗实录》。
⑨ 《明史·陈王宣传》。
11《明经世文编》引《王司马奏疏》。
12《行水金鉴·河水》引《明穆宗实录》。
14《明经世文编》引《徐武功文集》。
15《明经世文编》引《宸断大工录一》。
1721《行水金鉴·运河水》引《明穆宗实录》。
1928《明经世文编》引《周司农集》。
22《明经世文编》引《徐文定公集四》。
242526《明经世文编》引《宸断大工录三》。
30《明经世文编》引《黄中丞奏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