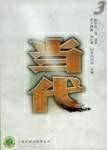宝岛诗踪
屠岸
拥抱
从桃园机场到小港机场,
鲜花和泪花相继开放。
是初次会见?是老友重逢?
我像是首次来拜访故乡。
学术研讨会舌锋铿锵,
剖示女性诗深刻的蕴藏。
两岸的交流似和弦、变奏,
大厅里交响曲激越而悠扬。
血浓于水的亲情呵高涨,
民族大团结至高无上;
日月潭波平,阿里山林密,
呼着昆仑雪,喊着太湖浪。
九个昼夜呵比百年更长:
难分的拥抱永刻在心房!
五个兄弟民族的女诗人
来到宝岛上明朗的大厅,
民族的服饰争鲜斗妍,
生动的语言沟通心灵。
五个姊妹民族的女诗人
来到宝岛上美丽的园林,
到处是同胞的开怀体贴,
时刻都感受到手足情深。
藏歌和彝歌响遏行云,
马头琴衬托着草原恋情。
诗艺的切磋,诗学的探讨,
紧紧牵系着两岸的诗心。
女诗人向缪斯祈祷虔诚:
愿海峡是腰带而不是斧痕。
同心圆
能否借用你开幕词的这个题目?
十二亿人民在同心圆里面繁衍。
圆轨的一脚在黄河浪峰里站住,
另一脚画一道弧线,拥抱着台湾。
你的致词比赞美诗更加动听,
抑扬顿挫间激情和豪情喷涌。
五千年血胤驾著九万里祥云,
来到同心圆会场听你的吟诵。
你笑着,提纲挈领又高瞻远瞩,
祝祷着冰河解冻和铁树开花。
会场上唇舌交锋,如火如荼,
弘扬诗艺的纪念牌大放光华。
五千个年轮围绕着圆心旋转:
诗韵把两岸的山水连成了一片。
台北寻踪
走下舷梯,脚踏上桃园机场,
哦!来到了你住过几十年的地方。
台北市曾经是你的第二故乡,
我欲寻踪,却不知你原住的街巷。
三妹说,这里拆迁过大批旧房,
二姐的老屋肯定已不知去向。
我往哪儿找?连路名都不知其详,
我只好沿着菩提树在街上彷徨……
你可曾到故宫博物院观赏宝藏?
你可曾把脚印留在阳明山道上?
不,你屡屡在生活的重击下负伤,
哪有心思到竹子湖去轻舟荡桨?
你如今面对着南加州最后的夕阳,
我遥望太平洋洪波,烟水苍茫……
日月潭
面对能高山、背靠玉山的大泽,
天庭如日轮、颔如月弧的水乡;
一片浩淼吞吐着空┑纳缴,
雨丝如细帘给湖水披上淡妆。
泽畔文武庙供奉关帝和岳王,
至圣先师俯瞰水云宫双殿。
一群群善男和信女膜拜焚香,
万顷碧波护套膨敬的祈愿。
甜水哺育原住民邵族的繁衍,
特有的艺术蕴含精巧和纯朴。
德化社原始崇拜的木雕惹眼,
九族文化村招引诗人的眷注。
我站在岸边凝望安静的烟水,
祝福西子的姐姐、湘灵的妹妹。
萱草
萱草,萱草,我藏在心中的忘忧草;
萱堂,萱堂,我永远怀念的亲娘。
母亲想外婆,把画室命名为萱荫,
我思念母亲,让萱荫做我的书房。
画室的墙上挂着“萱荫阁”匾额,
书房的桌上摆着“萱荫阁”图章。
品尝过金针菜无比纯真的甘美,
却不曾见到过萱草生长的模样。
我曾经询问过朋友,想一见萱草,
始终没如愿。我责备自己的荒唐。
突然,在彰化民俗文化村植物园,
一大片萱草在我的眼前放绿光。
扑上去,抱住它!感谢宝岛为我
提供了与母亲灵魂相会的地方。
阿里山夜市
没月光,电炬照明在一条街上,
玻璃柜内外,小商品满目琳琅。
姑娘端出乌龙茶,让免费品尝,
大嫂指著露珠茶,称品种优良。
向一位售货的少女问这问那,
她都含着笑耐心地一一回答:
“日月饼皮子是面粉或地瓜加麦芽,
里面是栗子馅,尝尝吧,味道顶呱呱!
“山葵粉,樱花果,芭乐干,特产样样好……
您又问又记,是记者?要拿去登报?”
“他要写一篇文章回大陆去发表。”
“太好了,可别把我们的店名漏掉。”
我抬头看招牌,哦,阿里山真奇妙:
“大统一商店”,五个字金光闪耀。
职权里山观日
黎明迟迟地出现在林梢,
观日楼座椅上人语悄悄。
雨帘罩住了一湖白雾——
起伏的雾波,汹涌的雾涛!
五点三十分早已来到,
睁眼望东方,盼得心焦。
只有雾浪漫过大森林,
不见太阳金色的闪耀。
天光寸寸亮,焦虑阵阵消,
且由我观赏滚滚的雾潮。
凭栏不再等旭日高升,
只惊喜于林雾美妙的舞蹈。
你撑伞挽著我走下楼桥,
穿过了雾穴,进入了雾坳……
阿里山森林火车
乘火车向深山寻踪前进,
窗外是影影绰绰的森林。
白雾用柔指抚摸著车窗,
火车缓缓地驶进了灵境。
山樱、吉野樱漫山遍野,
红桧和巨杉沿石坡阵列,
幽径的一侧绣球花斜倚,
大树根指向姊妹潭亭榭。
三兄弟,四姊妹,永结同心,
三代木,象鼻木,错节盘根;
从梅园寻觅到神木群巨雕,
始终没见到你的娉婷。
一幕幕梦幻在车窗上掠过,
灵境的追踪长牵在心窝……
阿里山姊妹潭
姐姐和妹妹爱上了同一个少年郎,
姐姐让妹妹;妹妹当上了新娘。
妹妹自责,觉得对不起姐姐,
满怀悔恨,投身于小潭的中央。
姐姐得悉妹妹为自己而身亡,
忧伤地谢绝登上妹夫的婚床。
姐姐自责,觉得对不起妹妹,
满怀悔恨,投身于大潭的中央。
泪水在一株株红桧的脸上流淌,
一条条山溪把悲哀的悼诗吟唱;
我踏著苔径来凭吊姊潭和妹潭,
见一片白雾弥漫着白色的哀伤;
两潭水紧连,潺潺地诉说著相让;
凄美的双魂依然在潭上彷徨……
嘉义吴凤庙
整排椰子树威武地守卫著山门,
红墙飞檐下延伸著草地石径。
碑亭前院子里伫立著苍松翠柏,
殿中的塑像宣示著杀身成仁。
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一日这一天,
闽籍的朱衣老人殒命在诸罗县。
通事的惨烈壮举呵感天动地,
杀人祭神的恶习革除于一旦。
番汉的和睦给台湾带来了安定,
仁者的义行受到了永世的崇敬。
今天有“学者”想否认吴凤的事迹,
以疏离大陆和宝岛的血肉亲情:
虚伪的考证抹不掉铁的史实,
为分裂帮腔只能絮叨于一时!
〔附记〕一九九九年七月,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诗人访问团团长,应台湾中国诗歌艺术学会的邀请,率团访问台湾。七日,到嘉义市吴凤庙,下车拜谒。吴凤,福建漳州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一六九八年),约于十六岁时随亲人移居台湾诸罗县(今嘉义市)。二十四岁时,任通事一职。其时,原住民山胞恨汉人迁入,不时出草杀汉人以祭神。前任通事与山胞有约:每岁供给汉族男女二人以为牺牲,使不再侵扰。吴凤任通事后,立志革除此恶习,遂苦口婆心,谆谆劝导,经多年教化,山胞同意不再杀戮汉人,历四十余年。一年,山地瘟疫蔓延,加之邻社仍流行上述恶习,山胞中之年轻者誓欲恢复杀汉人以消灾。吴凤度势不能免,但身为公务者,若不能安定地方,则愧对社稷。于是许约山胞于某日有一衣朱衣戴红巾者走过某地时可杀之以其头祭神。山胞如约,割下人头,方知是吴凤本人。是时乃乾隆三十四年(公元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一日,吴凤年七十一岁。酋长粤哥等悚惧感悟,遂邀约阿里山四十八社头目集会,宣布从此不再出草杀人,并设坛祭谢吴凤,各社埋竖圆形巨石,以使后世子孙代代遵守。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杀人祭神的恶习自此而一旦革除,汉人与山胞和睦相处至今日。台湾民众为纪念吴凤舍生取义之厚德,立庙祀奉,香火岁岁不断。据同行的台湾朋友告知,近年来“台独”主张者张扬分离主义和“本土化”,个别“学者”进行“考证”,企图否认吴凤及其事迹,目的在疏离大陆与台湾的历史联系。呜呼!其居心叵测,其目的不可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