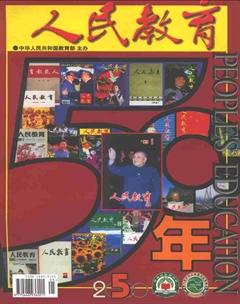校园两忆
肖复兴
阎老师
阎述诗老师,冬天永远不戴帽子,这曾是我们汇文中学的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景观。他的头发永远梳理得一丝不乱,似乎冬天的大风也难在他的头发上留下痕迹。
阎述诗是北京市的特級数学教师,这在当时我们学校数学教研组里,还是惟一的。学校里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校长对他都格外尊重。他只教高三毕业班,非常巧,我上初一的时候,他忽然要求代一个初一班的数学课。可惜,这样的好事没有轮到我们班。不过,他常在阶梯教室给我们初一年级的学生作数学课外辅导,谁都可以去听。他这样做,不仅为了我们学生,同时也是为了年轻的老师。他想把数学要从初一开始抓起的重要性,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给大家。
我那时并不怎么喜欢数学,可还是到阶梯教室听了他的一次课,是慕名而去的。那一天,阶梯教室坐满了学生和老师,连走道都挤得水泄不通。上课铃声响的时候,他正好出现在教室门口。他讲课的声音十分动听,像音乐在流淌;他板书极其整洁,一个黑板让他写得井然有序,像布局得当的一幅书法、一盘围棋。他从不擦掉一个字或符号,只要写上去了,就像钉上的钉,落下的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随手在黑板上画的圆,一笔下来,不用圜规,居然那么圆,让我们这些学生叹为观止,差点儿没叫出声来。
45分钟一节课,当他讲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下课的铃声正好清脆地响起,真是料“时”如神。下课以后,同学们围在黑板前啧啧赞叹。阎老师的板书安排得错落有致,那从未擦过一笔,从未涂过一下的黑板,满满堂堂,又干干净净,简直像是精心编织的一幅图案,同学们都舍不得把它擦掉。
是的,那简直是精美的艺术品。我还从未见过其他老师能够做到这样。阎老师并不是有意这样做,而是已经形成了习惯。后来,我回母校还见过阎老师的备课笔记本,虽然他的数学课教了那么多年,早巳驾轻就熟,但每一个笔记本、每一课的内容,他都写得依然那样一丝不苟,像他的板书一样,不涂改一笔一画,哪怕是一个圆、一个三角形,都用圆规和三角板画得规规矩矩,而且每一页都布置得整齐有序,一个笔记本就像一本印刷精良的书。可见,阎老师是把数学课当成艺术来对待的,所以他把数学课便化为了艺术。只是刚上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其实就是一位艺术家。
一直到阎老师逝世之后,学校办了一期纪念阎老师的板报,在板报上我见到诗人光未然先生写来的悼念信,信中提起那首著名的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方才知道是阎老师作的曲。他原来如此学艺广泛而精深。想起闾老师的数学课,便不再奇怪,他既是一位数学家,又是一位音乐家。他将音乐中形象的音符和旋律,与数学的符号和公式,那样神奇地结合起来。因为他拥有一片大海,给予我们的才如此滋润淋漓。
那是1963年,我上初三,阁述诗老师才58岁,他太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是患肝病离开我们的。肝病不是肝癌,并不是不可以治的。如果他不坚持在课堂上,早一些去医院看病,他不至于这么早就走的。他就像唱着他的《五月的鲜花》的战士,不愿离开自己战斗的岗位一样,不愿离开课堂。从那一年之后,我再唱起这首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便会想起阎老师。
就是从那时起,我对阎述诗老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以他的才华学识,他本可以不当一名清贫的中学教师。而且,艺术之路和仕途之径,都曾为他敞开。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日本教官接管了学校后曾让他出来做官,他却憤而离校出走,开一家小照相馆艰难度日谋生。解放初期,他的照相馆已经小有规模,凭他的艺术才华,他的照相水平远近颇有名气,收入自是不错。但是,这时母校请他回来教书,他二话没说,毅然放弃商海赚钱生涯,重返校园再执教鞭。一官一商,他都是那样瘐快挥手告别,惟有放弃不下的是教师生涯。这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做得到的。人生在世,诱惑良多,无处不在,都一一考验着人们的灵魂和良知。
我对阎述诗老师的人品和学品愈发敬重。据说,当初学校请他回校教书,校长的月薪才90元,而他却经市政府特批予他月薪120元,实在是得有其所,也说明他的德高望重。
世上有许多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阎述诗老师一生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白日教数学,晚间听音乐,手指在黑板与钢琴上均是黑白之间,相互弹奏;两相契合,物我两忘,陶然自乐。这在物欲横泛之时,阎述诗老师能守住艺术家和教育家的一颗清静透彻之心,对我们今日实在是一面醒目明澈的镜子。
诗人早就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想想抗战胜利都50多年了,《五月的鲜花》唱了整整有半个多世纪,却依然在整个中国的大地上回荡。岁月最为无情而公正,半个多世纪呀,会有多少歌、多少人被人们无情地遗忘!但是,阎述诗老师和他的”五月的鲜花》仍被人们记起,这就足够了,他死了,他却永远活着!
我在母校纪念阎述诗老师的会上,见到了他的女儿,她是著名演员王铁成的夫人。她告诉我,她的女儿至今还保留着三十多年前外公临终前吐出的最后一口鲜血——洁白的棉花上托着一块玛瑙红的血迹。
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与从自来水管里流出的水,终究是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历史。
那块血迹永远不会褪色。那是五月的鲜花,开遍在我们的心上。
田老师
田增科老师到澳洲去了。这是他第三次去那儿了。我隐隐地感到,这一次去,他大概不会再回来了。因为他的两个孩子在那里,另一个孩子在意大利,国内已经没有他的亲人了。几个孩子在国外干得都不错,执意要接他们老俩口出去,尽尽孝心。起初,田老师只是想到国外走走看看,都是短期行为,但这一次恐怕是要留在澳洲了。
我忽然觉得非常落寞。在偌大的北京,我没有任何亲戚,连八杆子打不着的都找不到一个。田老师,已经算是我在北京惟一的亲戚了。我和他交往有37年了,过了我的人生的一半,也过了田老师的人生的一半。岁月,让人的感情发生着变化,就像葡萄在时间的催化下能变成酒一样,浓郁芬芳醉人。
那是37年前,我在汇文中学上初三,田老师教我语文。那时,我15岁,田老师刚刚大学毕业,我们便开始了这长达37年的交往。这中间,是他帮助我修改了我的一篇篇作文,并亲自推荐我参加了北京市少年作文比赛,并获得了一等奖。那是我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篇文章,我会那样迷恋上文学吗?我今天的道路会不会发生变化?我有时这样想,便十分感谢田老师。我永远难忘他将我的那篇作文塞进信封后,又小心地投递进学校门前的绿色信筒里的情景;我也永远难忘当我的这篇文章被印进书中,他将那喷发着油墨清香的书递在我手中的时候,他那比我还要激动的情景,那是一个细雨飘洒的黄昏。
这中间,还横躺着一个“文化大革命”。说来我当时也许真是十分的可笑,我自以为自己才是革命的,而认为田老师当时有些保守,因为我们当时参加的并不是一个战斗队。有一段时间,我和田老师疏远了。可是,在我要到北大荒插队的时候,我原以为田老师不会来送我了,然而,田老师却面带微笑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在那些路远天长、心折魂断的日子里,田老师常有信来,一直劝我无论在什么样艰苦的条件下,千万不要放下笔、放下书。在那文化凋零的季节,他千方百计地为我买了一套《水浒》和一套《三国演义》,在我回京探亲结束要回北大荒的前夕,他赶到我的家里把书送来。那一晚,偏巧我出去和同学话别没有在家,徒留下桌上的一杯已经放凉的茶和漫天的繁星闪烁。
这中间,我和田老师先后都结了婚。他生下两女一子,我生下一个儿子。在那段一根扁担挑着老少两头的艰辛的日子里,我待业在家没有工作,他鼓励我别灰心,并借给我他的《苕溪渔隐从话》《中国画论辑要》《人间词话》《红楼梦》等书。他还送我一个笔记本,劝我再苦再难,读书是必要的,要相信艺不压身,学问终有需要的时候。
这中间,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他看后觉得不错,亲自骑上自行车跑到报社替我送到编辑的手中,并郑重地推荐给人家的。那篇文章,他至今保留如初,并保留着我中学的作文本。
这中间,他出版的第一本书,特意约我来写序言。我说:“这本书中的这些篇章并不是为文而文,而是一位老教师在和你坦率真挚地谈心。悠悠读来,我仿佛又回到学校,重温了坐在教室里听田老师讲课的那一片温馨,它曾伴我度过少年而渐渐长大。
这中间,我和田老师一样,当上了中学和大学的老师。在我刚开始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田老师曾经骑着自行车到学校专门听我讲课。我任教的中学在郊区,比较远,但他还是早早就到了。听他的学生要给更为年轻的学生讲课了,他的心情显得有些激動。后来,有次他到我教书的中央戏剧学院来听我讲课,我讲的是朱自清的《背影》。下课后,他告诉我文章中的一个字我给读错了。另外,除了应该结合朱自清先生的自身经历,还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讲述文章,会对文章的内涵理解得更深刻些。我感激地送他一直走到学院门口,看着他骑上车在冬天的风中远去,一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为止,我才发现自己的手中拿着的正是朱自清的《背影》……
37年的岁月就这样如水长逝。可以说,我和田老师这37年的交往,是读书写书的交往,清淡如水,却也清澈如水。由书滋润着情感,又由情感滋润着书,便也格外湿润而清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或值得保持37年的友情的。人生中,萍水相逢的、利害相加的、关系互通的人,总是不少。但我和田老师却是这样平淡又长久地保持着这样一份感情,让彼此都感到那感情中因有岁月的沉淀而显得那样沉甸甸的。这偌大的北京城中,由于我没有任何亲戚,我便把田老师当成了惟一的亲戚。在舂节老北京人讲究亲戚之间互相看望的礼节里,我惟一要看望的就是田老师一个人。
一晃,春节将要来临。田老师却到澳洲去了,而且不会再回来了。春节,我将无处可去。
我想起前年的春节,田老师当时也不在北京,正在澳洲女儿的家中。他特意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夹有一张他在女儿家门前照的照片,照片后面有田老师抄的一句清诗:“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一下子,遥远的澳洲变得近在咫尺,田老师又像坐在我的身边了。而且,那时总想这个春节田老师不在,下一个春节他是要回来的。毕竟他还想着那么多要读的未完之书。
可是,这一次,田老师不会再回来了。他早早寄给我一张贺卡,贺卡上印着积雪覆盖的原野。接到贺卡那天,北京正纷纷扬扬飘飞着冬天以来最大的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