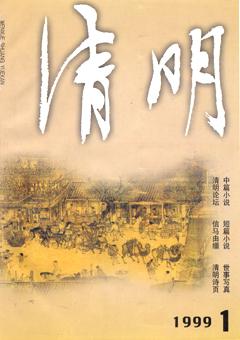怀念吴树声叔叔
孙 禹
读着父亲从老家合肥,寄到德国的纪念吴树声叔叔的悼文,我的手禁不住微微颤抖。我一向自诩是一个“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七尺汉子,竟然被泪水模糊了视线。当我逐字逐句读完父亲这篇深情的文章时,我周身的感官,仿佛被一把金色小号所奏出的苍凉而孤独的旋律所笼罩。倏地,吴叔叔那张清癯而充满个性的脸以及略显消瘦的整个形体,被雨后那绚丽缤纷的彩虹簇拥着,款款向我走来。于是,在我那幽静和沉睡的记忆深处,便涌起一股柔和、典雅的温泉……
那是一个对我来说能否成为一名军人,便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年代。种种原因我在父亲几乎跑断腿的奔波中,还是与当兵无缘。一天,我母亲告诉我,福州军区文工团来合肥招文艺兵,吴叔叔向他的战友(带兵人)力荐我。记得那是在省军区招待所,面对着几个高大威猛的准军人,我竟然毫不怯场。隐隐约约之中,总觉得身后有吴叔叔的面影,还有他带着浓重胸腔共鸣的山东口音:“小禹,你行!我是不会看错人的。”我浑然不知,他在何时便开始用这种肯定的语气,已经在为我设计了我未来的歌唱生涯了。自然也无从考察,他凭什么便单方面认定,我将别无选择地得靠我自己“雄狮怒吼”一般的嗓音唱遍天下。那时,他是我母亲所在编辑部的主任。在他初次用不容否定的口吻向我母亲宣称,我有一副超人之嗓音时,连我母亲都有些惊诧:亲生儿子这般过人的资质,竟然自己都并未给予重要的关注和及时发现?!
那时,我在梦里都渴望做一名军人。面对着我膜拜的、来自福建前线的军人,我唱了也是样板戏中的军人咏叹调:杨子荣的“甘洒热血写春秋”。我初次被自己从墙壁上反弹回来、带着金属般的声音惊呆了。继而更诧异的是,一曲唱完,来自前线的军人竟呆若木鸡,久久凝住似地。一周之后,我母亲告诉我:“人家看上你了,死活要带你走!”于是,我就再也睡不踏实。一闭上眼睛便是:军装、营帐、“北洋水师”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仿佛歌唱要入另册,战死僵场才是无愧生命的一种永恒和唯一归宿。不知怎地,此事尤如一阵夜风掠过,便再也没了下文。我在稀里糊涂的盼望和等待中,渐渐被痴迷美术和排球摄走了心魄。“为国捐躯,战死疆场”的壮怀激烈,随着家人和吴叔叔都不再提及,恰似一片远去的云,渐渐飘逝了。后来,似乎听我母亲含混地提及:是她再三斟酌,放弃了让我去当兵的选择。后来的日子,别的都已淡忘,但冥冥之中,吴叔叔那般无比坚定的确认,我终将能成为一个歌唱家的信念,仿佛一个不灭的信号,在我的潜意识中闪闪失失,似乎是扎下了根。他的确认,之所以在我的心目中能构成权威性,那便是在我父辈口中他是演过革命歌剧的。至于歌剧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和文艺载体,我毫无经历,更没有常识。只是觉得能唱歌剧的人很了不起。在我当时的概念中,歌剧应该不同于庐州府的“刀七戏”和安徽有些文人墨客们为之骄傲得似乎有些颠狂的“黄梅戏”。歌剧抑或是要有“真玩艺”和“动真家伙”的吧?!
“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二年,弟弟孙国庆首先戴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徽。那时,“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徽标志着在我们那个以旅游胜地黄山的闻名遐迩、古井贡酒的如雷贯耳和徽菜传统的耀祖光宗,远比科技和人文素质是否执全国之牛耳更为重要的农业大省里,竟有西洋音乐人才的存在。望着在我眼前晃动的校徽,我心里交织着一种复杂的感觉。因为那时十八九岁的我,正是马鞍山市话剧团的一名学员。我的偶像并不是李双江、刘秉义、夏利亚宾和保罗·罗伯逊。而是金山、于是之和李仁堂、邦达尔丘克……西洋音乐对我尤如夜空中两颗相隔极其遥远的星座,相安无事,永世不会相撞。然而,每当我在楼道里走着,便被那共鸣极佳的回响诱惑着,时而唱性大发。这时,吴叔叔便像一个幽灵出现在他家门口,微笑而执着地对我说:“你应该去考中央音乐学院!”他那种比我自己更明确而自信的神态和口吻,常常让我汗颜和局促不安。因为那时的我不仅不识简谱,而且常被习大提琴多年的弟弟称为:“柬埔寨”即“简谱债”之外,所会哼哼的歌曲几乎均是听会和顺着收音机模唱的。并且,一首歌断然是从头唱不到尾的。吴叔叔似乎并不在乎这些,我每次唱着经过他家,他竟是如此固执和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那坚定不移的、对我的厚望。再后来,当他的这种由不得我不重视的“固执己见”又受到其他几位专业人士的共鸣时,我只有揣着茫然和猎奇的心思北上赶考去了。既便是在北去列车上的不眠之夜,还是徘徊在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这三所大学之间,在我所编织的梦中,仍绝无能被音乐学院歌剧系录取,并在将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歌剧演员的半点感应。在我收到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告别马鞍山话剧团,回到合肥重见吴叔叔时,他并没有为自己的神掐妙算得以兑现而有丝毫的得意之色。只是仍旧用那种绝对有把握的口吻对我说:“你妈妈给我们编辑部发的喜糖,我吃到了。好好学,你能成,也应该成!”在那个岁月中,我母亲的编辑部里的同事们经常互发喜糖。五年之后,我在毕业公演的西洋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饰伯爵。那时,我突发奇想,假如我的将来,也能练就此种“三年早知道”的特异功能的话,岂不也成了奇人了吗?!自然,那时的国人为了长命虽对气功和特异功能尚未有足够的悟性,但是清晨即起大灌凉水、甩手疗法、猛喝鸡血、纵饮红茶菌等等,倒也是如痴如醉,趋之若鹜。
人与人之间,是否确有“缘份”存在?我从未认真品味。但后来,在我生命中太多的“奇事”发生,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和琢磨这所谓“缘份”二字。也许是吴叔叔第一次听到我“吼叫”的嗓音后,他便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郑重其事、宣读国书一般对我母亲说:“你儿子,学美术虽刻苦,但没有过人的才华。付出再多,收效不大。但我敢肯定,他的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的歌唱家!”在我母亲有意无意将她主编的话在饭桌上,随意而不甚连贯地透露出来之后,我心情的失落和怅然,孤独和无告,绝不亚于今天。每当我失意时,独自漫步于异国都市里,那些被黄昏笼罩、被教堂枯索的钟声所淹没的大街小巷中……我告别了我省大画家鲍加叔叔家里那间充满了油画芬芳的画室,在还来不及缓过神来,重新给自己定位和选择的彷徨中匆匆埋葬在雪地里、在柳絮中、在三伏天的日日夜夜里,梦想成为列宾和达芬奇一样的油画大家,也为自己留下一幅“伏尔加船夫曲”和挂着永恒微笑的蒙娜丽莎。从那时起,就以“倔”而出名的我,便无法躲避对吴叔叔的好奇。我不仅偷偷从父亲已封存的书架上,翻出在“文革”中他那被打成“叛徒哲学”的长篇小说《在狱中》细读,甚至常常在人家写批斗他的大字报以及他反击的大字报栏前驻足。欣赏着他那笔走龙蛇、力透纸背的书法……连我自己也很奇怪,从那时起,吴叔叔的言行就常常让我比他人更为重视。不知从何时起,我就已经将他视为一个与我很有关连的人了。毕竟他的观点和对我的判断,不仅对我本人,甚至对我父母都有很大影响。因为,在当时的文联大院里,吴叔叔无论书法、绘画、文章和歌唱,是少有人可以与他相比的。况且他还有一位画技更精的夫人顾美琴女士。直到今天,我在欧
州的这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北方的城市里,读着我父亲的文章,才知道吴叔叔身上如此之多的才艺竟大多都是自学而成的。锱铢积重,冰冻三尺。一个人靠自研自学便能成就如此这般造化,在我的心中,不啻是要被永远地敬重的。
吴叔叔在我从艺的道路上,以他不容抗辩的固执拨正了我人生中的偏差,让我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从那以后,每每再见他那双微笑的双眼时,仿佛便有了许多哲学的味道了。它们仿佛在重复着这样的哲言:“艺术是需要有天资的。假如一个人在某项艺术事业的选择上天资不足、才能不够,只有自寻烦恼。如同一艘马力不足的驳船,是无法和远洋巨轮相比拟的。”但是,在我五年的音乐学院歌剧系的学习和深造过程中,我并未将那种被纠正偏差、焕然一新的生命动力,全部投入到如何使一个中国的夏列亚宾早日诞生的奋斗中去。更不幸的是,大学五年中,我又染上了至今不治的“文学痴呆症”。记得有一年暑假的一个晚上,我为了写作不至汗湿稿纸,在我母亲编辑部同事下班后,躲将进去,反锁上门,在房顶上悬着的那个吊扇下,嗅着“编辑爷”改稿用的墨汁香和臭味,开始了我的文学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约莫十一点钟,编辑部的门被打开了,吴叔叔走了进来,我忙着要站起来。他似乎对我借用编辑部写稿又是“三年早知道”。他挥了挥手让我别动,告诉我忘了一篇未及审看的稿子。突然,他的双目似被火焰灼烫一下圆睁起来。紧紧盯住我手中食指和中指间夹着的一根香烟,足足有五六秒钟凝住不动。过了一会,他缓缓抬起头来,目光如同一把刀子,锐利地在我脸上剜着。他嘴巴嚅嗫着确乎想和我说点什么,但不知为什么却感到十分艰难。我下意识地将那还有半截子的烟掐死在烟缸里。在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口时,我实在地觉得,他整个人在被一种很严重的失望心绪压迫下,变得缩小了许多。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每逢写作依然还要吸烟。已经早已戒烟并以写作为生的父亲,为劝我不要吸烟道理说尽,狠话说绝,但我依旧不改。吴叔叔仍旧细心去发现和培养一个又一个年轻作者的同时,也发表我的习作。但我发现,在我后来回家度假的几个夏天里,吴叔叔注视我的目光中,便凭添了几许耐人寻味的内涵。多少年过去了,一个月光如练的仲夏之夜,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一个华人为我独唱音乐会成功所举办的聚餐会上,一位冯玉祥将军的后裔递给我一张图片,上面排列着三个不同的肺。未经污染的肺部血管清晰、脉络鲜明,被污染的肺丑陋脏黑杂物丛生,令人毛骨悚然。然而,被癌细胞遍袭的肺,仿佛一块失去全部弹性和真实感的橡皮死块。这时她轻轻在我耳边说道:“你在自毁你的前程……”她的话在我心上,如同静谧的原野上滚过一阵惊雷。那天晚上曲终人散,我凝视着这冯玉祥将军之后送我的图片,长久地发呆。间或,在我的眼前,父亲每当我吸烟时,那满脸“豺狼虎豹”似地凶狠表情不时地掠过。于是,我又忆起吴叔叔初次发现我吸烟时的目瞪口呆。一瞬间,我似乎顿悟了,他那双变得有些令我琢磨不透的目光中所蕴含的深意。那天的凌晨,我终于止不住又接过朋友伴着笑脸递来的一支烟。在我将它点燃后,猛吸几口,奇怪,这“万宝露”怎没了它应有的滋味?顿时,我是那样无法形容地藐视自己毫无毅力。我在“我完了”的绝望中猛醒了过来,一边用纸巾擦着额角流出的汗,一边欣慰地告诉自己,我这次的烟是戒定了。旧金山两年后的一个初春的日子里,我在华盛顿一位药理博士家里,像电影里的革命志士,面对党旗,举行庄严的入党仪式一样,怀着一种博大的责任和使命感,光荣地加入了:美华国际反烟大同盟。
尽管吴叔叔几乎是发现我将来可以以歌唱为生的第一人,但我断定,他也许终生都没有机会,亲耳聆听我在豪华的音乐厅里放歌,在辉煌的歌剧院里演唱西洋古典歌剧中的各种角色。但又正是他,在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歌剧院,用了五年的日日夜夜仅仅演了一部歌剧的惆怅中,再次以不容讨论和商量的口吻对我说:“小禹,你是学西洋歌剧的,为什么不去西方国家深造和唱大歌剧呢?你一定要去,走出去,那才是你真正的英雄用武之地!”他说到“用武之地”时,显然加重了语气,楼道里的共鸣被他的声音振动起来,发出黄钟大吕般的回响,显得那样庄严和神圣。仿佛天神在授予我一个不容推辞、任重而道远的光荣使命。我的全身一下子被这种带着宿命意味的神秘气氛所震摄。我的灵肉以及意识被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严峻紧紧地罩住。这种在我生命中,尤如被电击一般既庄严又带着浓重使命感的震摄,在我出国后十年,异国生活的漂泊和孤旅中,唯有在我主演西洋大歌剧中的国王和红衣大主教时,才能畅快淋漓地得以重温,有时,我疑惑这些都是发生在梦中。当庞大而訇响的交响乐伴着洪水滔天般的合唱,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我已经无法感到我的自身存在了。我觉得我是意大利歌剧泰斗威尔第用他的乐魄推上舞台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罗马的红衣大主教,我是俄罗斯民族歌剧作曲大师穆索尔斯基,被他那雄浑苍凉和悲壮的笔牵引上了舞台。用极度恐惧而又残酷的心态,多疑而又暴躁的情绪,错乱而满眼幻象丛生的精神世界来诠释着:双手蘸满皇位继承人的鲜血,终日活在疑神疑鬼,神经濒于崩溃边缘的俄国沙皇鲍利斯·古多诺夫。吴叔叔尤如一个先知,如同威尔第歌剧《纳布寇》中的大祭司匝卡利亚一般,以绝不容置疑的口吻和信任,在我人生几个重要的时段,小心翼翼地指示着,宣告着我将等待的福音,收获的福祉。至于需要以什么样的奉献和如何准备,才能坦然地去迎接那种奇妙的福音,去牢固地拥有那种终生受用不尽的福祉,他却从头至尾未曾点拨我丝毫。仿佛我仅仅需要按他所告诉我的“终极目标”一路走将下去,本身便会福星高照。难道不是吗?我常常这样自问。假如一件事的机缘巧合不能称为“奇”的话,那么在我颇为精彩的人生阅历中,多次的传奇事件,就不能不让我笃信:冥冥之中,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在保佑着我。请问:有谁,在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时竟不识简谱;有谁,在拿到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皮博迪音乐学院的奖学金和录取通知书时,竟还对英文发怵;又有谁,在比利时皇家歌剧大赛获大奖的前夜,竟将玻璃墙当空地穿越而过,结果被送进医院,在左眼的上角被缝了七针……我永生难忘,当我走上台去,不知所措地从评委主席手中接过奖状和奖金,迎着海潮一般地观众的狂呼:“中国,孙禹”时,我一边流泪,一边反复地想着:我是怎样才从遥远的中国走来,最终走上了这个辉煌和高贵的领奖台……
我的双眼又落在父亲悼文中那段让我心悸的文字上:“似乎是怕打扰别人,你在人们熟睡的凌晨,悄悄地走了。那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烛光同时也熄灭了……”吴叔叔那清瘦而飘逸的身形和面影再次占据和拥满我的视线。十年后,我这个“人在洋邦”整整漂流了数十载的游子又重归故里。在那个我在异国它乡曾多少次梦魂萦绕的“宿州路九号”大门口,一眼便认出您在老伴的挽扶下,吃力而轻飘飘地朝我走来,脚下仿佛踩着两片祥云。从那时到现在,我始终记不起您穿什么颜色衣服,只是深刻地记得,您整个人的颜色仿佛被碘酒久久
地浸泡过,泛着暗涩的灰黄色泽。您看到了我,表情显得很意外,略带点惊讶和激动。您努力地朝我微笑着,睁大了眼睛。您的老伴笑盈盈地看看您又看看我,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您停在我面前,用眼里全部的慈祥和笑意抚摸着我的脸庞,拥抱着我的全身。我明确地感到,您嘴巴嚅嗫着,在做极大的努力想告诉我,您此时此刻极想和我说的话。但结果让您自己很不满意。您有些欠意和羞赧地仅仅吐出一两个单字:“好!好……”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病魔竟能让您虚弱成这个样子。老伴扶着您怀着言犹未尽的深深遗憾,又像刚才那样吃力而又轻飘飘地离去。就在您和老伴就要拐进楼道时,您似乎和自己有些过不去似地,有些挣扎般地缓缓转过身来,又朝着仍在凝视着您而呆站的我投来深深的最后一瞥。这平静、安宁、踏实的一瞥,尤如高山出平湖的水面上,悄然掠过一纹涟漪,一瞬间便速疾地消逝了。那时,我的心里,每一个角落都被一种难以形容的感动盈满了……
三月下旬的一日,我在法国地中海沿岸的一座名城——尼斯,用演出意大利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的空档,给家里打越洋长途。电话里,我父亲告诉我:你吴叔叔走了。放下电话,我呆坐在窗前,放眼那一望无际,仿佛永远蔚蓝的地中海久久发愣。不知过了多久,在天海一线的远方,缓缓驶来一艘通体洁白似雪的客轮。当这艘被海水衬映得更加洁白的客轮驶近的时候,它倏地发出一声嘹亮的汽笛长鸣。于是,我觉得浩瀚无垠的大海深处,由弱至强,由远而近地传来亨得尔那庄严而空灵的“弥撒”圣曲。于是,汹涌的海涛恰似浩荡而辽远的混声大合唱,将我整个人彻底地淹没了……
吴叔叔,您安息吧!做为一个普通的人,您的仙逝和善后,也许平凡的尤如草木花卉,秋天凋落,春又复生。但是您的仙逝,不啻在我们父子两代人,还有许许多多得到您帮助和提携的作者和朋友们心中,耸立起一座值得永远纪念和仰视的丰碑。由于您的平凡,在平凡的人们心中,这座丰碑愈加显得真实和高大。我想您留在我父亲心中的丰碑,是您以您的人格和人品,以及几十年的相互了解所铸造的。而您留在我心中的,除了丰碑,还有一种用言词所无法倾诉的、刻骨铭心的感念之情。这种深刻的感念,在我今后的人生中,每当我取得成就,再创辉煌时,它都将会如同灿烂的旭日一样,冉冉东升……
责任编辑潘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