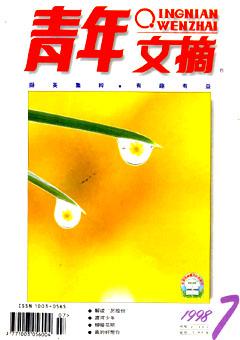解读“厉股份”
李俊兰
无论幽默还是戏谑,当公众将一个人的称谓同国家、民族的一段历史相联系,我们便有理由认为,这个人在史册上留下了些什么。
对这样的人,我们不应只是等待历史的庄严记录,还应让现实的人有所感觉——
“厉股份”对别人喊他厉股份抱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随大家喊去吧。”操一口声线较细的吴依方音的普通话,传达出的是北方男子汉的“爽”。
自1984年在社会上公开演讲、鼓吹股份制理论,到去年党的“十五大”将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写进总书记的报告,成为执政党的意志,其间几经风雨几度沉浮:共鸣与非议,掌声与棒喝,由此也使他本不平坦的学术之路愈发显得不平凡。而今,尘埃随风,是非公断,“厉股份”自然也就声名远播。
倒是他的学生们有些不解了:厉老师目前出版了47部学术著作,学术论文达几百篇之多,理论自成体系,如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第二次调节论、转型发展理论等等,可怎么独独喊他厉股份呢?是不是有点“以偏概全”了呢?
就是他自己,也认为最能代表他关于当前中国经济学术观点的是1990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可,可那怎么叫哇?”——他的大弟子、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朱善利博士非常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叫‘厉非均衡?那多拗口呀!再说,四个字的名字,像日本人。”
由此,“厉股份”的好处便凸显出来——它是大众话语。国际上在二次大战以后、中国则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日益成为显学,有造诣的经济学家往往成为国家决策层的座上客。厉先生的非均衡论、二次调节论等等学说,其直接的影响力、作用力恐怕首先还在于政府领导层或相关机构。唯有这股份制理论与中国的千千万万个企业,与数以亿计的民众民生息息相关,它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触动是广泛而深刻的,作为一项经济理论它所引起的关注也是空前的。换言之,它是厉教授以吴侬方音唱出的一首通俗歌曲,而且列排行榜第一。
厉股份——不是学术界的命名,不是领导人的钦定,这是中国民间的赠予,是集民间百草编织成的一顶荆冠——是厉先生以丹田之气、热血生命推动过的一段特定历史、那段历史又回报给他的最好礼物。
是为名解。不过,67年前,厉以宁先生在南京呱呱坠地时,其父母的祈愿是“凌厉而出以宁静。”
讲台上,这个把失业与通胀、转型与发展阐释得透辟入里的经济学家,是那个梦想成为化学家的求学者吗?这个在谈笑间播撒中西学识的著名教授,是那个将通往讲台的路视为畏途的内向青年吗?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阶梯大教室,宽敞明亮,晚六点,离上课还有半小时,才进门的人发现可容纳300人的教室已没有空位了。黑板前,一位男生正在抄写“公告”:此课为97级MBA的必修课,旁听的同学请坐最后两排,谢谢!——而此时“最后两排”的后面都站了两排人,有人干脆在水泥台阶上打了“地座”。
六点半,拎着一只旧提包、提包拉链处塞着一瓶矿泉水的厉先生走进教室,喧嚣归于肃静。“为什么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之初都会遇到失业问题呢?中国的失业问题同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特殊性呢?”这样的设问不由你不跟着他的思想走:“国际上有一条公认的现代化标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30%以下。目前美国是4%,西欧国家为10%,我们中国是80%。当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市,城市的岗位有限,于是出现了失业。所以失业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中国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大家注意,是既转型又发展,还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计划体制的后遗症,就是过去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隐蔽性失业不断公开化的问题”——语言朴素、平实,却让你一步步地贴近事物的本质。“失业问题的出路何在呢?”他用了一个比喻:“骑自行车的人都知道,骑得快车子反倒稳,慢就晃,停就倒。因此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有更多的岗位出现。”
课间休息时,他点燃了一根香烟,三三两两的学生拿着笔记本请他签名,也有围上来请教问题的。
据说这种“火爆”和“叫座”已持续了十来年。盛誉之下,这位教授却“托底”说,学经济、当教师都不是他的本意,“是偶然,使我踏入了经济学的大门”。
祖籍江苏仪征,南京出生,曾在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就读,12岁戴上近视镜,中学时既喜欢数理化又热衷于文学。“我立志当化学家是1947年,在金陵大学附中学习期间。我们到南京的一家化肥厂参观,使我了解到化肥对农业的种种好处,于是我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毕业后我被保送金陵大学,我选择了化学工程系。”不久,全国解放,他在湖南参加了工作,在一个消费合作社当了一年多“厉会计”。“1951年我离职参加高等学校考试,委托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好友赵辉杰代为报名,他认为我学习经济比较有优势,就替我做主,第一志愿填了北大经济系。7月我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录取通知。至今我还在感谢赵辉杰代我作出的选择。”——正是赵辉杰的“包办”,为中国贡献了一位经济学家。
大学毕业时,厉以宁很想到科学院经济所工作,他觉得自己口才不好,着急时还有些口吃,所以他怕讲课,也不愿讲课,但最后还是被留校当了资料员……
“厉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外国经济史中古罗马帝国那节课,”一位同学回忆道,“他在大黑板上,几笔就画出了罗马帝国极盛时的版图,然后讲历史演变,怎样成为今天的格局。他对这段历史熟悉得让我们吃惊。那堂课太精彩了,下课时我们使劲儿给他鼓掌!”——同学们哪里知道,厉先生和他的好友马雍合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时,两人还都是30岁上下的青年,精力旺盛,对罗马帝国由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原因,有过几次彻夜不眠的讨论,他们还以这段悲剧的历史眼光来审视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落伍,读活了经济史原著。
“口才不好,我就以充实的内容来弥补”。长达20年的知识积累,使厉以宁在讲台上挥洒自如。他一次次地叮嘱后来学子:“经济学家是社会的设计者,要为整个社会思考问题,要有这个使命感。”他在这里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也在这里展示自己的人性人品。
也是一次有二三百人参加的大课上,当厉先生将他撰写的几十万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义发到同学们手中时,一位男生站起来说有段话不准确。厉先生觉得不太可能,那位男生就辩驳,大家也议论纷纷。琢磨了一会儿,厉先生弄清是语言表述有点毛病,他让大家安静,然后一字一字地改正讲义。提意见的那位男生“下场”是——从此被他另眼相看甚为欣赏。
这件事给那位男生的心得是:“厉先生不愧是大家风范,以他的学识、威望,谁敢跟他争呀?学问高的人才能有这样的涵养,当场改错,还从此看重我。”如今,这位男生已成为一个几千人企业的负责人,会上会下每每听到不同意见不同观点时,他说脑海里出现的总是那堂课的情景。
是偶然,使厉以宁迈入了经济学的大门。
但绝不是偶然,使他成为经济学家的。
这个如海绵吸水一心向学的高材生,是那个京郊农村运肥垒坝、赣水岸边挑谷割稻的苦劳力吗?这个以对中国经济超前预测而令人折服的学者,是那个穷年累月面壁苦读的“板凳”吗?
作为北京大学人才链条的一环,厉以宁的命运既不同于他的师长陈岱孙、罗志如等人,也不同于他的学生朱善利这代人。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经济学家,他没有硕士、博士学位,他受他生活成长的那个时代的滋养,也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同时还饱尝了那个时代错误的苦果。
1957年的“反右”使厉以宁的恩师几乎全部蒙难。罗志如、陈振汉、徐毓等六教授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经济科学繁荣的意见书——因思想致罪,六教授有的被打成右派,厉以宁也因牵连挨整,开始了他为时20年的板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