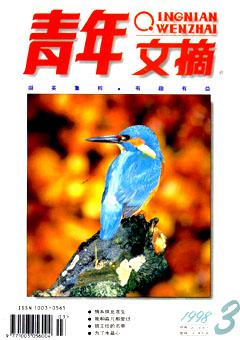荒漠里的理想家园
耿海亮
从前,这里是无边无际的沙丘之海;今天,这里已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他略略有些动情:“8年呐,这是让人掉眼泪的8年,但……毕竟我们挺过来了”
恩格贝,从很久以前到今天
这里的人在重建一个梦想。
人们说起恩格贝,总要用到一个词:“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这里水草丰美林木繁盛。很久以前,这里曾有一座“恩格贝召”,是一座香火鼎盛的喇嘛庙,游牧的人们常来这里朝拜。据说很久以前这里是牧歌伴着鸟鸣的地方。
但这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从秦皇汉武,到大跃进。战火与烧荒的野火伴着岁月流逝,林木不见了,草场不见了,人们迁往他乡,漫漫的黄沙吞噬了一切,恩格贝的美丽成了只有用无际沙漠中凸现出来的残砖碎瓦来印证的一个传说。
1989年7月6日,当时身为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副总裁的王明海带领20多名员工走进了这片无人的沙海。
当时,鄂尔多斯集团租下了这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为的是把这30万亩沙漠改造成草场,建立自己的绒山羊基地,养羊、采绒,为企业提供原料。
那年,黄河发水,渡口的船不能靠岸,一麻袋一麻袋的草籽是大家背过来的,没有路,陷在沙漠里的汽车是大家推过来的。
除了沙丘就是沙丘,除了风声就是风声。
7月21日,他们刚刚进驻恩格贝半个月。旱得冒烟的沙漠忽然下起了雨,到了傍晚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沙漠上竟然流出了一条浅浅的河。“鱼、鱼!”有人高喊,果然,一条条大大小小的鱼竟随着水,被搁浅在沙地上。人们欢跳着跑过去“捡”鱼,也就是在这时,人们听到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不是风声,不是沙声,是一种从未听到过的,但听到就让人心惊胆寒的声音。“洪水!快跑!”又有人喊了一声。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了每一个人的心,于是大家又扔下手中的鱼,拼命地往回跑,身后的河突然涨起来。
天黑了,雨没有停,隆隆的水声响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人们走出了小土屋,水在一夜之间已经退去了,再往前走,所有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洪水竟在一夜之间,将沙地淘出了一条100多米宽,18米深,长达10多公里的大沟。
这就是恩格贝。
大水冲走了表层的沙土,也冲走了他们辛辛苦苦播下的草籽,一切重新开始。
秋天到了,他们种下的草已经星星点点地在沙丘间长到了尺把高。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一场沙暴,就把他们半年的辛苦全部埋在了黄沙之下。这时他们才感觉到,最初的设想太天真了。没有树木挡风,草根本就不可能在这片荒漠上存活下来。
第二年春天,王明海领着他的兄弟们开始种树。
还是没有路。树苗是他们一捆捆地从沙漠外面背来的。
树从沙漠的边上种起,一棵棵地,成了排,一排排地就连成了片。树越种越多,越种越远,那一溜树已经种到了沙漠的腹地。每天早早起来,每人背上40到50棵两米多高的杨树苗,一脚深一脚浅地往沙漠深处背,30里路,然后再一锹沙一锹沙地挖坑种树。
到处是高大的流动沙丘,风一起,巨大的沙丘就像长了腿,头天晚上还在百米之外,第二天早晨就可能爬上你的房顶。在这里种树容易,但若要让树活下来就难了。树苗种下去,不是被风打折了,就是被沙子埋住了,没风没沙,又可能被旱死了。种下一棵树,只有到第三年头上,长到了胳膊粗,你才敢说,那树活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著名的治沙专家、日本鸟取大学教授、日本沙漠实践学会会长、年过80的老人远山正瑛先生来到了恩格贝。这位在日本本土治沙颇有成就的老人来到这里,共同的志向使他与王明海结成了忘年交:“王明海在,我在。”老人身体力行,整天一套野外工作服,同集团的员工一样,早出晚归,在沙漠里种草,种树。他还动员了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志愿者自费组成绿化协力队,每年到恩格贝植树,一直到今天。
恩格贝的创业者们对那一段日子都记忆犹新。但若让他们谈,便只四个字:“种草,种树。”种草,种树,5年,王明海他们像一群不知疲倦的蚂蚁背负着那一点绿色在沙漠中穿行。5年,辛苦的劳作终于得到了回报,肆虐不可挡的沙漠,竟被王明海他们种下的绿色一寸一寸地啃出了一个大大的缺口。
6000多亩林地成形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鄂尔多斯集团突然作出了一个决定:放弃治沙,全体人员撤出恩格贝。
治沙5年,给治沙者带来了希望,但对于鄂尔多斯集团来说,看到的却是绝望。最初的设想是美好的,沙漠变牧场,种草,就必须种树,种树既得防洪,又要蓄水,一环扣一环,等于是重建这里的生态环境。600万元投到沙漠里,不但没有见到任何回报,反而欠下了200万元的债务。就如同在沙丘中埋进了一棵草籽,治沙成了一场胜负难料的赌博。
企业放弃这个项目也在情理之中,但对在恩格贝住了5年的治沙者们,毕竟是有一点突然。然而,更令他们感到突然的是,身为公司副总裁的王明海竟决定辞去在公司内的职务,以个人名义向公司承包恩格贝10万亩沙漠15年,连同200万元的债务。他要留在这里。
这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这意味着他要放弃副总裁的职位,丰厚的年薪,舒适的生活。
“在这里干了5年,对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根草都有感情。那可是我们辛辛苦苦种起来的,一天天看着他们长起来的。沙漠里总算能见到一点绿色了,但是那是点很脆弱的绿色,如果不接着干下去,那这5年的辛苦就算白费了,用不了多长时间,这里又会变成一片沙漠。远山先生一个日本人,不计报酬来给我们治沙,而我一个中国人却跑了,我也丢不起那个脸。”王明海对我们说。
但他当时只对其他人说了一句:“愿意跟我留下的,就留下来。”他只说了这一句话,他也只能说这么一句。工作,职称,工资,大城市舒适的生活,他什么也不能许诺,在他这里,只有无边无际的沙漠和没有回报的辛苦的劳作。
人一个一个地走了。但还是有8个人跟着他留了下来。
王明海现在说:“我很感谢他们”
1994年10月的那个早晨,当从鄂尔多斯台地吹来的西北风搅起漫天黄沙时,王明海和他的8个兄弟就站在他们曾经为之付出了心血的白杨林边,站在风沙里。
洪水滔滔,和着心血澄出一片绿洲
王明海把在集团最后一年得的14万元奖金拿来还了债,但这远远不够。他就去借钱。“求人的滋味不好受啊!”回想起那段日子,他就直摇头。毕竟他曾经是有身分有地位的堂堂鄂尔多斯集团的副总裁,从前都是别人来求他,他签字、批条子的。更不好受的是三天两头有债主来讨债,为两万,三万,甚至是几千元钱的债务把他告上法庭。
然而最让他难受的是,他不能看着留下来的兄弟吃着山药咸菜,几个月一分钱没有,跟着自己治沙。
“治理沙漠的目的,还是让人生活得更好,治沙不能治得让人都吃不上饭。”求人难,他决定向沙漠要钱,变单纯的治沙,种草为开发沙漠,以开发带治理。
恩格贝沙漠地区气候干旱,平均年降水量250毫米。但是,常常是一场大雨就把这250毫米的降水全部倾泻到这里,这就是一场洪水!洪水每年携带着从鄂尔多斯台地冲下的几千万立方泥土,冲过恩格贝,泻入黄河。
沙漠里缺的就是水和土,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水土从自己的眼皮下流走。
“领着洪水在沙漠里转,把洪水困在沙漠里,把泥土流下。”王明海开始领着大家“玩洪水”。
冬天,他们用推土机在沙漠洪水的故道上推筑起十几公里长、30多米高的沙坝,当夏天洪水倾泻而来时,便被窝在沙坝里,而从上游冲下来的大量肥沃的泥土则沉淤在沙坝中。水流变缓了,清水淙淙流出去,留下来的是一两米厚的肥沃的土壤。“玩”一次洪水,恩格贝沙漠里就会澄出几千亩土地。恩格贝人称之为“澄地”。
3年,他们澄地3万多亩。有了土,就有了希望,有了土地,就可以种树,种草,种粮食,种药材。
这一切,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没有人知道,恩格贝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
为了找到洪水的源头故道,他们日日夜夜在风沙中穿行,几乎走遍了沙漠的每一个角落。
筑一道沙坝,投资要几十万。恩格贝人没有钱,甚至连筑基的石料都买不起,他们便到十几里外的野地里去拣石头,再一车车拉回来。
土留下来了,水也不能放走,恩格贝人又在两条“孔兑”(洪水冲出来的大沟)间筑坝,修起了两座水库。
恩格贝人说:“我们王总‘玩水玩得好。”可王明海却说:“只有外行才敢挡洪水,这是逼出来的。”
敢想还要敢做,敢做,更要敢想。
在恩格贝沙漠里有一眼清泉,传说这是“恩格贝召”兴盛时,善男信女们前来朝拜时取水的圣泉。一次,几位德国的治沙专家来恩格贝参观,见到这泉水,忍不住尝了一口说:“这味道好像是矿泉水。”同行的人听了哈哈一笑:“对,沙漠里的矿泉水。”所有人都当这是一句玩笑,笑过也就忘了。可王明海没有,他拎上一桶水,去了北京。他甚至不知道该找哪去化验。从环保部门到轻工食品研究所,一直到地矿部他转了个遍。
等他再次回到恩格贝的时候,他带回来的是几家权威机构的证明,这是优质矿泉水,绿色食品。然后就是半年的苦战,一个年产7000吨的矿泉水厂就在这沙漠里建起来了。
在沙漠中修宾馆,搞旅游,在沙漠中养驼鸟,谁敢想?恩格贝人想到了也做到了。沙漠宾馆每年接待上万名游客,驼鸟养殖已经成了恩格贝的支柱产业。
除了还债,恩格贝人把开发沙漠获得的资金全部投入了沙漠治理。他们3年澄出良田3万亩,而那条绿色的林带也以每年50至60万株的速度向沙漠腹地挺进。
但没有人知道,3年来,恩格贝人几乎是空着口袋,饿着肚子在这里苦干。
恩格贝人的一点精神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采访的时候,王明海总是爱说这句话。
承包3年,恩格贝的领导常常是一年两年拿不到一分钱工资,开发沙漠得到的资金除了还债,剩下的又全部投入到治沙中去了。
当年同王明海留在恩格贝的创业者们,都是鄂尔多斯集团的干部,家都在沙漠外的城市里,放弃了这一切几年守在沙漠里,他们图的是什么?
当你和他们谈到家庭,几乎每个人都充满了愧疚,谈到爱人孩子,每个人都眼圈发红。一年365天,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他们几乎每天都守在沙漠里。
家扔给了爱人,孩子扔给了爱人,一个大男人不但不能挣钱养家,在困难的时候,还要把家里的钱“偷”到沙漠里来。
“要说一点想法没有那是假话,谁不比,你不比别人还比。”同王明海一同留下来的王俊原来是集团里的工会干部,如果当年回到集团,每月是千把元的工资,年底还有几万元的分红。而在这里,种草,种树,种粮食,养羊,堆沙坝,哪一样活都得上,“原来我的手可是又白又嫩”,他伸出满是老茧的手给我们看:“每天就是一杯水,一张报,开会布置布置会场,清闲得很。但我不想那么做,人总得干点事情。”
在恩格贝,过年大概是唯一的固定假期。那年春节,已经是腊月二十六了,账面上仅有的一点钱给工人开了工资,而王明海和他的兄弟们已经一年多没有开一分钱工资了。而这时,粮站的人又来讨债,他们还欠人家10多万元的饲料款。当粮站的汉子看到账面上的记录,看到愁眉不展的几个男人,他不再要债,反而从自己身上掏出2500元钱,放到他们面前:“拿着吧,过年了,怎么也得拿点钱回去吧,老婆孩子等着呢。”
王明海把兄弟们的家属请到了恩格贝,摆了一桌简单的酒席,他举起一盅酒,举到她们面前:“我保证,有一天,恩格贝的男人不再从家里偷钱!”
他对他的兄弟们说:“从我们出来那天起,我们就在爬坡,爬一个高坡,最难受的时候,也就快到顶了,大家挺一挺!挺一挺!”
也许,他根本不用说这句话,当3年前,他们毅然抛家舍业留在恩格贝的时候,当在水库决口,他们跳进冰冷刺骨的水中,用身体挡住奔泻的洪水的时候,当所有的建设者爬上随时可能崩塌的沙坝的时候,他们便抱定了一个梦想。
“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没有钩心斗角,不争名,不争利,大家只想一件事,做事。”
“治沙不是苦行僧,等将来我们的事业成功了,等恩格贝变绿了,发展了,到那时,出去我们也腰粗,我们也是大款!”
没有工资,他们硬是用石块修起了一条7公里的路:没有工资,他们硬是给恩格贝通上了电,安上了程控电话;没有钱,他们硬是在沙漠里建起了驼鸟厂,矿泉水厂;没有钱,他们仍坚持与种养培育专家日尔干培养繁育着世界最优秀的绒山羊。
恩格贝有一面旗帜,大黄底色上是一点绿色的标志,而后就是三个黑色的大字:“恩格贝”。风沙一起,那旗就展开去,猎猎作响。
有过去集团里的同事请王明海喝酒,酒后,大家取笑他:“王总,听说你们那里实行的是年薪制,可就是到了年底也不发钱。”王明海红了脸:“对,但是你们那发了工资还闹罢工,我这不发工资,也没礼拜,可到我这来的人却越来越多!”
一个人总要有一点精神,而一个人的精神又可以感召一大批人。
当“王明海”“远山正瑛”“恩格贝人”以一种精神的象征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之后,全国各地有数百名年轻的志愿者先后来到了这片荒漠。
王志华,现在在恩格贝驼鸟养殖场饲养驼鸟,来恩格贝之前在杭州打工,揣上一篇《远山的呼唤》,带上打工挣来的1500元,只身来到了这里。“我没想过自己会在这里养驼鸟,内蒙古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茫茫草原,在沙海中植树,原来想象得很浪漫。但来了之后,一直在跟大家干一些零散的活,挖沙、捡石头,也种树,但毕竟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波澜壮阔。”他不好意思地笑笑,看了看身边的小驼鸟,“后来王总说过一句话:‘每个志愿者到恩格贝来,多少原来都可能抱着些虚幻的理想主义的念头,谁到这来,也不是为了体验生活,专门来受苦。没关系,恩格贝是理想主义的天堂,只不过,要实现这理想,就得把摆在面前的每一份工作都踏踏实实地做好。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发展前途,苦点,累点,有没有报酬都无所谓,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无论是作为恩格贝人还是作为志愿者我都感到很骄傲。”
来自山东的倪家龙在孔雀养殖场孵化小孔雀。他原来在山东大学读经济管理专业,还差一年就毕业了,但他还是放弃了学业,今年3月来到了恩格贝。“外国人都能来这里治沙,我们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放弃了学业,你不感觉可惜吗?”“到这里是抱着干一番事业的决心来的,也就无所谓可惜了,既然来了,就要做出点样子来。”
还有辽宁来的孟凡梅、蒋建栋,江西的王坚,安徽的李娟……在恩格贝的创业史上,这同样是一串闪亮的名字。
他们与恩格贝人共同种过树,种过草,一同筑过沙坝,很多人已经离开了恩格贝,他们抱着激情与梦想来,带着收获走,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恩格贝的日子,而恩格贝人也会记住他们。
今天来到恩格贝,我们无法想象8年前这里曾是漫漫黄沙覆盖的世界,就如同当年王明海无法相信恩格贝那美丽的传说。
一片一片的白杨林,苗圃,良田,鲜花,小鸟,羊群。8年间,恩格贝的创业者们共栽植乔木200多万株,植灌木200多万株,并且在沙漠中淤澄出良田3万亩,使承包的10万亩沙漠的植被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
8年,恩格贝的创业者在这片荒漠中种下了一片永久的绿色。
“我现在考虑的是,不能让大家一直穷下去。治沙,总得有饭吃吧。”承包3年,恩格贝不但还清了债务,每年他们还投入治沙资金100多万,而这些钱又都是他们一分一分地从沙漠中抠出来、从口袋里省出来的。今年,恩格贝的领导们又是一年多没有发工资了。
“我想在两三年内扭转困境。然后”,他顿了顿,望着眼前的杨树林:“用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把这里建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上都独一无二的城市,类似村镇一样的城市,但决不是村镇,是一个类似治沙产业化集团似的城市。这里人口很少,人们都很富裕,文明,没有犯罪,这里官很少,但劳动生产率很高,要做事的人很多……”
我们无法想象他所描绘的这一切。这就是在王明海、在恩格贝人的头脑中的那个梦想吗?但看到恩格贝人8年来风风雨雨的历程,看到今天恩格贝的景象,我们又不得不相信这一切。
他们既然敢将希望植于荒漠之下,就必定自信能让它萌芽、生长。
(王宏摘自《中国青年》199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