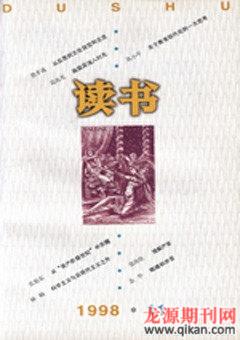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处境
朱青生 王 林 王南溟
王林兄,南溟兄:
一九九七年是中国艺术界值得庆祝的一年。汪建伟和冯梦波参加了卡塞尔文献展,标志着中国艺术家参加了世界上全部最重要的展览,在国际艺坛上已经没有缺席。多少年“走向世界”的追求,终于告一段落。一九九三年孔长安和我一起讨论威尼斯双年展之后的目标,两人皆认为,谁参加卡塞尔文献展,就意味真正成功。在欧美和国内的艺术家都曾努力争取。现在有了结果。虽然不是我为第一,但还是有完成一件事的喜悦荡漾在心中。
你们二位约我说出自己关于中国艺术国际策略的意见。我的意见建立在对中国艺术现状的分析之上。中国艺术界(不是指美协系统的中国美术)的主导倾向是被“洋选”展览和涉外“买办”控制着,但是在文化上普遍地还被困在被动的“殖民地心态”之中。值得与法国国民的心态相比较,一个法国人,每天的衣食住行水平与一个中国市民相当,但他却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自信地行走,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文化。在美国人面前和在中国人面前他的态度差不多是一样的,为自己是法国人觉得骄傲。法国有自己的悠久文化传统,这一点可与中国媲美;法国有现代文化,这一点同美国抗衡。美国没有悠久传统,但还可以以新的创造为荣,就像一个出身贫寒的大将。而中国人如果仅仅是强调悠久传统,现在却无所长,反倒像个文弱的名门之后。中国国家已经强大,在国际必定被重视,而其人民和文化不一定受尊敬。尊敬是出于理,发自他人内心。重视是出于力,发自他人的畏惧和利益的欲望。要想在国际上受尊敬,单有古老悠久的文化和强大的国力还不够,必须要有创造性的现代文化。如此看来,现代艺术本身虽无民族性,但的确与这个文化休戚相关!
怎样去对待“洋选”和“买办”这种倾向?艺术的性质和国家的境遇使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时又有无奈,又有慨叹。
其无奈处在于艺术的现实成就的标准是被人接受,艺术家在国内的展览条件差,不仅在展览设备条件上如此,主要还在于对艺术家的态度。艺术家在中国失去以往的主题性创作的土壤,而探索的风格也极少有展览机会,美术馆和博物馆是收场租的。西方国家博物馆展览不仅不收作者的钱,还要负责为作品投保,印制画册、明信片、招贴和请柬,发给参展艺术家工资。对中国艺术家,还免费邀请去当地考察研究。我在苏黎士Riedbdrg东方艺术馆的个展的作品,博物馆从瑞士放一集装箱大卡车开到海德堡我的画室门口,将每一幅画用特种包装材料裹好,一一签字然后起运。一个大车装十几张画,缓缓离去,真让人感受一种尊严。学者或评论家担当“裁判”,谁被选中举办文化性(或称博物馆系统的)艺术展览就胜出一局。虽然这中间的机会因素很多,但是顾及个人的价值和声誉,具有学养和地位的展览策划人常常深思熟虑。虽免不了一时看不透特别新颖的艺术观念和作品,但是,也很难发生很差的作品展出、很好的作品去掉这一类事情。因为他们在法律和道德上既不接受艺术家的委托办文化性展览,也不接受艺术家的贿赂写评论文章。这是由文化独立的体制决定的。国内要经过相当时期的磨合才能到达这种境界。此是无奈之一层。
中国艺术家矢志从艺,生活常依赖别人接受其作品。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市场经济,有钱的买主以其口味鼓励或者挫伤着作者的心。最花费精力和智慧的探索性艺术,常常不为市场接受。古来就有“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作牡丹”的怨叹。今天从艺术收藏角度来购买作品者来自海外。一九九六年波恩举办《啊,中国!》(China!)展,非常自负地宣称,他们选择了在中国最好的但不能展览的艺术家和艺术。实际上是借展览募捐了一大笔钱,在中国买了不少作品,的确也是注重探索性。后来就此而做起生意来,颇涉丑闻。但对中国艺术家来说,处于相对“单调”和“贫困”之中,能得到“出国”和“卖画”的双重机会,明知操纵者不地道,别有用心,也愿意投稿,这是无奈之二层。(波恩展只是选择了调侃、讥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作品参展。作为主题展,并无可厚非。但是组织者一再暗示中国文化只是如此,把一部反映参展者的录相片拍得像马戏团介绍,并利用冷战后余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情绪,做了不少新闻炒作,不仅在德国受到批评,对我们也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我当时与他们也作了一个对话,对其欧洲文化殖民心态作了清晰的辨析。对话整理后,我要求复验原文被一再拖延。最后不得已,我通过外交途径,由大使馆转交给他们正式信件,撤回了我的对话发表权。)无奈是出于不得已,而有主动摄取、自甘人后的情况,更令人感慨。
整个世界的艺术进入本世纪后,就不以画种区分艺术的高低,即使是以市场行情来衡量,当代最昂贵的艺术作品也从不以材料定价。可是中国国内却特别强调“油彩和画布”,一出手就低人一筹。作为一个艺术家,扪心自问,谁都以艺术水平论高下,至于用什么材料来作,则是个次要问题。主次一经颠倒,必定贻笑天下。欧美那些别有用心的展览策划人和好心的文化工作者,对中国一味推崇油画都评以“二流印象派加二流表现派”,前者出于阴险,据以作为欧洲文化主流对东方的征服;后者出于痛心,中国自甘如此,外人只能兴叹。我自己本科是油画专业毕业,对油画特别喜爱,在伦勃朗一幅画前常能留连二、三小时,目前也很喜欢徐明华老师、方励君、王广义、刘晓东诸位的作品,但是深慨油画至上对中国艺术家境界的阻碍。大师在意自己的创思,该用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想用什么就用什么。先以画种为尚,竟自觉取法乎中,此慨叹之一层。
也许油画作为技法,在表现力和刻划精度上颇具特长又有收藏习性支撑,卖得好也是一种行业,况且画油画者的诚实和认真的“油画精神”在浮躁奸滑之风屡禁不止的中国,论品性相对高尚,于世有补。但是涉及对“现代化”的理解,顿生疑难。现代化是每个国家和文化都必将遭遇的历史进程。率先现代化了的发达国家和民族,其进程中与自有传统文化的传承、反叛、冲突和再生的关系,常常被以势利定准则的短见者视为普遍原则。美国文化风行全球,并不是美国文化伟大,而是全球势利短见者太多。美国的歌舞剧本来也就是美式秧歌,美国Pop,但是美国政府为了国家利益,把二者当作包装纸,到处利用“势”和“利”二手强制推举。中国现代化真的可用美国方式推行,那也认了。“古曲虽自爱,今人不多弹”这也不算新鲜。其实由马克斯·韦伯总结和提倡的“新教精神”是适合于北方国家(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而在东欧和南欧都不适合。日本的成功更是最好的反证,日本从来没有什么新教伦理。后来亚洲小国的发展进一步证明“现代化”是有不同的道路。每个国家和民族只有自己的现代化,没有普遍的现代化。现代化重在一个“化”字,是现实的生存在国土风俗中的人的变化,而不是被率先进化的国家和国民所同化和奴化。现代化是一种文化,文化是生成的,而不是取代的。小国家小品种文化尚且不容易被同化,中华文明要变成美式文明为基准的普遍意义的现代化,那除非灭国。因此,现代化的真正含义是积极接受一切新进的刺激,在现实基础和文化习俗中创造出自己的新现实,新文化。中国艺术常常在忽阴忽阳地跳动,要么声称改变自己的文明,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背景;要么回到传统,一味在“古玩”堆上纵欲,忘记了我们不早一天现代化,就可能被视为世界公民的劣种。回顾我国近代的许多优秀分子,一直在调侃,调侃了五百年(从人类十四世纪人文主义萌芽算起),至少二百年(从人类机器革命算起),弄得一个大国文化上成了落后国家,真是愧恨交加。五四时代,一些热情的知识分子向往改造中国的民族性,八十年下来传统的东西是所剩无几了,但民族的精神到底改造了多少?是日益正大,还是愈加委琐?如果不能从民族的精神中将积极的因素提升出,不能把民族文化中创造的力量鼓动起来,指望华盛顿的那些参议员来救中国?还是指望安迪·沃霍尔的艺术改造中国画?所以在没有自力更生的文化创造的前提下,东抄西凑,迎合欧美口味的国际化努力,是伪普遍原则。由此生起的慨叹又何尝不能化作一片慷慨。
一九九七年过去了,一个追求“走向世界”的愿望已经实现。中国艺术的希望再次着实回落到二大支柱之上,这就是“文化”与“质量”。
余言再叙,颂撰安
朱青生
一九九八年春节
青生学兄,南溟学兄:
青生学兄关于中国艺术国际策略的来信,已经拜读。尽管“感动”一词,在策略化的中国美术界已不再让人感动,但对青生兄这封信,我愿意再用。
九十年代中国美术作品在参加了国际上最重要的所有展事之后,正面临真正的失落。前几年大谈“国际接轨”,其实不过是参展冲动。其间艺术家追求成功的幻想太多。一个欧美艺术家参加威尼斯、卡塞尔,与一个中国艺术家参加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后者不过是主展人的政治策略,是西方式多元化拼盘中的一个品种。可惜我们的艺术家不能自觉,甚至于投其所好。看到一些在国内很“牛”的经纪人和艺术家穿着长衫、对襟和三十年代学生装,按“老外”需要的形象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式上,我只觉得心里难受。不是因为他们,而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偌大中国,十几亿人口,没有自己主办的大型国际展事,难怪得我们的艺术家要削尖脑壳,去争取“被选择”带来的好处。至于国际接轨则不必奢谈,自己既无轨又无车怎么接?搭车而已,人家的列车路过中国,下面人头攒动,列车长伸手一指,点到谁就是谁,激动、兴奋,受宠若惊,几天几夜睡不着。这里的确有个文化权利问题。记得波恩博物馆举办《中国!》展,我和馆长Dieter Ronte曾有一番长谈,大意是说不能仅仅从人权主义角度认识中国,当时Bonte先生是非常认同。但展览一到欧洲便变得非常的政治化,典型的例子便是郭晋的作品。本来他画儿童,主要是对孩提时代的回忆,有一种时过境迁、人生多舛、童心难寻的感慨,结果让一位主展人一宣传,竟和什么中国孤儿院联系起来,真是荒诞。一九九六年我劳神费力去参与策划上海(美术)双年展,并力主它向国际大型展览靠拢,无非是想从艺术体制上造成国际交流的可能性。只可惜限于莫名其妙的“中国国情”,这个展览要成长为比肩于威尼斯、卡塞尔的国际展事,实在遥而无期。但这个问题,始终是一个问题。韩国尚有规模不小的光州双年展,何况中国呢。
作为批评家,百无一用,书生一介,我们只能纸上谈兵。当然思想是自有其力量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相信,还要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呢?从一九八九年以后,我就开始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立性问题。现时的中国艺术,一方面由于先进通讯和公共传媒的使用而获得了世界性的文化资讯。另一方面又由于其特殊境遇,面临着双重困境:一边是欧美现代化标准的强权,一边是港台商业化操作的诱惑。目前中国当代文化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混乱。前现代的问题、现代的问题、后现代的问题互相交织在一起。我们既有启蒙主义的任务和形式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又有文化身份的问题正在提出。在此情景下,我们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显得急功近利而又稀里糊涂。前几年我参与《美术批评家提名展》,本意是想抵制商业化,强调本土批评的作用,但结果还是让商品意识搞得面目模糊,且落入学院主义窠臼。我一直闹不明白,当年《中国美术报》上的先锋们,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为什么那么喜欢学院派,而且那么热衷于投入以前那种主题性画展。难道权利就是反对的归宿?最近看电视《水浒》,别的没什么感觉,只是觉得知识分子应保持批判的张力,即使天诛地灭,也当无怨无悔。
谈到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这是中国人上下一致的追求。坦率说,我不完全同意青生兄信中所言“没有普遍的现代化”,因为不加分析地这么讲,很容易导致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结而使保守主义乃至封建主义抬头。现代化之谓有两层含义,一是科技发达带动生产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称之为世俗现代化可也。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做千家万户奔小康。但人类不太可能在这条道上无限发展。现在大家都羡慕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水平,汽车、情人、小别墅。但有人计算过,如果解放全人类,让全球五十多亿人过上这种标准的生活,我们所消耗的能源需要二十个地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天文学家恐怕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也就是说,人类不可能实现美国式的现代化,世俗现代化的进程值得全人类去反省。现代化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人的自由程度。从启蒙主义起,个性解放就是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可以说整个现代艺术就是从浪漫主义对个人情感的强调开始的。我们不能把个体解放视为仅仅是西方的文化精神,从而以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加以拒绝,因为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不断解放和对于充分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不是某些民族的专利,而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此可谓精神的现代化,这是具有普遍性的。
当然,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普遍的现代化”才能言说。至于文化建设,警惕由此推出的全球西方化和美国化,实属必要。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始的话题,即中国美术如何在面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霸权时确立自身文化位置和自身文化身分的问题。
除了前面所说文化体制方面的建设即世界文化权利的分享之外,我想最重要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是前提,即我们在国际上确立文化位置和文化身分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断为国争光?还是光大种族优势?对此不必多说。我想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争取中国人精神上的解放,不仅从封建主义文化而且从殖民主义文化中解放出来。文化殖民主义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已成为惯性意识形态。比如开个书店,你要叫苏轼书店鲁迅书店肯定不如卡夫卡书店或博尔赫斯书店响亮。一种化妆品,叫做“霞飞”总让人感觉低档,一改名“霞飞奥妮斯”就很诱惑人。对此你有什么办法?但艺术是干什么来着?不就是因为对既定现实和惯性意识不满,想通过感性创造的力量来开拓人类精神的可能性吗?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才重返人本主义,重返人的欲望、需要和要求。在世纪之交应该响亮地提出新人本主义和新浪漫主义。人的身份问题实质上就是人的解放问题,只不过这种解放不再是林肯解放黑奴宣言式的人人平等,而是克林顿关于同性恋法案的差异共存。今天言及“自由”,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个人的自由应该以他人的自由作为界限”,另一方面是“承认他人可以与自己不同这样一种权利”。我们是在差异原则中讨论并存的或共享的自由。只有在解放人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讨论中国艺术的国际策略。
第二是中国经验。正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中国文化大变动的时期,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十分丰富。我之所言“中国经验”,包括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当下经验、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从文化学角度讲,我们不能把中国经验视作一个整块,而应看成是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生存状态及精神体验。对每个艺术家而言,它都是具体的、局部的、真实的和本质性的。从历史所载是中原文化一统天下。就现实而言,中国之大,仍相当于欧洲多国,各地区生活状况和生存方式差别甚大,资讯的丰瘠侧重亦多有不同。我们应该抵抗当代文化中一体化倾向对区域性特点的抹煞,这里所言的当代文化乃是非常具体的,就像盒式高楼、可口可乐、港台歌星、好莱坞电影以及笑容可掬随处可见的肯德基老总。我从来不认为艺术属于国家概念,故不惮于对中国美术作区域性研究,有时甚至认为,我们所谓的国际接轨,要对于人真正有意义,就是区域间的交流,亦即人与人之间共享不同特点的交流。具体的生存经验对于艺术的作用乃是本质性的,我们正是在周遭的经历与体验之中,产生想象力和创作冲动。
第三个问题是批判精神。我始终认为,当代艺术必须坚持知识分子性。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是知识的贮存器——在这方面知识分子赶不上计算机——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他们是社会思考的神经,是一群在精神文化领域中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寻找可能性的人。艺术家的知识分子性首先表现为对当代文化的思想反省和批判精神。批判和反抗有所不同,反抗往往是基于历史对于现状的否定,而批判则是反省现实对于未来的责任。我之所以认为中国一九八九后的政治音乐和玩世绘画的大多数作品,反抗性强烈而批判性贫弱,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所针对的基本上是毛泽东时代的问题——虚假的政治神话和空洞的社会理想,呈现于外,则表现为东西方冷战。简单的意识形态反抗往往类似农民起义,容易滑人草寇主义,到最后不过是项羽的理想——“彼可取而代之”,一种权利统治代替另一种统治权利。文化发展总是以群体规范为归宿,其普及化则是习惯势力的形成。而艺术乃是处在不同文化阶段的人对文化制约性的反省,正是这种反省保护了人的生命欲望、心理需要和精神追求。对既成文化的批判和对于作为文化产物的既成人的批判,使艺术返回起点。所以,艺术对历史文化和当下文化的批判即是人的自我批判。而回到人本即意味着回到批判的立场。我和岛子先生正在策划一个展览,题目即“知识分子与艺术意义”。我们的意图是想在艺术领域提倡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创造性,寻找当代知识分子话语方位,从当代文化批判的立场出发,去思考艺术意义及价值取向。当然这种个人努力,对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中国当代美术而言,只是沧海一粟。但如果有更多的批评家和艺术家真如青生兄所言,“将慨叹化作慷慨”,也许你我生活其中的美术界不至于朝着最不好的方向发展。
还是那句鼓励自己的老话:如果我们不能尽情发挥,那就让我们尽力而为罢!
致
问候!
王林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三日于四川美术学院桃花山青生兄,王林兄:
如青生兄在通信中所提议的那样,中国艺术的希望要着实回落到“文化”与“质量”两大支柱上。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艺术进入了国际交往中,它主要表现在中国艺术能参加国际上重大的展览,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于我们在国际交往中缺乏自主权,而使中国当代艺术在依赖性的展览中越来越处于附属的地位。这种地位的获得,一方面产生于强势种族对中国艺术的篡改,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艺术家屈从于这种强势并在这种强权下学得无比乖巧的结果。
歪曲中国艺术的“当代性”是海外举办中国艺术展的最明显特征,在这里,中国当代艺术恰似西方展览中被豢养的宠物,博得的是廉价的欢喜。在这种豢养下,中国当代艺术已经丧失了其文化与制度上的挑战性——既丧失挑战西方霸权主义的品质,也丧失挑战中国历史文化场境中既定秩序的意志,在后殖民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下,一种庸俗带进了艺术现场,这就是我们二十世纪末的艺术思想状况。
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可贵处在于他开始真正进入了自由主义领域。在八十年代,我们可以提出新潮口号,可以有新潮展览,但这种知识和人文精神都或多或少地可以看成是体制内的某种意图的传播,正是八十年代将这种精神变成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予以自上而下的鼓吹才促成了自上而下的启蒙运动,而那时的启蒙只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发言人,是顺着社会潮流的宠儿,这就不同于九十年代。正是九十年代意识形态的转变,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分离,才使知识分子进入了自己的角色,因为自此他开始在体制外从事其思想漫游,自由主义和批判性是这一时期的景色。从而开始撰写这部知识分子的历史,当在西方反意识形态已被纳入意识形态体制中的时候,我们仍然从游离意识形态开始,这拉开了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激动人心场面的序幕,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所作为。
基于此,正像如何在中国语境中寻找到有意义的艺术话语是我们当代艺术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那样,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以保障当代艺术的展览和通过展览促进艺术在本土的发展并建立起我们艺术的“文化”与“质量”,也已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现实语境及其艺术表达上的明确性问题,而这恰恰在当代艺术批评中被忽略了,所以,中国当代艺术越来越变得像狭隘的种族图像志。当代艺术已不再仅仅依靠文本自身发言,它被规定为意义的艺术,并且它的意义产生于文本与语境的一种互动关系中,即艺术的意义往往被语境所规定,这就是当代艺术区别于以往艺术的一个特征,它使艺术进入局部的和有具体针对性的文化场景中。当一个观众或批评家、展览策划人在尚未了解特定的语境而想了解那些艺术时,就显然不完全具备了解该艺术意义所在的要件。所以,就像观光旅游一样,某种强势种族往往以旅游眼光来看待第三世界的文化,而被看中的往往不是第三世界已发展的或正在发展的文化,这种旅游文化的地位很难使中国当代艺术在海外成为某种学术话题并介入整个当代艺术领域的学术讨论中,所以,中国当代艺术在海外的展览往往成为某种西方新闻和国际间政治策略的代码。
在九十年代最后的几年中,中国当代艺术已完全走过了八十年代以来简单模仿西方现代艺术这段历史,也知道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待于展览制度的健全和对艺术中“文化”与“质量”的重要性的认识,这将从根本上扭转九十年代艺术的歧途,并从此使中国当代艺术在新的支点上发展。中国当代艺术,正以其边缘文化的特征进入与人类文明对话的空间中,它在当代艺术中的积极价值就在于一个长久的专制主义文化正面临着瓦解,及其在瓦解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转而为批判性话题。所以,当下中国已经为我们搭了一个思想舞台,它以新的批判精神揭示文化上批判的重要性,正是当下语境才有了批判的可能性。在中国,一个新的艺术制度的产生本身就需要以批判精神为支撑,而如何将当下语境变为批判的资源以凸现艺术上的知识分子使命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源头。
此致
敬礼
王南溟
一九九八年七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