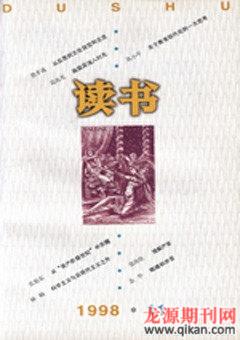关于教育现代化的一点思考
丛小平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分期,大陆与海外学者似有相当大的分歧。大陆史学界主流依然坚持以一八四○年为近代中国的分野,但海外学者已打破这种以外在事件为基准,过分强调外来因素的历史划界方式,转而从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发展去寻求近代史的线索。例如,从近代化的角度考量明清以来的商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研究清代江南士绅的分化,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分析辛亥革命的爆发,等等。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近代历史就不再是一个大断层,而是有着历史的和内在连续性的变革。
但是在教育史研究领域中,海外与大陆学者却又趋于一致,即将近代教育的起始点定位于西方教育制度的传入以及西式教育制度的确立。的确,在中国近代社会,教育体制算得上是变化急剧的一个领域。且不说一八四○年以后西方传教士所办的西式学校,从一八六○年代起,洋务派在“以夷制夷”的方针下,办起方言馆、译学馆、船政学堂,甚至送学童出洋,西方的影响可谓不小。一九○二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教育,一九○四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了近代教育的完整体系,从此新式学校大规模建立。一九○五年废除科举更是与传统教育体制彻底决裂的大举动,从此中国教育走上顺应世界潮流,与西式教育制度看齐的不归之途。
但是我们要问,在这种表层大变革的下面,中国教育制度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针对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有选择地改革,还是一味地对西方教育制度的模仿?中国教育制度是否有其自身的发展线索与命题?这些线索是被西式教育制度的建立所打断,还是跨越了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延续到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教育体系,顽强地浮现于民国建立之后?例如,科举的废除是由于其自身已不能满足社会制度对人才的选拔和教育普及的需求,还是纯粹对西方教育制度冲击的回应?明清以来在教育方面的趋势对近代教育有什么影响?中国近代学校的社会功能和作用与西方学校完全一样吗?教师政治地位低下与经济状况的窘迫是近代社会才出现的问题吗?提出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对传统与近代的历史分界提出质疑,对传统与现代性的对立不那么确定,从而将近代教育体系的确立与发展置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脉络中进行深入的研究。
台湾学者吴智和先生所著《明代的儒学教官》对明代教官的养成、选拔、任用、考核,其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在教育中的作用,以及与学术的关系作了详尽的阐述,其资料之翔实与丰厚,论述之清晰,在这一领域中,怕无人能出其右。书中关于明代教育方面的几个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近代教育问题作一些联想。首先是关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这恐怕是近代教育界长期面对的问题,究其根源,实则始于明代。教官》一书中指出,在政治上,明制规定,教官最高不过九品,而大多数则无品级,属于官僚体制的末阶、科举的剩员,政治地位自然卑下。而且,由于品级低微,薪资微薄,经济地位窘迫自不待言。但是,明代广建府州县学校以支持科举制度,为官僚体制提供后备力量,教官责无旁贷地成为主流教育体制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教官也由于明代国家对学校功能的设计而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明代的学校为一府一县的“首善之区”,承担着礼仪教化的功能。因此对教官的道德行为要求甚高,为师能授业解惑,为范则作人表率,教官也成为教化的官师。明代所形成的教师政治经济地位低下与道德要求高尚这种“剪刀差”,仍是民国乃至人民共和国时期的问题。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们努力想改变教师的经济地位,曾不断向政府和社会呼吁,教师们自己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如果我们翻阅一下从民国建立以来的报纸和杂志,一定会收获不小。而且,不少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教育家们常常以介绍近代西方国家教师收入水平的方式,试图借助“全球性”话语的权威改变教师的经济状况,为教师们争取更多的福利,但是这种努力收效甚微,直到八十年代仍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另一方面,对教师要为人表率的道德要求却一直是近代师范教育强调的一个重点,这与西方学校里教师仅仅扮演知识技能传授者的专业角色大相径庭。
明代教官这种责高位低的状况未尝不暗示着教育集团从此向着与政治集团分离的方向发展。因为,在明代,教官的选拔和任用已形成与官僚选任有所区别的途径,教官的选任,由明初的遍选儒生到明中期的副榜进士专任,再转变到后期任用举人、贡生、监生。到明代中晚期,教官多为有中级或初级功名却又科场失意的文人。所以,及至明代晚期,教官实际上已被排除出由正途出身官员所组成的官僚集团。而且,一任教官,不仅仕途无望,终生就被羁绊于学校教务,至死不过一“老明经”。大多数能安守教职者,皆因科场蹭蹬,政治上不得志,又急需禄养。这部分人的教学生涯固然清苦,但却保证了教育集团的稳定性、持续性和专业性。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表述清晰的、类似欧洲近代教育史上壁垒森严的教育专业群体,但无论如何,在明代,有一群士人,或者说,读书人中的一部分(根据吴书的估计,有明一代,教官保持在四千人以上),长期以教育为主。有了这样的基础,到清末教育改革时,教育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分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惜的是,《教官》一书的研究并未涉及明代书院的教师和私塾、义学、社学等初等教育机构的教师,否则,我们就会有更完整的前近代教师与教育的图景。
教师素质和专业水平也是近代以来教育界长期讨论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也与明代以降的教师选任有相当重要的关联。在明代,由于教官地位卑微,薪俸微薄,许多正途出身的士人极力逃避出任教职,政府不得不从仅有初级功名的士人中选任,因此,到明后期,贡生监生成为教官的主要来源。这一批人知识水平(即通经程度)与所教生员相差无几,若生员中有考上中高级功名者,其地位反在教官之上。生员看不起教官,“犯上作乱”之事时有发生,教官的知识水平也常为世人批评。清代这一趋势更加恶化,由于允许捐纳,许多教官甚至没有正式功名,其知识水平还不如所教的生员,这也是清代学校名存实亡的一个原因。清末民初地方学校风潮中,有相当数量属于这种因学生不满老师教学水平而“造”老师“反”的事件。在近代教育制度中,尽管有师范院校培养专业教师,但数量却供不应求。而且,在民国时代,许多师范生不安心教育事业,把师范学校当作进入高等学校的跳板。二十年代初期的教育改革甚至取消了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竭力向西方式教育制度看齐,结果,不仅造成教师短缺,教师的资格也大打折扣,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初中毕业教高小,高小毕业教初小,甚至同级任教的现象并不少见。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曾推行过教师资格制度,但在基层收效不大,而教师资格制度也由于战争爆发而中断。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农村学校教师和民办教师中,此种现象依然存在,直至八十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近代教育的这一问题也许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才解释得清楚,那么,中国教育近代化中的问题就不完全是以建立西式教育制度所能解决的。
明代对教育的普及似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且极其制度化。除了国家在首都设国子监外,各府、州、县均设官立学校,依次设教授、学正、教谕一名,训导四至二名不等(统称为教官)。廪生、广生名额从四十到二十不等,各级附生人数则不限。这一体系后来为清所承袭,不过却是每况愈下、名存实亡。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划的学制,其中师范教育体系部分,也是一种从上到下的教育网络。这种由国家拨发经费,以行政区划和等级为范围的各级官立学校,其学生由政府供给津贴,按地区配给名额,毕业生又由政府分派,几乎是从明代以来官学教育体系的一个延伸。当然,所不同的是,近代教师培训机构已经独立设置,不再依附于官僚体系和科举制度,学校在名称上也明确了培训目的,课程设置有所革新,不仅加入了许多西方知识内容,而且增设了教育专业所需要的心理学、教学法等课程。这里我们看到了在社会大变革中所产生的断层,也看到了断层中的延续。所以,西方教育制度的传入和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这一变革并非平地起高楼,或完全摧毁原有的教育体系,而必须是建立在原有制度基础上的延续。因此,这种近代的教育制度也就具有了某种传统性和本地的色彩,传统与近代性寓于同一体系,外来的文化与本土文化共生共存,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教育现代化历史的过程也许就是这样发生的。
美国学者萨丽·鲍斯韦克(Sally Borthwick)指出,在欧美国家中,学校是一种分离于社区之外的组织,但学校的课程却与社会的需求紧密配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学校设立于社区之内,与社区联系密切,但学校的课程内容却与社区的需求脱节。的确,在中国,学校(某些书院也许例外)从来不是与世隔绝的清修之地。但是,中国传统学校与社区息息相关的联系正是中国学校预设的重要功能之一。中国学校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在于其课程内容,而在于学校在社区内的地位与活动。《教官》一书虽专讲教官,但却不能不涉及明代的学校及其功能。明代设计学校的教化功能十分明确,学校是地方人才荟萃之所,先贤先圣祭祀之地,举行乡饮酒礼、教习乐舞、表彰孝子节妇的场所,也是公藏图书的地方,总而言之,是本地区文化和精神道德的中心。因此学校不仅是教育机构,而且对本地社区礼仪风尚,民俗道德都负有相当责任。到了明代晚期,学校功能衰退,世风日下,灾荒民变,异族入侵,于是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主张重振学校的地位,并赋予其地方自治方面的功能,试图将道德教化与地方自治借学校机构而融为一体。清代学校系统名存实亡,教官不教,学生不学,于是学校在社区中的地位日见式微。清王朝鼎盛时,严刑竣法与仕途收买并用,尚足以安抚士人。及至清末,科举败坏,吏治腐败,兼有内乱外患,社会问题严重,于是,改革呼声日高,整顿学校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就呼之欲出。从这一角度看梁启超《变法通议》中把学校建设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相当自然的事。而顾、黄的思想在清末民初广为流行,民国时期在地方自治中呼声很高的是“教育为地方自治之本”,也都是因为对学校教化地方的功能寄予了厚望。二十年代后期陶行知在南京建立晓庄师范学校,其意并不仅仅在于培养小学教师。晓庄师范在当地成为社区的中心,办起小学,幼儿园,成人夜校,图书馆,卫生所,甚至组织自卫队,积极参与社区生活的各项事务。建立这种教育机构的意义,其实已经超出了教育领域,而成为一种对社会组织形式的探索。不仅陶氏的实践如此,中华民国的教育法令也规定了学校在地方自治中的重要地位和参与地方事务的必要。中国近代学校的这种特点和功能恐怕不是移植西式学校体系所能解释的,它实际上是在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基础上对外来制度的再创造。在这里,传统与近代的切割似乎就无从下手。
《教官》一书还谈到了教官演变的另一方面。由于教官属于官僚阶层的末阶,明代教官总体上受官僚制度的约束。例如在回避制度下,官员不得在自己的本籍任职。但是,教官薪俸微薄,多数有家室之累,远途任职有很大困难。更麻烦的是语言,南方出身的教官在北方任职,或北方人执教南方,贻误学生不说,教官本人也深感不便。因此,许多教官寻求在本乡附近的省份或县份任职,以便就近照顾家庭,也无大的语言障碍。所以,有明一代,南人北教,北人南教的现象渐次减少。清代亦沿袭此例,教官除本府外,得以在本省任职。如果考察近代师范教育和教师养成制度,这种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本土化的倾向在二十世纪则更趋于明朗化。师范学校章程也明确规定了师范生毕业后必须服务于本地教育机构。高等院校的教师及高层管理人员在民国时期流动较为频繁,但中等师资离乡离土的则相对少一些,初等学校的教师几乎没有流动。本土化的倾向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更为强化,连高等院校师资的流动率也变小,八十年代,这一倾向更为明显。教师本土化固然是教育体系方面的问题,需要对其利弊进行分析研究,但是,这与近代以来中国持续存在的地方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值得回味。
《教官》一书还对明代教官的考绩与升黜制度及其方法进行了考察考绩与升黜的具体办法除了考核教官本人“通经”与否,即专业水平的高低外,更主要的是考察学生的中举人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考察“升学率”,即看教官名下的学生,有多少能考上举人。例如一县的教谕在九年任内,若考出三名举人,又考通经书者,则可升迁;有举人二名者,本等任用;如举人不及二名者,则降级。对比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教育界出现的以升学率评定教师及学校优劣的倾向,我们似乎可以作一点点联想。也许中国教育制度有其自身的脉络和命题,这些命题跨越如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等这样的表层政治性变动,保持了自己的延续性,而中国教育现代化所要面对的是这些命题的演变。这就使得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进程,而这种独特的进程,正是历史学家所要深入研究的。
(《明代的儒学教官》吴智和著,台湾学生书局一九九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