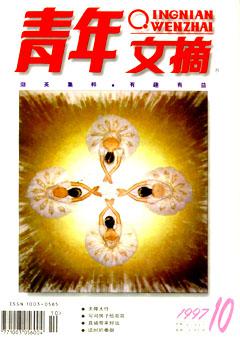青草戒指
窦登咏
那是一种郊外常见的野草,叶子狭长又有些柔和,就是这样一种野草喂养了我的初恋,但我至今仍不知道它的名字,如果有的话一定是一个既好听又浪漫的名字,就如有个女孩叫媚一样悦耳动听。
媚是那种多愁善感的女孩,在我们相识最初的日子里,我常对媚弱不禁风的样子不以为然,总以为有这样的女孩做朋友是一种快乐,而做恋人不一定是幸福,但后来媚不仅给了我快乐,还给了我刻骨铭心的爱情。
那天没有雪、没有雨,同样也没有灿烂的阳光,当我和媚坐在一片草滩西望时,太阳已跌进了远处的山里了。可我们谁也没有要回去的意思,看着媚若有所思的样子,我不忍去打乱她的思绪,就随手从身边扯了一根野草,是那种叶子狭长又有些柔和的野草,在手指上裹了一个圈,这使我别出心裁地又编了一枚青草戒指,还在上面镶了一朵米兰花。这时,有一个声音仿佛从远远的地方传来:“豆子,你能把它戴在我的手上吗?”媚的语调既轻又柔,如她的名字,我想不到媚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我仍被眼前这位弱不禁风的女孩深深感动了,要知道除了几本必修书和一支笨拙但从不曾枯竭过的笔,我几乎是一无所有。握住媚玲珑的右手,我仿佛握住的不仅是爱情,还有一生的幸福,我也分明看见媚的眼里闪烁着兴奋的泪花。早先的想法已荡然无存,带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走进校园时,已是华灯初放了。
那夜我第一次为爱情而失眠,从给媚戴上那枚青草戒指时起,我就已不再是媚普通的朋友了。媚把一生的幸福都押在了一枚青草戒指上,这样做对媚是一种不公平,于是我暗暗发誓要给媚一枚金的,把媚寄托在我身上的种种愿望兑现成真。
毕业后,我放弃了已分配好的工作,告别了媚,只身去了南方,我没有忘记当初给自己许下的诺言。在南方我拼命地挣钱,三年后,当我怀揣一沓钞票从南方回来,掏出那枚沉甸甸的金戒指要给媚戴上时,媚却像一个孩子似地哭了:“你以为金戒指可以升华我们的爱情吗?你错了。”说着,媚从桌柜里取出一个红绸布包裹的小盒子,一层层地剥开,里面露出了那枚青草戒指,米兰花早已枯萎,青草也不如先前翠艳,捧着它,媚轻声说:“只有这才是我一生最精美最珍贵的首饰啊,这些年我一直舍不得戴它,因为我深深地珍惜这份缘和相知相伴的这份感觉。”
望着媚手里那枚贫穷中的爱情信物,突然间那些用金钱膨胀起来的兴奋和骄傲,如一朵朵五彩缤纷的肥皂泡,被风吹得漫天飞舞,在落地时又一个个地破碎了,只有那枚青草戒指和上面的那朵米兰花在我眼前真实地存在。
(李本世摘自《家庭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