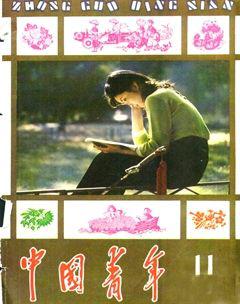海岛兵:寂寞中的美丽
窦卫龙
流泪的“刽子手”
还没有上岛前,陪同我的新闻干事汪彪将我悄悄拉至一旁:“窦记者,真不好意思,在我们这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谁上岛都要带些蔬菜上去,你看,我们是不是也带点?”
当踏上这个只有2.76平方公里的小岛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条规矩的意义。
这里远离大陆40海里,荒无人烟,终日听不到鸡鸣犬吠,27人的观通站成了这岛上的清一色的男性家族。
这里种不了蔬菜,米菜油盐得靠渔船每周补给一次,若遇上台风或大浪,渔船靠不了岛,十天半月,天天吃粉丝、海带、喝酱油汤便是常事了。
日子久了,岛上的兵们便想出了不少点子:开始是一挎包一挎包地从大陆
上背回泥土,倒在石缝里,种菜。怎奈岛上吹过的风都是咸的,菜芽刚昌出尖就被海风吹死了。种菜不行就养鸡,谁知,岛上那些兔子般大小的老鼠竟发现了新大陆,同官兵们开战,夺鸡,尽管官兵们日夜为鸡站岗放哨,可一年到头,从鼠口里逃生的鸡,也就只够他们喝一碗鸣汤。
养鸡不行,他们便养起了猪、牛。
猪和牛倒好养,在岛上不需猪圈和牛栏,更不用专人管理。到了吃食的时间,军营是他们的唯一去处,猪、牛同人一样怕寂寞。
这些猪牛平日里总喜欢往战士圈里“拱”,和战士们打在一起。战士们也喜欢它们一道满岛上逛,活泛一点的战士还爱骑在牛背上。有不少官兵还非常有心地给自己偏爱的猪或牛起个什么“肥肥”“小王子”一类的名字,猪牛倒成了他们的伙伴。
这下可好,到了宰杀的时候,官兵们谁也舍不得。岛兵们开了个全体大会,定了“法律”,规定了一个宰杀的前提条件:“须到非宰杀不可的时候才能进行、必须是关键时刻。”有了这前提条件的保护,岛上的猪,肥肥的,像小牛:牛壮壮的,像小象。但总有“非宰杀不可的时候。”
猪肥牛壮,大陆上用的宰杀工具已经不起作用了。
站里就给上级拍了封电报,请示使用武器。以后,站里自然每年多了数发用于射杀猪牛的子弹。
谁来做枪手呢?战士们都说:“这是刽子手,我不干。”结果只能由岛上最高行政长官——站长狠下心来,做了“刽子手”。
在岛上已经呆了17年的“老海岛”、现任站长张锦平对此深有体会。岛上站长这官什么都好做,就是“枪手”难当。在你端枪瞄准扣动扳机那一瞬,其他官兵向你射来的“仇恨的目光”会让你的手发抖,而你即将要夺去生命的那个它的眼神,更会让你心如刀绞。
那次,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上级工作组,张锦平把枪瞄准了那个最听话、最漂亮的名叫“露丝”的牛。记得当初给它起名字时,他几宿都没睡觉,翻遍了“岛上图书馆”,最后才在那本外国名著里找到这个挺洋、挺俊的名字,他觉得它和书中的她极象,属于温顺型的。
枪响了,鲜血从“露丝”的脖子下面涌了出来。不知是他的手抖,还是子弹没打中要害处,“露丝”没有倒下,反而坚强地站着,没有嗷叫,没有跑开,更没有反抗,只把头转向张锦平这位“枪手”。
张锦平的手软了,他看见了“露丝”的两只大眼睛,看见了它大串大串的眼泪如雨而下,看见了它眼底深处的眷恋。张锦平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扔下枪扑向“露丝”。张锦平哭了,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
从此,在这个岛上的奉献者的名册里,又多了一长串“露丝”这样的名字。
雾岛阳光浴
这个岛远离大陆,濒临公海。
岛上的兵称它“543”,这不是军事代号,而是指一年中有5个月起浓雾、3个月刮台风、4个月降暴雨。
50年代,部队进驻海岛时,住的要么是石头砌起来的又矮又暗、极难透气的石屋,要么是潮湿无光的山洞。现在,除了个别班、排仍住在防空洞里,大部分部队已经住上了明亮宽敞的二层楼。尽管如此,由于海岛气候条件恶劣,变化无常,海岛部队官兵的生活仍是困难重重。
有人说:“从岛上下来的官兵,如果没得过风湿病、关节炎,皮肤病,那他准是个机器人,或者是八辈祖宗积了善德,保了他。”话虽说得绝了点,但却是真的。
我们爬上山顶营区的时候,正赶上雾季。来迎接我们的部队副教导员崔胜龙说,雾季是最难受的,阳光不常见到,换洗的衣服在关紧门窗的屋里要十几天才能闷干。
以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我真切地体验着这雾季的“难受劲”。
在北京呆久了,会时常因气候干燥得让人难受而冷不丁地甩上一句骂娘的话。没成想,真到了这个空气潮湿的地方,心里的滋味真觉得比蹲监狱还难受。
新的被褥湿湿的,板结得有点儿沉,扑鼻的是带有霉味的湿漉漉的气体。漂亮的军官蚊帐在这里只能算是一个装饰,雾季里连蚊子都飞不起来。门窗关得很紧,就这样,雾还是像幽灵一样,无孔不入,钻进来,把整个房间弄得阴沉沉的,压得你胸口闷得难受。早晨起来一开门,雾裹夹着雨点就会重重地砸在你的脸上、身上。
雾季的海岛,住在楼下的官兵就比楼上的多一分辛苦。一觉醒来,地上会生出许多豌豆大的水珠,密密麻麻。鞋之类的物件头天晚上就放在了床下用铁丝系着的悬空板上,这时,本周的小值日会赶在大伙起床前,把水珠用竹帚扫出屋外,嘿,足足有几瓢。
走进官兵的宿舍,你会发现他们比大陆上的战士多有一个衣柜,多几套衣服、几双鞋。雾季里,阳光难得一见,官兵们换洗的衣服只好委屈地关在屋里“闷”,洗一套闷一套,等到没有换的衣服了,就得把半干的衣服穿上,让体温来“烘”干。
这还不算,没有阳光,屋里和屋外就没有多大区别,因为潮湿,身上老是黏糊糊的,那种难受劲就甭提了。头两天,营里安排陪我的文书小张还在中午和晚上带我去洗澡间,名为冲凉实为冲黏。后来我发现官兵们只能在晚上很短的时间内做简单地冲擦,于是就问小张:“你们不觉得难受吗?”“习惯了,另外今年特别,已经5个月没下雨了,岛上的淡水不能不节省着用。不过,水再紧,都要保证上级机关领导。这是岛上的规定,营长不让说。”
要知道,淡水在这个岛上,是多么地可贵。
第二天,我非常自觉地“要求”营领导取消给我的特殊生活待遇。
一天中午,小张兴冲冲地跑进来,不等我开口就拉着我向外跑:“窦记者,快,到山下去。”原来,漫长的雾季里也会出现雾淡的日子,阳光透过漂浮的雾纱,洒落下来,这时,营连领导就会命令官兵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阳光地带,尽情洗阳光浴。当晚,查铺的领导准能发现一些战士的嘴角仍挂着满足的微笑。
故事填充寂寞的岁月
有哲人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海岛官兵真信这句话。
在岛上作领导,千万别愁工作上不去,不用你招呼,下命令,官兵们都会有事没事往工作房、训练房跑。争着去上班,争着当标兵。海岛生活的寂寞,让每个人都想找一点事做来填补空虚。
因此,海岛的兵对他们的头有个特别要求,那就是会带他们玩。
说到玩,海岛官兵可谓是殚精竭虑想了不少办法,正如五连政治指导员周香荣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在这里当指导员,你必须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兴趣十分广泛的娱乐活动家,时时刻刻都要想办法把空虚寂寞单调这些词从官兵们的业余生活中驱逐出去。这样你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称职的海岛指挥员。”
在海岛的每个连队、观测站、雷达站,几乎都备有本单位独创的活动记录。沙滩足球、海上垂钓、贝壳拼图、海上射击等许多具有海味的活动、比赛,这多少给一代又一代海岛官兵们带来了欢乐。
在东海最前哨的一个岛屿上,在山顶的营区内,我看到了这样一个篮球场,与大陆上的篮球场不同的是,在场地的周围,拦着2米多高的渔网。
原来,十几年前,岛上的战士为了开展活动,修建了这个球场,但是,在比赛的时候,常常是一用力,篮球便借着海风滚到山下,被海浪卷跑。战士们只能守在山顶“望球兴叹”。后来,5位渔家姑娘知道了这件事,就私下里悄悄地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为战士们织了这张“拦球网”。当网被送到岛上时,整个连队就像过节一样。5位姑娘见此情景,也很感动,表示承担今后修网补网的任务。十几年过去了,姑娘们真的从未间断过,用她们灵巧的手为海岛官兵织出了一片晴朗的天空。
在岛上,还有一道很别致的风景,那就是讲故事。海岛的照明一般都是靠油机发电。为了节约用油,常常是夜幕降临时,关掉生活区的照明电。这样不能开展活动,大家就自动地穿着大黄裤衩,赤着背(海岛营区没有女性),端着小马扎,靠拢到指导员或连长身边,听这些自封为老海岛的老兵讲听过的或是没听过的,真的或是假的故事。久了,肚子掏干了,大家就开始随意神侃,有一句没一句的,如同球场中途休息。再久了,便有了“规矩”:大家轮流讲,或者是叫轮流吹,反正吹牛,随便,最终是要大家笑,笑起来就不想家了。
我去过的几个海岛,官兵们难得见到大陆上来的人,见了我们,都是兴奋异常,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在海岛兵营里,我感受最强烈的一个字就是“苦”。但这个字,守岛的官兵们却没跟我提起过。
作者通联:北京西三环中路19号《人民海军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