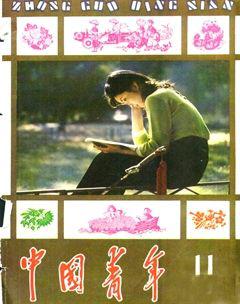不出国的留学经历
张奔斗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南京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共同创办的教学、研究机构.经过严格的考试,我有幸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充分感受了一段——
发言不需要举手
从小学开始,我们接受的一直是“举手发言”的教育。举手成了发言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而且,要等到老师提问后才能举起手。而在南京大学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上课,这一点就行不通了。
为中国学生授课的美国教授多数是第一次面对中国学生。他们对中国学生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他们太安静了,他们听懂了吗?可我分明看到一些表情疑惑的脸……”而中国同学之间在课后也常有这样的对话:“喂,关于某某部分的内容,你听懂了吗?”“我也没听懂,我看你频频点头,不时冲老师微笑,还以为你听懂了呢!”
时隔不久,教授们了解到中国学生“上课打断老师授课是不礼貌”的理论,几位“不甘寂寞”的教授在课堂上表示:任何一位如遇到听不懂的地方,请立刻向我提问。请相信你不是这个教室里最笨的人,如果你听不懂某个问题,一定还会有别人也听不懂的。你们渴望弄懂我教的东西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有了这样的表示,同学们的胆子大了起来,我们或流利或不甚标准的英语在教室里渐渐多起来,而发言也从提问转向对教师授课内容发表自己的观点。特别是下半学期,我们仗着英语说得比较“溜”了,有时还就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教授呢?这时往往站在角落里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吵”。在美国教授看来,上课不应是一个单向传授的过程,而应是一个双向、甚至多向交流的过程。到了期末,我们这帮原本被评为“过于安静”的学生被一位教国际关系的教授说成是他“遇到过的思维最活跃的学生”。这话听得我们很得意,想想这一年来提出过的那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和观点,这些教授留在美国恐怕也没机会听到吧! “千万别忘打引号”
大学4年,大大小小也算写了不少论文。写论文的记忆虽然算不上美好,可也不至于痛苦,因为事情来得挺容易:先找出一大堆别人的文章,搜刮出其中精髓,拼拼凑凑,再加上些自己的观点,便成了一篇自己的论文。有时也会觉得不安,好像自己是频频“站在巨人的肩头”,却没告诉老师这些巨人都是些谁。时间一长,这种不安也淡化了。“天下文章一大抄”,古时的秀才不是早就总结过嘛!
可这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就行不通了。“不得抄袭”被写在中心《教学手册》的显著位置,每位美国教授也反复强调:偷窃别人的思想与偷窃别人的财富无异。我们那不苟言笑的历史教授伸出两只长长的胳膊,食指和中指作引号状,声音冷酷得能结成冰:“当你引用别人的观点时,请永远不要忘记打引号,偷窃别人的观点比偷窃别人的钱更可耻!”
那么,什么情况下该加上那4个小点呢?首先,当你原封不动引用别人文中的话时,请打引号;另外,当你用自己的话叙述别人的观点时,请打引号:还有当你使用某个学者发明的一个新词汇时,也要专为这个词打上引号。那么,何时可以省去引号呢?我们的国际关系教授说:“只有写诸如《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之类众所周知的事实时,你才不用打引号。”历史教授更绝,他的标准是:“当你不清楚某句或某段话是否该打上引号做注释时,那就说明你该为它打上引号。”
打上引号,就得做注释:注明引号里的话是谁说的。如果是摘自书籍,就要注明书名、出版社名、出版年代、第几版、第几页;如果摘自报刊,还要注明是哪年哪月的哪份报刊。写论文时,每位同学都在计算机上小心翼翼地频繁敲打着双引号键,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一篇15页的论文常常是满目引号,一般有60到70个注释,文章末尾还拖着长长的一串参考
书目。引号多得让我们都不好意思,教授们则很满意。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引用别人的观点和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矛盾,你可以引用别人的话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在这样的论文里,别人的观点仅是论据,而论点和论证的过程都是自己的。这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是清楚地说明了这些“巨人”都是谁,无剽窃之嫌;二是要求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哪些是你的,哪些是“巨人”的,泾渭分明,一目了然。 “坐法”里面有“说法”
在中国大学课堂,有一个普遍现象——学生爱从教室后面往前坐,往往教室的后几排坐得满满的,前几排却空空如也。我们把这“遗风”带到了中心。教授们被我们搞得大惑不解,指着前几排空座位说:“这里听得更清楚,为什么不坐在这儿?”我们互相看看,谁也不动。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位置,尤其是当我们还没来得及看完教授布置的阅读材料时。因为按照规律,坐得越靠前,被提问的可能性越大。
可时隔不久,我们就发现,不挪窝不行了。因为在教学大纲上,几乎每门课的总评成绩都有20%取决于课堂表现。想得到好成绩,就必须“表现”,想“表现”,就得坐在教室的前面。我们得多提问、多发言,争取让教授多多注意我们,坐在前几排无疑是很有效的方法。再说,教授讲得投入时往往越说越快,坐在前面至少也能补救一下我们不太灵光的英语听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同学坐位的前移,有人还对此作了哲学思考:爱坐后面是“防守型坐法”,坐在教室前面则显得更有进攻性。
图书馆的坐法也很有意思。图书馆有两种座位:一种是大桌子,可供4个人同时使用;一种是用木板隔开的小桌子,坐下来互不干扰。一般都认为美国人讲个人主义,中国人信奉集体主义,可从中国同学和美国同学在图书馆的坐法看却恰恰相反:中国同学喜欢选择隔开的小桌子,各干各的;美国同学则喜欢坐在一张大桌子上,有良好的学习氛围,遇到不懂的问题还可以相互讨论。不过,如果讨论声音过大,就要受到别人的“注目礼”了。
最后期限没商量
“最后期限”这个词在英文里叫“deadline”,“dead”是歹亡之意,“line”是指线、界限。合在一起真是准确至极——过了期限你就死定啦!
在中心,很多事情都有个“dead一line”。中心组织学生外出游玩,每次的出发时间都是铁板钉钉,不容更改。一次到了开车时间还有同学没来,带队教师手一挥:“开车!”——自己不守时,责任只能由自己承担。
少玩一次没什么,有时要是不守时亏可就吃大了。中心的“deadline”要求最严的是交论文。每门课的教学大纲上,都写着论文必须在哪月哪日几点之前交,有时甚至精确到了半点钟。准确而冷冰冰的数字里透出的是不容商量的意味。论文晚交了有什么后果?老师根本就不会看,而你这次论文也没有成绩。
我们的经济学教授,一开始疏忽大意,在论文递交的最后期限上只注明了哪一天,没说明是几点,立刻被我们抓住了机会:“夜里11点59分还应算是那一天啊!”教授愣了一下,立刻笑容满面地说:“好,那我就那天晚上12点打开我的信箱收你们的论文,在这之后我可不再收你们的论文了。”
中心的机房,10台IBM计算机24小时开放。每学期未的“论文旺季”,夜里3点机房里坐得满满的是常有的事。最紧张时,要一大早爬起来到机房在“计算机预约单”上预约,才能抢到一个机位。机房里经常有这样的对话:“喂!你在写哪一篇?”“美国经济问题,星期五晚上12点前交。你呢?”“我在写历史论文,下星期一下午1点上课时交。”“唉,快打字吧……”
“deadline”改掉了我们不少人懒散的性格。想当初在大学写学年论文,一些同学没能按时完成,跟导师一说,一般都会获准拿到暑假去写,下个学期再交。在中心,可没这等好事。
意志比聪明更重要
刚进中心时,中方主任的一席话引得台下女生一片惊呼:“别看你们现在白白净净的,一学期下来,脸色可不会有现在这么好了。尤其是女同学,你们会变得很憔悴。”
主任说得没错。第一学期心里没底,除了吃饭、睡觉、上课和少量的聊天外,其余时间几乎都泡在图书馆和机房。倒不是自己多用功,而是不这样的话,学习任务就完不成。教授布置的阅读材料非常多,有时一天要看100多页密密麻麻的英文原版书。加上很强的专业性,读起来真是吃力。没办法,只有多花时间了。中心流行一种说法:这里1年的学习量,相当于中国的研究生院3年。
最惨的是期末,不仅有考试,还有几篇大论文。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作息表都有。我第一学期未有段时间是这么过的:吃过晚饭歇一会儿,从7点开始写到夜里1点过,吃点东西,再继续写到5点多。然后睡到中午12点起床,吃过午饭后继续写到下午4点多,锻炼1小时,洗澡、吃晚饭。这在当时的中国同学中是一种比较流行的作息方法。在万籁寂静的夜晚,在桔黄色的台灯下,孤独地写啊写,似乎永远写不到尽头,“为什么我要跑到这里来”的动摇会乘虚而入。但经历过的人,都会说:“这一年受下来,以后就没有吃不了的苦。”
学习已经很紧张了,很多同学还自己“找罪受”。上学期末,因为机房机位紧张,教授说论文不必打印出来。可仍有相当一批同学半夜里去占机位将文章打印了出来,因为这样干净、整洁。中心里十分聪明的学生并不多,我甚至觉得还没有我中学的那个班多,但这样做事认真、力求完美的人却不少。我也常常想,一个坚强的意志要比一个聪明的大脑更是成功的必备品吧!尤其是当我们渐渐长大、成熟时,聪明就更不应是我们唯一赖以生存的东西了。 责任编辑:邱四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