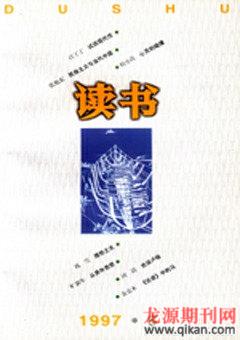政治社会以什么方式来治理?
吕 嘉
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政治就凌驾于社会之上,直接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许多明智之士对政治敬而远之,隐身山林。但亦有崇尚理性力量的人们,始终孜孜以求那至善的目标: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政治形式。在数学家刚刚发现勾股定理的时候,哲人就已系统研究什么是人类的“理想国”了。可几千年过去了,人类理性仍在政治迷宫的门外彷徨。政治学,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学科,目前仍算不上是一门科学——一个可以对其所研究领域的现象做出正确解释与预测的知识体系。更令人感慨不已的是,在人人皆可自由驰骋的理性世界,那些见人所未见,知人所未知的哲人却常常是最孤独寂寞的!他们有幸瞥见政治本质的神秘之光,又往往不为社会所理解,甚至为人们所误解。真是“高处不胜寒”啊!
卢梭就是这少数幸运而又不幸的哲人之一。
卢梭的睿智与不幸,都与他的“公意”理论相关。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政治目标。社会公众和绝大多数政治学者都真诚地相信:人民,即所有社会成员,最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凡涉及全体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都应该听从全体人民的选择。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公意”理论,却提出了对民主制度的另一种看法。卢梭认为,一当人们组成政治性的社会共同体,这个社会也就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单个公民意见的总和——众意——之外的“公意”。这个“公意”以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为依归”,而且“永远是公正的”。而单个公民意见的总和,即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并不能表达出人民真正需要的东西。卢梭的看法是:“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楚幸福。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公意与众意一致的情况极为罕见。因此,人们很难自己管理好自己。他断言:“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对于人类来说,“最好而又最自然的秩序,便是让最明智的人来治理群众,只要能确定他们治理群众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公意”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是全体人民自由、幸福的保障,“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于是,很多学者指责卢梭实际否定了民主,认为卢梭的理论给予专制统治者一种方便的借口:臣民只关心个人私利,唯有他代表公意,从而有充分的理由强迫不顺从的臣民服从他的专制统治。有人断言:卢梭理论的“最终目标是为专制政府提供理论基础”(阿·库·穆霍帕德希亚:《西方政治思想概述》,求实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146页);罗素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版,第225页)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卢梭是反对专制的。他称人们缔结契约,结合为一个共同体的目的,就是“以全部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结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并且像以往一样自由”。人民作为这个集体的所有结合者,就是这个集体主权的所有者。人民主权不可转让和分割。立法权属于人民,“法律不过是社会结合的条件。服从法律的人民就应当是法律的创作者。”行政权力也属于人民,它的受任者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
反对专制的卢梭,为什么又主张由最明智的人治理群众?这是因为,他发现了现代政治社会的内在矛盾:这个社会的建立,是为了所有利己个人的共同利益;而这共同利益又与每个利己个人的实际利益相对立,只能凌驾于这些利己个人之上。
卢梭的深刻就在于他认识到:政治社会的共同利益,只是使这些利己个人得以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条件:既保障每个利己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和权利,又使他们之间必然的利益冲突保持在一定秩序的范围之内;而绝不是他们切身利益的总和。他说:“个人利益远不是与普遍的福利结合在一起,反而在事物的自然秩序之中它们是彼此互相排斥的”。现实告诉我们,在市场条件下,犯规是个人谋取暴利的捷径,但一旦所有人都犯规,市场也就不可能存在了,社会也就陷入无政府状态而无所谓公共利益了。现代社会是由利己的个人组成的,他们的共同利益,就是使他们得以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条件——强制规范个人利益,使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时必须有所不可为。而要做到这一点,体现公共利益的“公意”必然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
“众意”很难达到与“公意”一致的地步,是这个利己个人组的社会的正常情况。如果社会成员都囿于个人的私利,他们就很难考虑超出个人利益之外的事情,很难表达出这个建立在对抗之上的政治社会真正需要什么。即卢梭所说:“人民永远是愿望自己幸福的,但是人民自己却并不能永远看得清什么是幸福。”因此,体现政治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公意,就像高深莫测的自然规律,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发现。
卢梭的另一不同凡响之处,是他的“社会危机导致社会契约”的理论。卢梭思想中蕴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囿于私利的芸芸众生所以能明智地共同缔结社会契约,创立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条件,是由于这样一个特殊前提,众意与公意一致的特殊条件:社会危机。卢梭说:“我设想,人类曾经达到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被消灭。”这样,这些本性贪婪的人们就必须“寻找出一种结合的方式”——缔结社会契约以解决他们所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
政治社会的社会共同利益,只是使利益相互冲突的人们得以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条件。它不像个人的、集团的特殊利益,有着具体的、直观的形态。正所谓“大象无形”。尤其是在人们之间的冲突还不尖锐,社会生活还未陷入危机的时候,人们看到、想到的就只是自己的特殊利益,以及与自己利益有关的各种特殊利益。社会的共同利益隐而不显。只有当人们的生活因相互之间的对抗而失去了秩序,所有人的生存都面临危机的时候,维护某种社会秩序才开始显示出其凌驾所有社会成员特殊利益之上的共同利益的性质。因此,人们常常只有在社会危机时才能感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存在,才被迫超出个人利益的局限,去思考有关社会共同利益的政治问题,并趋向于形成某种共同的认识。萨拜因有一句名言:“政治哲学著作的大量问世,是社会本身正在经历艰难困苦时期的确实征兆。”(萨拜因:《什么叫政治理论?》,詹姆斯·A·古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编:《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九年版第11页)很能说明问题。
卢梭察觉到政治社会的另一个矛盾是:人民缔结社会契约,组成政治社会,是为了解决个人所不能解决的社会危机,并保护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由和平等;但是,政治社会得以维系的条件只有少数人能够知晓,由这少数明智的人治理社会是最合适的;而任何人都是有局限的,即便不是出于私利,掌权者也并不总能时时刻刻遵循公意,而易于违背人民的利益去滥用权力。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卢梭设想的基本途径是“人民主权”:而人民权力的存在形式就是民主制度。卢梭认为:民主制度可以比其他政府体制能够选择出更好的执政者。
共同利益的对政治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正确认识它的艰难,使得政治社会的兴衰与其政治领袖的个人因素——才干大小,所确立的治国纲领正确与否等——息息相关。即如卢梭所说:“公意永远是正确的,但那指导着公意的判断却并不永远都是明智的。”如果政治领袖的才干不逮,难以正确把握“公意”,不能以它为基础制定正确的决策,政治社会的发展就会停滞,就会陷入危机以至崩溃。同样,政治领袖具有雄才大略也并非总是好事:政治领袖“由于滥用他那过多的才干而给人民造成的不幸,也并不亚于一个能力有限的君主由于自己缺乏才干而给人民所造成的不幸”。可以说,政治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人身系天下安危的社会。卢梭举例:“如果由于某种幸运的机缘,一个天生治国的人物居然在一个几乎被一群矫揉造作的执政者们弄得举国陆沉的国君制里执掌了国政的话,他所发挥的才能一定会使人们大为惊讶:这就会给那个国家开辟一个新时代。”历史与现实中的无数事例都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政治领袖在治国方略上失误,必然导致国家、民族的灾难;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也往往肇始于新的政治领袖及其所倡导的新的政治思想的崛起。对此,卢梭从比较中指出了民主制度的可取处。他说:“有一种最根本的无可避免的缺点,使得国君制政府永远不如共和制政府,那就是:在后者之中差不多唯有英明能干的人,公共舆论才会把他提升到首要的职位上来,而他们也会光荣地履行职务的;反之,在国君制之下,走运的人则每每不过是些卑鄙的诽谤者、卑鄙的骗子和卑鄙的阴谋家;使他们能在朝廷里爬上高位的那点小聪明,当他们一旦爬了上去之后,就会向公众暴露他们的不称职。”
民主制度可以制约权力的滥用。当政府滥用权力,使“最卑鄙的利益竟厚颜无耻地伪装上公共幸福的神圣名义”,当君王以公共的利益为借口而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的时候,“公意”就沉默了。此时,唯有人民民主才能重新恢复人民的主权者的地位,重新将社会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对此,卢梭设想中的民主,是选择政治领袖与政府形式的方式,而不是达到政治领域的真理的途径。
对政治社会的深刻认识,使卢梭对任何政治形式都心存忧虑:“只要政府的职能是被许多的执政者分掌时,则少数人迟早总会掌握最大的权威。”而民主使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充分汇集于政治决策领域之时,又极易于伤及社会的稳定与秩序。他的论点是,“没有别的政府是像民主的政府或者说人民的政府那样易于发生内战和内乱的了。”他告诫人们:“在这种体制之下,公民就特别应以力量和恒心来武装自己,并且在自己的一生中天天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背诵着一位有德的侯爵在波兰议会上所说的话:‘我宁愿自由而有危险,但不愿安宁而受奴役。”
研读《社会契约论》,深感卢梭的逆耳之言比任何有关民主制度的空洞赞美都更有意义。问题是,只要人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和矛盾,政治权力就只能凌驾于社会之上,民主政治亦不例外。否则,民主就意味着无政府状态。我们需要民主,但更需要知道民主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社会契约论》,[法]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年二月修订第二版1.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