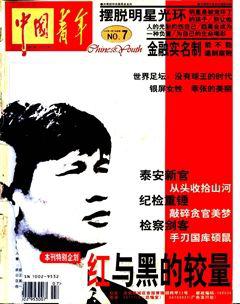田头,那座盖满花圈的新坟
耿海亮 黄新军
蒲草编圆了童年的月
夏天,河南固始乡下的夜色是很美的,人声已经散尽,只有断续的蛙鸣。菜花开过,麦子已经抽穗,门前的水塘边,桃树和梨树都已经挂果,潮暖的风吹过来,夹杂着一股淡淡的柴草的烟气和嫩嫩的果香。
9岁的程广惠坐在自家土屋的门口,借着月光编蒲包。
把命运和土地联在一起的庄稼人,无心体会乡村夜色的美丽,更何况是一个9岁的农家女孩子。从记事起,她家里就是这个样子,父亲有心脏病,母亲患胃病,一年中有半年两个人是在病床上度过的,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哥哥还不能扛起田里的活。在靠出劳力挣工分分口
粮的日子里,在已经很贫穷的农村,这个家的日子就格外的艰难。
金黄的蒲草叶在程广惠长了一层茧的小手间飞跳着。小广惠一年前,就和邻居的大婶们学会了这门手艺,她也是村里最小的会编蒲包的孩子。一个蒲包可以赚四五分钱,她一早一晚可以打两个。在1972年,这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卖三个蒲包就可以买一斤盐,这样就可以让家里的野菜汤再多一点味道。
今天的月亮真圆,程广惠抬头看看天,手里的活没有停下来,作业赶在天黑以前就已经做完了。去年春天,已经断粮好几天的家里,怎么也找不出一块五毛钱的学费,是母亲带着她,哭着挨家挨户地借钱,才凑够的。今年不用借了,自己就可以挣出来了。自己是班里学习最好的,还是班干部,今天老师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广惠这孩子有出息。”想到这,她又忍不住笑了,活动活动有些酸胀的手腕,接着挑起一根蒲叶。“广惠,快些睡吧。”母亲在里屋叫她。“哎。”她应了一声,手里的活没有停下,睡前,她要把这个蒲包打完。
没能拿出来的录取通知书
小孩子并不在意日子是苦是甜,一切就如同她手中的蒲草叶,虽然涩,但轻折几下也就滑过去了。
门前的桃花倒是年年开,只是父母亲依然旧病缠身。哥哥虽然能干一些田里的活。但一个劳力的工分分得的一点点口粮,分到四张嘴里,稀米汤也常常要断顿。
那是1978年,那年她已经16岁,上初中了。
鸡还没叫头遍,程广惠就已经起床了。她把屋里屋外打扫一遍,然后给父母和哥哥做早饭,趁空,再给笼子里的兔子喂上一把青草。待大家都起来,吃过饭,太阳才刚刚从东边探出头来。这时,她就该背上书包到几里以外的学校去上学了。如果是雨天、雪天,她还要到后院邻居家去喊一嗓子:“照才,上学喽!”随着喊声,那个叫曾照才的男孩就从家门里一瘸一拐地走出来。照才腿脚不灵,遇上坏天气,上学放学,广惠总忘不了照应他一下。
上初中后,除了编蒲包外,她又养了20多只长毛兔。每年年底,卖兔子的钱,她要存起来。父母的药钱、家里的油盐酱醋、自己的学费、笔、本都要从这里出。她还要替几个筹不到钱的同学交学费。
她是全校唯一不上晚自习的学生,家离学校并不远,才三里多,放学路上她要给兔子打一捆草,家务得在天完全黑下来以前干完,这样就可以就着天光写作业。油灯能不点就不点,灯油在她家里也是一件必需的奢侈品。
龙井村的程广惠聪明、成绩好是出了名的:数学竞赛是全乡第二,语文、数学、外语联赛是第一名。
老师说:“等着你上高中,考大学。”
那天,她几乎是一路从学校跑回来的,一进院,把手里的草一扔,就奔进屋里:“爹!妈!……”
父亲半卧在床上,母亲从屋外走进来,他们似乎并未留意女儿兴奋的神情:“广惠,跟你说件事。你哥要分家单过了,明天就搬出去……”
广惠觉得胸口一紧,也许是因为草屋里见不到一点太阳,刚才头上热腾腾的汗,一下子变得冰凉。哥哥已经结婚,分家是早晚的事。但她没想到这一切会来得这么快。这就是说,她要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力去挣工分,换口粮,也就是说……
伸进书包里的手,又慢慢地掏出来,空空的。她刚才还以为能一扫这小屋里的阴霾的那张盖着大红印的纸片,无力地蜷曲在书包的角落里。
那是录取她上县高中的通知书。
晚上,程广惠把书包刷洗干净,连同那纸录取通知书,平平整整地放到衣箱的最底层。
第二天早上,她给父母做完饭,从门后拿起镰刀、扁担,下地去了。
老汉的药是和着眼泪喝下去的
田里的小麦刚刚返青,油菜苗嫩生生的,看得人心里发痒。程广惠站在田埂
上,心里默念着,但愿今年有个好收成。
她结婚那年,村里开始搞承包,她和丈夫董长贵分了3亩多地。但土里刨食过日子太紧巴。除了和丈夫在田里干活,她又养了十多只鸡、鸭、鹅,三头猪,一头牛。
买猪崽、牛犊的钱是借的,春播买化肥的钱还得借。毕竟是四壁空空的一个新家,两个穷人。两人住的草房,还是好心的乡亲们你出料他出工为他们盖起来的。
身上背着债,一年也就很少敢沾一点荤腥,如果不是来了什么贵客,鸡是舍不得杀的。鸡蛋、鸭蛋是换油、买盐用的,孩子也难得吃上一口。到了年底,三头肥猪卖出钱来,还了年初借下的债,留下来年买猪崽的钱,也就剩不下什么了。第二年开春,可能还得借债。
每年春节前,到集上转一圈,回来,她什么年货也没舍得买,但总忘不了给婆婆买一件褂子。结婚十几年,她几乎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
日子虽然清苦,夫妻俩倒是过得和美,十几年了,拌嘴的时候是有,但绝没有像别人家那样吵闹过,倒是广惠要常常东家西家地劝架,大半夜还要一个人追出十几里路,去寻邻居那叫嚷着要跳河的媳妇。
村里几户单过的老人,平日里也少不了她的照应,有点什么重活,或是生了病,不用叫,广惠自己就来了。
那年夏天,后院70多岁的申广日老汉得了肠炎,疼得在床上直打滚,是她借了辆自行车,顶着大雨,来回三十多里路去乡卫生院给他买药。药刚买回来,又发现老汉连屎带尿拉了一床。邻居们都不愿上前,又是她二话不说,不顾脏臭,放下手里的药就给老人擦身子,换洗衣被。老汉只能一声声地叫着“好闺女”,药是和着眼泪喝下去的。
1986年,程广惠的第二个儿子刚满8个月,她听人说,村里的孤老头黄庆发,抱养了一个还没满月的女孩,没有奶水,怕是养活不了。一个也是吃,两个也是吃,自己有奶总不能看着别人的孩子饿死。程广惠把那孩子接到了自己家。
但家里的米缸快要见底了。每年青黄不接时,家里都会断粮十几天。那段时间,每天只有中午才能吃上一碗清得数得出米粒的稀饭。而就是靠这一碗稀饭,她要干一天的农活、家务。晚上,又累又饿的程广惠早早就得给两个孩子喂最后一遍奶。
孩子喂饱了,天还没黑透,她就得睡下。倒不是困,断粮的日子就得早点睡。睡着了,自己就不知道饿了。
她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
今年1月5日,养猪十几年的程广惠第一次杀了一头猪。十几户邻居都被她请来了。
这是乡里的民俗。哪家杀了猪,就要把邻居请来,吃一顿猪肉。她养猪十几年了,都是年底卖钱,还债养家了,还从来没舍得杀过一头。在村里,能请人吃“猪晃子”,也是家境殷实的的象征。毕竟,这两年日子已经稍稍宽裕了。
3年前,丈夫到邻村的砖场学烧窑。丈夫早出晚归,一天到晚扑在窑场上,她则担起了家里的全部农活,种地,养猪,还要照顾老人、孩子。现在丈夫已经当上了窑场的烧窑师傅,每个月可以挣400元钱。今年开春不用再借债了,苦日子算熬出头了!
晚上,长贵陪着十多个邻居,围坐在饭桌旁。一声“干!”杯一举,酒香、肉香伴着邻居们的笑声就在他家的小院里弥散开来。女人是不上席的,程广惠屋里屋外地忙活着。
乡下难得有什么热闹看,不知什么时候,屋外围过来村里的二十多个孩子。“过来,吃点肉!”广惠给每个孩子一勺饭,一碗肉,分到最后,孩子太多,碗不够了。以前是碗里没粮,现在是肉多了没有碗,广惠笑了,她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
十多个男人加上二十多个孩子,把半扇猪肉吃得连汤带肉剩下不到两碗。广惠又汉把这两碗肉端给一直没上桌的母亲和两个孩子。“你也过来吃一点吧。”母亲叫她,“忙了一天了,怎么也得喝口汤吧。”“不了,您吃吧,一头大猪还愁没我吃的?”广惠又和丈夫去分剩下的半扇猪了。这块带给婆婆,那块留给妈。还有几块明天给村里的几户老人送去,他们也没养猪,快过年了,也让他们换换口味
十多年来,程广惠就杀了这么一头猪。她千瓢食、万勺糠辛辛苦苦喂大的猪,到头来,自己连一块肉也没吃上。
酒席间蒸腾的热气在草房的土墙上结成一层白霜,那天夜里,天很冷。
血,在黎明前流尽
第二天,跟平日一样,程广惠又早早
起床给长贵做好早饭。他还要到窑上去。
送走丈夫,见天还没亮,程广惠又躺下了,忽然间,她听见外面有人喊:“救命啊!杀人啦!”
她忙翻身下床,连棉衣都没顾上穿就冲出门去。只见30多米外的打谷场上,两个人影扭打在一起。其中一个人正拿着尖刀往另一个人身上乱刺。那被刺的人是隔壁的邻居吴老汉。
“别扎了!再扎就把人扎死了!”情急之中,程广惠喊出了这么一句。
那杀人的一惊,停下手,转身便跑。“杀了人还想跑?”她又喊了一句,猛地冲到谷场上,迎头拦住杀人者的去路。那人没想到这个女子居然敢挺胸站在自己面前,一时竟愣住了,趁这个功夫,广惠一伸手就抓住了他手里的刀:“来人哪!抓强盗啊!”早已经杀红了眼的歹徒,这才缓过神来,刀往回一抽,又猛刺过去……一刀、两刀、三刀……他再转身要逃时,那个浑身是血的女人竟又扑过来,死死地抱住了他的腿………
没有人知道纤弱的广惠哪来的气力,一个人和那个狂兽一般的杀人犯拼斗了20多分钟,据说那个入室行劫杀人的歹徒被捕后在公安局里挣断了4副新手铐。
循着呼喊声,邻近村庄的村民们赶来了。躲在厕所里的歹徒被愤怒的村民用铁锹、棍棒打翻在地。
浑身是血的广惠和吴老汉被乡邻们抬上架子车,推往15里外的乡卫生院。
一路的花圈,刺痛了3000多双含泪的眼
身上挨了7刀的吴老汉躺在医院里,已经获救。
程广惠回来了,还是躺在架子车上,只是两只眼睛睁着,一直没有闭上。送到乡卫生院时,她身上的血已经流干了。医生在她身上找到了11处深深的刀口。
当年为她垒起草房的乡亲们又含泪为她搭起了灵棚,灵棚搭在她家的小院里。青幔白花下,32岁的程广惠静静地躺在十几年前为她母亲打造的棺木里。
棺木旁跪倒的是丈夫、两个儿子,和她用奶水喂大的那个小女孩。
停灵三日,龙井村里的哭声没有断过。
盖棺了。董长贵几次要冲过去推开那张隔断阴阳两界、碾碎骨肉亲情的厚重的木板,都被乡邻们拉住了,人们只能听见他轻轻地念叨着:“不是说好一起走的吗,怎么你就先去了?”
三个孩子一声声“妈……”“妈……”断人肝肠。
广惠的老母亲更是哭得在棺材前打滚,泪水和着地上女儿的血:“我的儿啊,我的棺材里咋装的是你呀……”
1996年1月8日。天色似乎已经被冻得凝住了,一直是阴沉沉的,没有风。一幅白布制成的挽联悬挂在龙井村村部门前:“烈女忠义,血染红尘联广宇;故里伤情,泪洒胸襟哭惠人。”
张广乡政府今天为它的村民程广惠开追悼大会。
没人召集,一大早,方圆十几里各乡的3000多人,就聚集在村部前的谷场上,麦地里。
广惠的亲人们来了。广惠的乡邻来了。更多的是与广惠素不相识的人,他们来,只是听说一个好人走了,来给她送行。
乡党委书记致的悼词,断断续续地被自己的抽泣声打断。
广惠的灵柩被乡亲们从她家的院子抬往她的墓地,浩大的送葬的人群,慢慢地无声地走过她平日里走过的乡路。坑坑洼洼的乡路,今天似乎变得平坦了。好人走了,绵延一路的花圈,刺痛了3000多双含泪的眼。
好人怎么就走了呢?
如今,村里的那条小路有了一个名字:“广惠路”。从村口进去,走不远,路边就是广惠家的草房,再走不远,路的尽头就是广惠的责任田。黄黄的菜花开得正盛,田头是一座盖满花圈的新坟。
小路不长。
采访过程中,我们一直没有见到住校上学的程广惠的两个孩子,回京后,我们收到了他们的来信:
亲爱的叔叔,上周你们从北京赶到我家,来看望我们。真不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叔叔,妈妈被那坏人杀死了,我们兄弟永远失去了母亲。现在我们都不敢回我们家的草房住,妈妈就被那坏人杀死在那儿,地上都是妈妈的血呀……
妈死后,政府给俺家很大的关怀,领导们经常来我家,叔叔阿姨们也不断来看望我们。我们一看见人家的孩子都有妈,而我们没有,就想哭,我们好想好想妈呀!
我们一定听叔叔的话,做个好孩子。
祝叔叔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被坏人杀死的程广惠的孩子董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