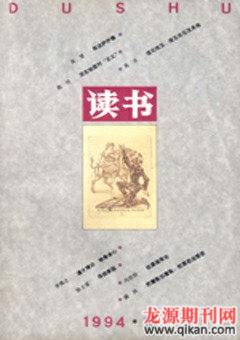旧事重提说“话本”
陈午楼
《文史知识》一九八八年第十期载施蛰存先生《说“话本”》一文,系针对日本汉学家增田涉在一九六五年发表的《论“话本”的定义》而发。施先生说增田涉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国外和台湾学者的热烈讨论。这些讨论文章,他无缘见到,他得知这一信息,已是一九八二年的事了;到一九八八年他才看到增田涉《论“话本”的定义》台湾译本的摘要。
施先生在文中介绍增田涉对鲁迅首创的、向来为中国学人所沿用的“话本”的定义,提出了疑问。施先生认为“话本”的意义是各式民间演唱艺人所依据的底本。
国外和台湾学者讨论此事的文章,我没有见过,无法参加百家争鸣。但距增田涉发表关于“话本”的论文三十二年前我发表过《说书有无脚本?》一文,涉及到“话本”定义的问题了。要说明的是:我的论述,并非来自任何文献,而是依据多年亲自调查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或称“活资料”。
我认为“脚本”既“无”又“有”。先说“无”,后说“有”:
五十年代初期,我向好多老艺人请教过,一致说没有脚本,完全是口传心受。这口传心受的方式,便是逐字逐句地教,表情、姿态,一样一样地学。这种传授方法,我亲见过。每次只教几句而已。口传心受的学艺方法是艰苦的,但基本功却打得扎实。学成之后,登台献艺,则各人按自己才能去发挥、增减。这是“无”,再说“有”。
第一种类型,这些脚本都是手抄本,多数记于旧式帐簿上、纸摺上,或随便一个什么小本子上,且是艺人自记的。由于文化水平限制,故别字、错字、漏字极多,更谈不上合乎语法、修辞、逻辑的规范了,加上字迹潦草,难以卒读。第二种类型,是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艺人,能把从师学来的书词,用工整的小楷全部记下来。已知的有清末的顾玉田自记的《前三国》,民国以后的费骏良自记的全部《三国》、五十年代辞世的郎照星自记的部分《绿牡丹》。等等。
第一种类型的脚本,我见过某说《三国》的老艺人《东吴招亲》残稿,其中引用了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照录之原样):
沼池白地柴芸间千里江临一日还两岸原声堤不住青州已过万重山
一首七绝,十个别字。前辈艺人创书,引用此诗朗诵之意,是为了描写江水湍急;后代艺人虽在台上朗诵,并不解诗意。再看其中一段书词(也照录原样):
赵将军起身到房舱在胸前将第一封锦囊取出保主人洞房花烛为何摆在胸前因为鹤紧为辱沈怕忘却,赵将军将书信取在手中,临神观看,书信上,信面上注得明白,第一封锦囊船抵码头拆看,望两遍记得,外面来人,取火,是,火取来将书信化为丙丁……
上面引用数十年前所见艺人脚本残稿,意在说明脚本面貌,并非对早年失去学习文化机会的艺人在文字上苛求。
第三种脚本类型是提纲式的:记录所说之书有多少回目和大致的情节,每个回目中有哪些“关子”,何处有什么插科打诨,何处加上哪些诗、词、歌、赋、赞。回目包罗全书内容,“关子”则为全书的艺术结构,插科打诨则为制造趣味的材料(以幽默内容为主)。此三者是为一部书的支柱。至于诗、词、歌、赋、赞,多为强调人物性格,或为渲染环境气氛,或为增加趣味性,或作“入话”之用(如《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连引十余首描写春景诗词作为“入话”,引入正文)。
上述三种类型中,不乏互相模仿抄袭者,长期下来,不免形成若干书词的公式化,殊少创新;能创新者在书坛上就能产生影响,以至成名。
艺人们不承认书词有脚本,这是可信的。都强调口传心受,这固属事实,也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某名家嫡派真传。艺人们又承认书词有脚本,这也是可信的。这些脚本的由来,多是前辈艺人为了传之子孙而记录下来的,它是研究说书的可贵资料。在旧时代,艺人保留脚本而不承认有脚本,或是承认有脚本而不肯示人,是防止被人学去。这是关系到饭碗竞争的大事。讳言脚本存在的秘密即在此。
作为研究者,我认为扬州评话的脚本“无”和“有”的情况都存在。从“有”的角度看,我所知和亲见的脚本大体如上述三个类型。据此,则“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这个定义是正确的,不宜再作出其它定义。
不过,施蛰存先生的文章,既不同意增田涉的观点,同时他还对“话本”存在着一个疑问,认为话本只是一个通名,不能成为一种文学型类,并考证出,直至清初,还没有出现“话本”这个名称。
施先生认为“话本”可作“通名”说,论之有据。其据即《都城记胜》、《梦梁录》。后者有言:“凡傀儡,敷衍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拙见以为,学术研究,不但要观其名,更要究其实。建国初期,我做过戏改工作,得知某些地方戏,演的是“幕表戏”,即既无剧本,又无导演,但每幕每场的内容都有个提纲,即“幕表”。其道白、唱词经历代相传,已定型为程式化。如描写山景、村景、出门叮咛语、见面客套语等等,皆有固定的唱词,可长可短,故称“水词”,言其水分多也。施先生引《梦梁录》的话,可能就是指的“幕表戏”这个类型。这恰恰为增田涉误解“话本”定义,提供一个未必准确的论据。我以为,“话本”定义,即作“说话人的底本”解,不宜另生枝节。如须说“通名”,可用“脚本”这个词:一切戏曲、曲艺演唱之底本,不论线条粗细,皆可称为“脚本”。
为某个文学型类(genre)或品种(sub-gonre)下个确切定义是困难的。就“话本”而言,尚有种种演变过程。
一个是文人仿说书艺人的口头文学写出的小说,称为“拟话本”。拟者,仿也。其代表作是“三言”、“二拍”。再一个是,许多明清章回体小说之成书,又大都来源于平话。如《三国志演义》来自“说三分”,《西游记》来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等。经吴承恩等据平话和其它资料创为章回体的专供阅读而非供说书人上台演出的文学作品,只能叫做小说,不能叫做话本了。但存世流传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精忠说岳》、《平妖传》、《七侠五义》,或许加上《金瓶梅词话》等等“正规”的明清章回体小说,仍然保持若干平话遗风,如每一章回的开头是“话说”、结尾留下“关子”,埋设悬念后,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了,以及若干幽默人物、幽默场景、幽默情节、幽默语言,和“说时迟,那时快”等平话语汇,还有那“有诗为证”、“后人有诗叹曰”等抒情韵文的穿插和铺垫。
第三个是,至清中叶,江左人文荟萃的扬州,有许多天才的评话艺术大家,又根据明清章回体小说,另创为长篇评话。其书词记录稿较小说原著扩大数倍、十数倍不等。如《水浒传》原书中关于武松故事约八万字左右,而扬州评话“武十回”录音稿约有一百一十万字,比原书扩大了近十四倍,经整理后出版的本子,仍有八十多万字。这些记录稿,无论出版与否,都只能叫“话本”,不宜称为小说。也有的学人将两者并称为“真本小说”的,如胡士莹教授就著有《话本小说概论》。但这“话本小说”仍然是“说书人的底本”。
从上述三点来看,“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之定义仍然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