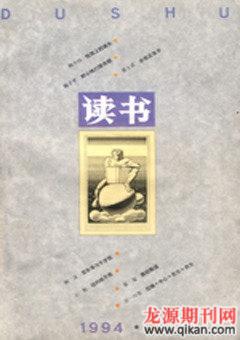离经叛道
张 宽
一场多元文化的论争
美国教育界关于多元文化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论争的焦点之一是西方的文化经典(canon)。而要谈西方文化经典,又必须从大学里的“西方文化课”说起。
美国比较正规的大学里都设立了“西方文化”课程。这个课程,从渊源上说,同美国的国策紧密相关,从时间上则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一八二四年,“常春藤大学”联盟发表了“耶鲁宣言”,认为天降大任于美国,古希腊以来的欧洲人文传统应在美国人身上发扬光大,美国之立国精神和赖以发展的动力,都必须基于欧洲传统文明的价值和理念。为西方文化的传承作出贡献,美国的大学责无旁贷。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曾派出空军参战,飞行员的训练除军事科目以外还设置了“西方文化”课程,表示美国是为欧洲文明而战。一九一九年哥伦比亚大学最早把“西方文明”列为本科生的必修课之后,其他大学纷纷跟进。课程的名称有所不同,构想却基本一致:大学生是文化的承担者,所有大学新生必须熟读一定数量的西方经典作品,西方文化必须在他们身上传下去。
问题是:一所著名大学竟然要挑战这种构想。
斯坦福大学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设置“西方文明”必修课,简称Western CIV。一九八九年以前,它的学生必须在头三个学期内精读至少以下十五种西方经典:《希伯来圣经·创世纪》;《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主要章节;至少一部古希腊悲剧;柏拉图《理想国》一至七章的主要段落;《圣经·新约》节选,至少包含一部《福音书》;奥古斯丁《忏悔录》一至九章;但丁《神曲·炼狱篇》;莫尔《乌托邦》;马基亚维利《君主论》;路德《论基督教自由》;伽里略《星座信息》、《试验家》;伏尔泰《老实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达尔文《选集》;弗洛依德《心理分析纲要》、《文明与不满足》。
八八年初,经过近两年的辩论和准备,校学术委员会决定取消原有的“西方文明”课程,代之以较具有包容性的“文化、理念、价值”课程(Cultures,Ideas,Values简称CIV),作为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新课程的核心阅读书目多了一些弹性,除了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以外,每学期至少必须阅读一部非西方经典,另外还必须用一部经典(作者背景不论)来讨论诸如阶级、种族或者性别问题。如此一来,《可兰经》、《罗摩衍那》、老子、孔子、《源氏物语》等都可能进入必读书目,而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则可以用来研究种族和奴役问题,《包法利夫人》也可以用来探索女性内心世界……。
斯坦福的这一改动应当说是一种建设性的尝试,不料却在美国学术界和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多家重要报刊很快登出一系列煽动性的报道和评论,标题是“被抛弃的经典”,“西方的没落”,“永别了,苏格拉底”,“寻找黑色的但丁”……联邦教育部长贝纳特不辞劳苦从东岸赶来校园,试图阻止新课程的实施;校长肯尼迪在公共电视台上与贝纳特辩论;贝纳特放狠话说,斯坦福的作法将给美国的教育界带来灾难性后果,最终有可能葬送整个的西方文化……
在媒体煽起的那场“文化热”中,三本讨论文化的著作先后成为畅销书,一是艾兰·布洛姆的《美国人心智的封闭》(A11anBloom,The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二是罗杰·金巴尔的《有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Roger Kimball,Tenured Radicals),三是丁尼希·苏瑟的《非自由主义的教育——大学校园内的种族与性问题》(DineshDSouza,Illiberal Education:The Problem of Race and Sex onCampus)。通常情况下学术性的著作难以进入畅销书行列,这三本讨论分析教育界状况的学术性著作居然风靡读书界,在美国的出版史上还是头一次。
金巴尔的书指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作者说六十年代末造反的那一批大学生如今已经四十多岁,他们不少人进入了教育界,获得了大学里的终身教职。这批教授如今的学术活动只是他们当年政治活动的延伸。人文科学所属的英文、法文、比较文学、人类学各系挤满了这样的左翼教授,他们占领了阵地并且要从那里出发,以文化为武器与其心目中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作斗争,他们的目的是改造世界。金巴尔危言耸听地指出,上述的左倾教授的作为正严重地危害着美国的高等教育,人文科学领域的混乱状况都要归罪于这批有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传统的西方经典正在被这一伙捧着铁饭碗的激进派“谋杀”。他们“谋杀”经典的手段,可以是哗众取宠的当代理论,尤其是从保尔·德·曼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此外还有校园里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试图从女性的角度重新认识经典,结果必定是抛弃原有的经典;黑人民权运动来势汹猛,更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占统治地位的白人文化。文化上的新左派已获取了相当高的学术和行政地位,要压制他们的声音已经不可能。一个令人忧虑的事实是近年来人文学科在萎缩之中,选择人文科学为专业的学生愈来愈少,这个现象,金巴尔认为是学生对左翼教授在人文领域进行政治灌输的抗议所致。
苏瑟的书则以近似报告文学的风格来叙述近年来发生在几所著名大学的涉及种族和性别的重大事件。他认为美国一流大学新生录取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倾向,简单说来就是优败劣胜的负淘汰,歧视的主要对象是白种人,有时也包括亚裔。“在同等条件下美洲裔考生被柏克莱录取的概率,比亚裔考生被录取的概率高出百分之两千。”书中煽动性地指出,正是那些占尽便宜的低考分少数族裔学生,在进入学校以后滥用权利,打着反对种族主义的旗号大搞分离主义活动。斯坦福取消“西方文明”课程,主要原因即是学校行政部门屈服于少数左翼学生的无理取闹,校方在分离主义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一味退让,因此新的文化必修课中西方经典大量减少,新的阅读书目荒诞无稽。许多大学“正将荷马、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排斥到必读书目以外。”学校重视非西方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不仅不能稍微纾解校区内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偏狭情绪,反而助长了“分离主义的逆流。”女权主义和少数族裔激进分子成了校园里的“暴君”。学校奉行的“开明”政策,未能帮助营造出一个种族之间互不歧视,多种文化互相融合的和谐氛围。作者进一步认为,女性研究和少数族裔文化研究领域都存在政治背景,学术水准往往不在考虑之中。杜克大学文科各系为了保持和巩固自己在学术研究领域里的“前卫性”,聘用了一批著名左翼教授,在苏瑟看来,也成了一项罪名。苏瑟是十多年前从印度赴美读书后留下的第一代移民,身为少数族裔却猛力抨击少数族裔在校园内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现象颇值得玩味。
布洛姆那本书出版最早,影响也最大——作者日前去世,祝福他在天的灵魂。该书出版有个小插曲:作者原是芝加哥大学古希腊哲学教授,学术声誉平平,跨行当写了一本研究美国当代校园文化著作,出版商还不敢轻易接受。直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答应写篇短序,出版商才决定印两千本试试。岂知书一出版立即风行全国,一版再版,连续半年多列在《纽约书评》畅销书榜上。本书可以被看成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对二十余年来大学校园里的自由化倾向的一场系统清算。布洛姆在书中严厉抨击了校园内成为时尚的“开放性”(Open-ness),他认为正是这种所谓的“开放性”造成了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美国的大学生们对自己的政治文化遗产要么知之甚少,要么冷嘲热讽,取玩世不恭态度,学校成了诋毁亵渎自己传统中固有价值的场所,这样的地方,决计无法培养出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合格公民。美国的大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由“开放性”导致的相对主义价值观从根本上取消了教育的原本目的,即追求真理,追求美好的生活。“开放性”在外来文化和非主流价值观的冲击面前,已经成了“盲目信仰主义”、投降主义的代名词。传统主流文化由于校园内相对主义盛行不再彰显,所谓的“大开放”实际上反而导致了美国青年学生心智的大封闭。现在的大学生,无论是价值取向还是行为模式,无论是艺术趣味还是道德情操,与作者年轻时的那一代人比,相差何止万里。他们所吸收的精神食粮,从摇滚音乐到好莱坞出品的流行影视,从《花花公子》到《今日美国科学》等浅薄的书刊,差不多都应该归入没有价值的垃圾一类。美国校园里的思想混乱状况与近代德国哲学中以尼采为代表的虚无主义思潮有联系。德国的虚无主义到了美国以后,从哲学课的讲坛和书本中解放了出来,其影响力不仅控制了大学校园,而且超出校园浸染到民间。抵制虚无主义思潮侵蚀的最有力武器,照布洛姆的说法,是西方文化经典,通过阅读从苏格拉底到维特根斯坦,从荷马到乔伊思的西方文史精品,可以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心胸开阔、理智健全、沉稳刚毅、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现代国民。学校应该坚持西方经典作为学生必须修身课,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尽可能多读原著。不要用似是而非的新观点、新方法对作品进行阐释,伟大的作品只“等待读者去读它们”(by just reading them),“要像作者所希望的那样去读”。阅读经典是灵魂的畅游,是智力的训练。作为人的存在的意义,在他看来,与阅读伟大作品似乎是密不可分的。
这三本书,特别是布洛姆的那本,提出了一些问题,如认为美国的教育在走下坡路,是值得注意的。但是,这几位作者却把原因归结到“开放性”,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事实上,八十年代中后期,共和党的里根、布什主政,意识形态领域的保守主义思潮高涨,上述的三本书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起了读书界广泛的兴趣。而斯坦福大学在这时候酝酿修改原有的“西方文明”课程,试图稍向左转,表现出多一点宽容和多元,明显是逆潮流而动,难怪要激起一阵风浪。
在围绕西方经典的这场论战中,传统派的代表作除了上述三本以外还有荷希的《文化遗产》(Hirsch,E.D.Jr.,CulturlHeracy)和许多散见在刊物中的论文。传统派坚持西方经典的“至尊”地位,其基本论点可以归纳如下:
●一部作品成为经典有一定标准,这个标准可以是作品的智性品质(intellectualquality),也可以是作品在文化史上的影响。作品的品质涉及到理性、知性、真实性、准确性等。作品品质的高低虽然无法用数学方法测量,仍然有一定的客观标准,绝不是随意的。有一个叫作“客观实在”的东西独立于人们的话语之外,同时又和话语相对应。既然有客观实在,真实性和客观性就是可能的。在西方,现实主义的传统屡屡受到挑战,却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现代自然科学即以这种客观实在为依据。
●经典具有提升人类心智的功能,它帮助读者超越环境和地域给他们的限制,引导他们从狭隘走向博大。而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具有更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唯有将个人放到最具普遍意义的人类文化(西方文化)中,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人之为人的智性潜力。
●知识分子应该被训练出批判社会的眼光,西方文化由苏格拉底、弗洛依德、尼采、马克思、罗素等人凸显出了一条深厚的、其他文化所缺乏的自我批判传统。而美国从本质上讲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欧洲传统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美国都占主导地位。
但是近几十年来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传统派的反攻(backlash)虽然获得了政界的支持和公共媒体的喝采,却也不能限制改革派出书。改革派的代表著作有代瑞尔·格勒斯主编的论集《开明教育政纲》(Darryl Gless,Ed.,The Politics of Liberal Educa-tion),吉拉德·吉拉夫的《超越文化战争》(Gerald Graff,Beyond theCulfure Wars),约翰·古乐瑞的《文化资本》(John Guillory,CulturalCapital)等。改革派的论点,值得注意的有:
●所有文化一律平等,不仅在道义上平等,在智性上也平等。认为某一特定文化全面优于其他文化,不过是欧洲中心的帝国主义陈辞滥调。所谓非功利性、普遍性、客观性常常是靠不住的,它们往往不能超越历史和地域的局限,现代哲学的主要理论一直在证明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评价一部作品品质的所谓客观标准并不存在。所谓普遍性只是一种幻觉,个人的自身认同只在他作为社会次级团体的成员时才显示出来。人之异于动物在于人身上的第二自然属性,个体的规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生俱来的种族、阶级、性别等背景。在教育中强求将少数族裔纳入主流文化,是在限制他们第二自然属性的发展,严格说来是反人道主义的行为。
●西方经典的作者清一色的是“死掉了的白种男人”(deadWhitema1es)。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教育环境中,经典作品应该体现文化、族裔、性别等多方面的代表性。即便是斯坦福经过修正以后的课程,仍旧留下太多“死掉了的白种男人”作家。就算是增加了几部非西方经典,添上了几位女性作家,如果课程仍由清一色的“活着的白种男人”来讲授,那么改革的意义就未能实现。所谓代表性,不仅应体现在经典作家的构成上,也体现在讲授经典的教师构成上。西方文明在历史上可说是压迫性的文明,对内它压迫妇女、农奴和其他下层阶级,对外压迫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西方经典全都出自白种男人之手的原因,在于白种男人是西方文明中的特权阶层。考虑到这些因素,也就可以说西方经典是压迫他人的产物。
●教育,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教育,从来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宣称传统西方经典超越了任何倾向性,无非是自欺欺人的神话。指责改革派以政治冲击学术,实质上是试图借此来掩饰传统派长期以来对学生进行政治灌输的事实。改革派是希望用民主多元的政治来取代传统派霸权主义的政治。
这场大讨论还在继续,有关的书还在一本接一本的出。争论的双方出发点完全不同,因此辩论也难以见出高下。不过在美国这样典型的工商资本主义社会,人文学科教授的声音通常无足轻重,“大讨论”将人文科学的影响引到校园以外,应该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讨论的中心,简单说来是“教什么?怎样教?”的问题。美国大学教育的真正危机还远远不是西方经典的消失,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经费短缺,是学生缺少训练和学习动力,是各类选修课目“象跳蚤市场一样杂乱无章”。……
传统的西方经典课程之所以成了一个问题,与大学生的成份有直接关系。近年来女生和少数族裔在大学里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有些自己特殊的文化需求,原有的西方文化课无法满足他们的这种需求。当然,诚如布洛姆所言,托玛斯·库恩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分析以及里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人文科学领域对库恩理论的运用,助长了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就目前而言,应当说保守派还有相当力量,但是整个说来,多元文化的要求已经向西方经典的绝对统治地位挑战,冲突无可避免。
写这篇文章的这两天,笔者专门去了一趟学校书店的教材部,在那里逗留了几分钟,发现柏拉图、荷马率领一队雄壮的队伍挺立在书架上,占据着一大片地方,非西方经典则被可怜巴巴地挤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看来西方经典从来没有消失,“经典消失”问题是一个假问题。
顺便说一句,在美国这场关于“经典”的论战中,我同情革新派;但是,若是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论战,我将偏向于传统派,因为就研习经典这方面来说,我们已经背离传统太久,“西化”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