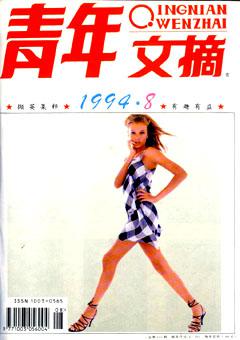蒙混过关
[德]霍尔格·勃兰特 沈锡良
在两次走私被逮住并课以重罚以后,吉拉想起“急中生智”这句谚语,不由地哼起了一首歌。
此后她总是耍新花招以蒙骗海关关员。但是,不管她多么巧妙地将瑞士表藏在身上,还是藏在行李的秘密抽屉里,一旦有人向她提出下面的问题,一种压抑感就开始萦绕在她的心头:“太太,你有什么需要申报的吗?”
她顿时察觉到自己的脸色起了变化。手掌湿了,身体也不知不觉地在颤抖。她极力想使自己显得无拘无束。即使海关关员相信她所谓清白无辜的谎言或者检查时未发现隐藏物,每次在检票口她都感到精神完全崩溃了。她清楚,不能长时间地从事这种生意,她的神经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难道从今往后就没有办法让物品万无一失地通过海关了吗?
她终于想出了打破僵局的主意。只要不是她自己提着走私品进出海关,她就不会害怕了。她需要一个替她保管走私品的人。
可她又的确不能向哪位旅客解释,请求代为保管这20块手表。这种事没有人会答应的。
不过,那位代劳者要是根本预料不到会出什么事的话,就可能不会拒绝这种无理的要求。
事实上,她只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两只箱子对换一下就可以了,把别人的行李带过海关,然后让那并非心甘情愿的帮手认识到这只是出于疏忽。
就算被查出,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对方落入海关关员之手,大不了手表被没收。这无论如何比高额的罚款或是她这样的惯犯可能去坐牢要强得多。
下定决心后,吉拉犹如获得了新生。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去进行她的第一次尝试。
苏黎世来的飞机到达了。吉拉一下飞机便最先站在行李传送带旁,伺机抓起一只与她的箱子很相像的箱子就想走,她急匆匆地想往海关赶。
可她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就在那一刹那,一个十分激动的声音阻止了她:
“对不起,我想您错拿了我的箱子。”
吉拉不耐烦地转过身,看到一个年轻男子正气喘吁吁地赶来。
“您的箱子吗?”她重复道。
“是啊,您看,”年轻男子竭力使她相信。“我的箱子比您的那只要小些,就像兄弟似的。”他为自己语言的诙谐笑了起来。
吉拉跟着笑了,但明显地有些局促。她的计划彻底破产了,而现在她不得不再一次为如何能稳稳当当地通过海关煞费苦心。
随后的一刻工夫颇令她窘迫,她发誓下一回要更小心地选择箱子。
她赶在自己的航班离开瑞士前行动了。她打量了一下其余的乘客以及他们的行李,决定对一只轻便的塑料箱下手,尽管自己携带的是一只皮箱。塑料箱子是容易买得到的,她在一家旅行用品商店里就看到过跟它一模一样的箱子。
她买好了箱子,一并带上原来的行李箱躲进厕所,迅速地重新装箱。很快她的箱子跟那位白发老人的箱子丝毫不差了,那老人此刻正在办理行李发送手续。
整个飞行途中,吉拉心境极佳。她甚至为她的即将到达而兴奋不已呢。
然而,她又失败了。白发老人虽然不知道吉拉在她自己箱子上划了刀痕作为标记,但对她错拿了箱子马上怒气冲冲。
“把我的箱子拿过来,年轻的太太!”他要求道。“我的书是不容许搞错的。”
不奇怪,这一次又泡汤了。那只陌生的箱子至少比她的重一倍。
一不做,二不休。几天后,吉拉开始了第三次尝试。
在苏黎世挑选箱子仿佛成了例行公事。她选中了一只做工考究、外覆黄铜箔片的暗红色优质皮箱。这种箱子她在一位胖女人身边看到过,那女人还匆匆忙忙地喝过一杯咖啡。
吃一堑,长一智。吉拉悄悄地走近那女人,趁她不注意时掂了掂箱子的份量。
不会重于12公斤,她估计。于是她去厕所将自己的部分行李装在她刚买来的皮箱里,重新回到了大厅。
她一直等到那位女人在行李柜前排上了号,趁机换下了箱子。箱子上已贴上了对她极有用的标签,简直是天赐良机。如此这般以后,她在法兰克福的日子就会轻松许多。
换箱子的事谁也没发觉。那位女人也没注意到。吉拉沾沾自喜。
飞行途中,吉拉还睡了一个小时。她已好久无法安眠了。她高度紧张的神经总算渐渐松弛了下来。
这种紧张的神经在她到达德国后又出现了:她原是从容地提着那只陌生的箱子,不料那位陌生女人拿着她的行李箱,正走过她的身边前往验关处。
海关人员迟疑了一会儿,就让那位陌生女人过去了。嗨,这可太棒了!
吉拉愉快地跟在她后面。
“请等一下!您有什么需要申报的吗?”
“没有。”吉拉正想继续走。
“那我们可否查看一下您的箱子?”
“当然可以。”吉拉用力将那只陌生的箱子放在桌上,然后把它打开。
最上面放着睡衣。
那位海关关员微微一笑:“您肯定这是您的箱子吗?”
“是我的呀,”娇小可爱的吉拉作出保证。“这件睡衣是我母亲的。这里面还有好多她的东西呢。”
那名官员满意地点点头。“我只是问问。因为突然有人说行李搞错了。”
“干吗就该是我呢?”
“或许正因为不是您。”
吉拉呆呆地注视着放在内衣下面的塑料袋,里面装有白色粉末。
前面那位胖女人宽心地向后瞧了瞧,急忙提着箱子离开了。
有只手搭在了吉拉的肩上。“您被捕了,”她听见一个粗暴的声音。“这么些毒品至少够您6年受的了。”
(晴日摘自《译林》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