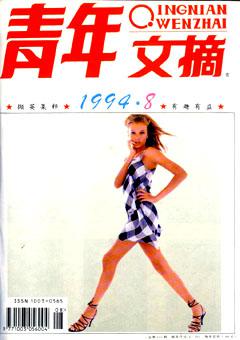岁月的回声
林 莺
我喜欢翻阅相集,如同欣赏家珍。读相片,如翻检往事的册典,总有一种舒缓优美的旋律从中浮起,总有一股醇酒般浓浓的醉意。
和好友枫的合影集,是我最珍重最精心收藏的一本。它记录着我们青春时代一串美妙轻盈的韵脚,记录着一段如秋日早晨晴明无际如长河之水逶迤清纯的友谊,记录着我们热烈的情怀和冷峻的思考。
蓝天帷幕之下,长风斜过,云彩鼓动活泼的风帆;一行大雁凌空飞翔,群山横卧,近翠远黛,我与枫揽肩挽臂……20年前,似诗似梦的年华,逍遥的岁月,就这样镌刻在薄薄的相纸上,镌刻在我心间。
我与枫是在县城文化馆认识的,她搞美术,我学文学。那天,我看到一个女孩拿着画笔魔幻般地召唤出美丽的山水花鸟,还有潇洒的人物形象,我十分惊异。女孩穿着玉绿色呢裙,系着翠绿围巾,高贵典雅的色调在她身上结成高雅的气韵。那就是枫。
不久之后,我们一起调至城西小学任教,朝夕相处,成了知交。
我们的友情是在蓝天绿野里生长的。
假日清晨,我们避开琐事俗礼,到外砂河畔踏青涉水,欣赏朝霞晨雾,陶醉天光云影。眼前一带流水,一片金色沙滩;身旁一旷绿野,一脉山林,令人安闲怡然。我们常常开怀畅谈,不疲不困,话题无边无际。在那寂寞、闷恹、墨守成规的年代,心情窘迫,这一切足以迷醉性灵。我们高声吟诵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朗诵王维的《山居秋暝》、《渭城曲》;讲《一千零一夜》中的人面狮身,讲埃及的金字塔之谜,谈曹雪芹、托尔斯泰……那份精神享受,可谓生活中的最高境界。
枫不仅美丽,而且聪明。与这样的朋友相处,似可泯除自己天性中的一份愚昧,沐一次智慧的灵泉。我真愿能锁住每一次兴会和旅行。
有一天傍晚,枫急急敲开我的家门:“今晚那朵县花就开了。”昙花,对孤陋寡闻的我来说,还是第一次见识,在我想象之中,那是一种美丽得近乎神奇的花木,她浓缩生命而创造极端的辉煌,牺牲生存时间而换取生存质量。它在我的想象中,似烟似雾,如歌如幻。据说花开时能看到花瓣在动,如同美丽的花仙子翩翩而来。我欣喜若狂地同枫来到她家的院子里。我们把昙花搬到灯光透射的窗下,依肩并坐,凝视静观。夜渐深,如冰雪白玉雕成的花苞缓缓舒展,一股清香袅袅飘起,娇柔纯真,如出水芙蓉。如此的奇观,如此的圣洁,使人们都沉醉在梦幻之中,唯恐一点声响惊扰了眼前这柔弱的花魂。至今,每赏花观月,我都会想起这个难忘的夜晚。
我与枫谈得最多的是个人的心事,个人的理想和追求。那些年,社会上的风风雨雨常把人心抽打得成畸形,没有事业的空虚,家庭出身的委屈,数次招考成绩名列前茅而最终落第的愤懑,使我的心常存辛酸、疲惫和疼痛。每当我心思太累,面对明天的噩梦升腾起无望的情绪时,枫就会陪我到河边散步。她那精辟的带哲理的语言,会使我把种种遭际化为淡泊,心的视野逐渐宽广。
在那前途渺茫的日子里,我们仍心存奋斗。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情感,被昏暗的烛光引诱入魔。我坚持文学创作,枫坚持绘画。我们想成为文艺芳园中的一朵小花或一棵小草,不望辉煌,只求存在。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我与枫又唤起澎湃的热忱。我们挑灯夜战,互相勉励。也许是深深的缘分,我们一同踏进大学校园,住在广寒宫的同一楼层。
枫现在成了大学讲师,成了满腹经伦的女学者,正处于事业的巅峰。她有了幸福的家庭,我们仍如姐妹般心心相通。
捧着影集,我重温到那久违的熟悉和亲切。照片所飞越过的时间和空间,均已不再,但这段珍贵的友情,丰富了我的青春,永远在我心中留下无限的回音。
每当节日,接到枫的贺卡,我便会想起这一段鲜活的日子。岁月的风,永远不会把记忆吹淡。
(蒋惕吾摘自1994年3月18日《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