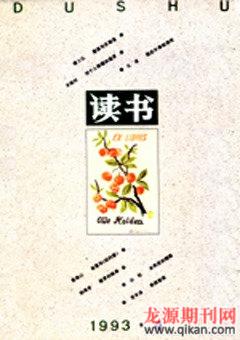魏安德的中国工厂研究
葛佳渊 罗厚立
西潮东渐以来,尊西崇洋逐渐蔚为风气。到本世纪初已形成“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邓实语)的现象。在此风气熏染之下,欧美洋理论一直对国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各种文章著作竞相套用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而很少加以甄别。若仔细观察,导论之类的西方初级教材似乎比真正的理论专书更有影响。不仅如此,甚至有的标榜是乾嘉之路,以考据为宗旨的上古文史研究,其注释中大量引以为据的也多是各种新老西方教材的译本。这些译本有的恰好将原意译错,可能正好可以符合作者“考据”的需要。更偶有真搞考据的老学者,童心未泯,将这种“考据”誉为“为学术立一新方向”。
有趣的是,西人对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的具体研究却未受到同样的青睐。当然,西方人研究洋东西大概更得心应手,而研究中国则不免出些文字史实的错误,似乎不那么让人佩服。但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同行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说,在今日各个题目的研究都有一定数量的论著之时,不看别人的研究而自己闭门造车,常常会事倍功半。近年来有识之士已在陆续刊行海外中国研究,但数量十分有限,其中社会学著作尤为少见。
加州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魏安德(An-drew G.Walder)的中国工厂研究,曾连续获全美社会学会的“杰出贡献奖”和全美亚洲学会的“李文森奖”,颇轰动一时。但它似乎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魏氏对中国工厂的研究属于西方“工业关系”(industrialrela-tions)这门学科。其主要关心的是劳资双方的关系问题。而社会学者在研究劳资互动中,更注意权力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谁相对谁来说更有权力以及这些权力是如何取得和如何行使的问题。而魏氏的研究又与过去的“群体论”(group theory)和“独裁论”(totalitarianism)不同,所关注的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人们日常生活和行为的影响。具体地说,魏氏首先关注的,是在计划体制下的中国工厂究竟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社会政治组织的问题。
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厂的生存与否完全取决于其效益如何。劳动力作为马克思所说的可变资本,其成本的最小化是工厂管理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不仅是一个可以与工厂分离的生产要素,其雇佣也依工厂对生产的需求的涨落而起伏。工厂作为一个经济组织,雇佣关系首先是一个市场关系。因此,劳动力的价格——工资——和雇佣条件多为劳资双方正式讨价还价的结果。
然而魏安德所见的计划体制下的中国,工厂的存亡继绝与其效益好坏甚少关联,而更多地取决其在计划体系中的地位。劳动力作为“不变资本”,其价格全由计划决定。劳动力与企业既不被视为可分的实体,劳动力的成本也与工厂效益无关。因此,计划体制下的工厂可以不必考虑如何有效地运用劳力。相反,为了避免将来可能缺员的危险,中国工厂的管理者趋向于大量积存多余的劳力,就象他们积存其它固定生产要素(如原材料、零部件)一样。这两种经济体制在经济逻辑上的根本歧异,对于各自的劳资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
魏安德以为,中国工厂不但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且更是一个社会组织。在计划体制下,雇佣或就业本身就带有社会福利的色彩。同时工厂还要提供许多市场体制下只由市场、社会福利机构、或政府部门才提供的物资与服务:如住房、幼儿园、食堂、医务所等。由于“国营”、“集体”、“个体”的区分本身就带有与其名分相符的福利与工资条件。中国工厂实际上成为社会分层(socialstratification)的重要工具。就业单位之好坏可以与工资级别同样重要。“正式工”、“合同工”或“临时工”的名分不同也限定了相应的升迁轨迹。
计划体制下的工厂还发挥着诸多市场体制下老板无需关顾的政治功能。工厂与其他“单位”一样,起着政府和基层组织的功能。单位大则可以对外代表其职工,干预公安司法。小则各种身份证明,包括旅行证明的签发,都离不开单位。
这些组织特质塑造了一整套与市场关系迥然不同的权力关系。对工人们在经济、政治、以及个人生活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厂正是中国工人的政治与社会名分所系之处。其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工人对单位的经济依附,对组织的政治依附,和对车间工段领导的人身依附。这种依附关系成为魏氏的权力理论的中心概念,也是他借以推演整个理论的基石。
魏安德以为:经济依附程度之高低可由两个指标来衡量。第一、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须由其就业单位来提供;第二、这些基本需要有多少可从单位以外的渠道(如市场)获得满足。依附程度的高低与前者成正比,而与后者成反比。也就是说,愈多的物资或服务必须由就业单位提供,即意味着这些物资与服务愈难在单位以外求得,工人对单位的依附程度就愈高。在中国,工人不仅依赖单位分配住房,提供医疗、保育、食堂,而且还常常通过单位获得便宜或紧俏的物资。在某种程度上说工厂起着家庭的功能,所以我们常有“爱厂如家”或“以厂为家”的说法。但工厂毕竟不是家,厂领导也不是家长,故从魏氏的角度看,工人与组织的关系即是一种经济依附关系。
工厂组织浓厚的政治色彩,构筑了一套相当稳定的赏罚陟黜的渠道,将工人的荣辱沉浮牢固地置于一定的掌握之中。工人的升降进退较少基于其工作的好坏。在动员工人投身建设的同时,工厂将那些原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员的行为与思想准则,延用到普通工人身上。
由于许多非经济的特权操于车间或工段领导之手,魏氏认为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形成一种人身的依附关系。基层领导之好恶取舍,常常影响到工人的个人生活。中国工厂中的车间工段领导,与其西方同级人员相比,操有更多的权力,更象西方早期的“合同工头”(contract foreman)。由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操有权柄,使其“中介”作用大大提高。工人与他们的亲疏远近,往往决定他们对工人升等、提拔、转正定级的考核和推荐。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人既没有正常管道宣泄,也没有辞职另就的途径,在丧失赫胥(Hirsch)所说的宣泄(voice)和另就(exit)两种表达不满的方式时,对这些基层干部的依附也就较其他国家更深一层了。
这种在经济、政治以及人身方面对单位的依附,派生出许多中国工厂在制度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方面与众不同的特征。其中魏氏着墨较多者是他所说的“恩属”关系(patron-clientelism)。有的领导可以通过对一些人在升迁利禄上的优惠,建立起一套稳定的“恩主”(patron)与“属客”的关系。所谓“突击提干”、“以工代干”等擢升方式,均可从这一角度考察。这种组织对“骨干”、“先进”或“落后”的亲疏远近并不是任人“唯亲”或“唯贤”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可以概括的,魏氏将其称为“有原则的特殊恩宠”(principled particularism)。这种权力关系多以属客对恩主的效忠为纽带,从而换取恩主对属客“有原则的特殊对待”。其所以有原则,是因为它并不等于私人关系;其所以特殊,是因为奖惩陟黜不基于工作绩效而基于对组织的效忠。魏氏强调说,这种既带有私相授受情感成分又含有层级组织成分的恩属制,有规律地施惠于某一部分人,以至于塑造了一套纵向的效忠网络,从而也导致了工人中的疏离和分野。
在讨论“有原则的特殊恩宠”时,魏安德对“表现”一词极为关注。他指出:由于该词在语意上的含混,使得基层领导得以随意评估工人,同时也使工作考核失去客观的依据。虽然“有原则的特殊恩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激励工人的服从与纪律,但其结果有时也会适得其反。魏安德根据对一百多位职工的访问资料,总结出三类可能的对应方式:即“算计式取径”(calculative orienta-tion);“积极竞争式取径”(active-competitive orientation);和“消极抵御式取径”(passive-defensive orientation)。虽然有不少工人脚踏实地以图进取,但亦有人委身求荣,阿附逢迎。
过去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工厂多强调“意识形态”和“群众运动”等方面,魏安德则更强调结构性的一面。他指出:在革命成功到组织建设的过渡期间,空洞的口号和动员群众的艺术变得愈来愈不重要。工厂是要出产品的。复杂的工厂管理也不可能靠“突击队”或“大干多少天”来长久地维持。纪律、服从和效忠渐渐显得举足轻重,而“有原则的特殊恩宠”便逐渐取“群众运动”而代之并成为权力结构的有机成分。
与其他许多研究不同,魏氏的研究从比较社会学入手,以跨国比较见长。他在讨论中国工厂时不断插入苏联、日本和美国的工厂的实例加以比较。魏氏以苏联(欧洲文化、计划体制)与中国的相似性来加强其结构层面的解释能力;同时又以日本(儒家文化、市场体制)与中国的相异来否定文化层面的解释。他将中国的基层领导与西方早期的“合同工头”(Contract foreman)进行的比较体现了他对西方工业史的深刻把握。
虽然魏安德强调计划体制国家权力关系在总体结构上的相似,但他并没有忽视它们在具体现象上的差别。由于中国特有的人口压力,中国工厂权力关系呈现出一套特有的布局:在中国,工作的转换较苏联东欧困难得多;而且,中国的国营、集体的身份差别也远较这些国家明显。由于八十年代以前的物资供给缺乏,中国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消费品与票证的分发配给制度。马丁·怀特(Martin Whyte)研究的中国工厂将有的“班组”学习讨论制度,作为车间组织的延伸,充当了工人对组织依附的中介。魏氏认为,所有这些都强化了中国的权力依附程度。
魏书最有创新之处,乃是强调对中国社会进行结构的而非文化的诠释。这一取向在魏安德还是学生时既已开始强调。他在密西根大学读书时已发表文章详细论述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中,工人阶级本身及其依附性是工业化高潮或“工业化驱动”(industri-alization drive)的产物。在本书中,魏氏进一步发挥这个关于革命成功后迅速工业化的有关工业政策和人事制度造成前述中国工人特征的论题。魏氏特别用对一九四九年以前天津上海等工厂的研究来证明许多现象正是实行计划体制才产生的。简言之,魏安德强调社会结构的作用,而认为文化和传统的作用至少在中国工厂研究方面影响不大。
但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议。一些学者认为魏氏强调结构和制度的作用太过。文化和传统的影响不容忽视。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上海天津是通商口岸,受西方影响较大,所以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工厂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对结构制度的过分强调使魏氏忽略了工人的能动作用,也忽视了“利益团体”(interest group)之间的互动关系。前述魏氏所指的工人对制度的几种回应方式如隐蔽的抵制和主动的进取,并非完全为结构制度所控制。如是则魏氏所讨论的工厂权力关系至少未能涵盖全部。
实际上,中国工厂企业的许多超经济职能在其他的商业或“事业”单位也屡见不鲜,农村也有过“以社为家”、“爱社如家”的口号。这些实际上也适用于结构性的分析,但却不宜说成是“快速工业化”的产物。同样,日本的工厂制度和中国极不相同,但在视厂如“家”这一点上,至少在心态上很为接近,而疏离于同样是市场经济的西方。中国儒家理想型的大家庭早在西潮入侵之前就已破败,周作人早就指出会党的兴起实即家庭制度崩坏的结果,盖会党在许多方面即起着一个大“家”的社会功用。但在制度破败的同时,理想却还在,还没有变。中日均有以厂(或公司、或单位)为家的提法,正是这一理想的余荫。这样看来,从结构的角度去考察,仍能得出文化影响的结论,两者未必非相互抵触不可。
反过来,过去我们说到依附,马上联想到“封建”,更容易附会中国历史上的食客、部曲或家臣之类的“封建人身依附”。实际上中国自己的“封建”更多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和社会的,本无多少依附。倒是西方的封建,包括马克思所说的封建,才最强调依附。盖以服役(特别是兵役)而换取土地和庇护正是西方封建制的基本要素。魏安德所讨论的“恩属制”确实看不出多少中国传统的影响和文化的积淀,反倒更象西方的封建制度。
说到底,我们今日所说的市场经济也好,计划经济也好,都不是我们自己的祖传,而是从那更广义的“西方”泊来的。因此,一九四九年以前上海天津等口岸工厂与一九四九年以后计划体制下的工厂的不同,其实也可说是这一部分“西方”与那一部分“西方”的不同。熊彼得和章太炎都说过,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不过是中古封建时期尚武好战精神的延续。“封建”对西方的“文化积淀”作用看来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魏安德的研究确实证明计划体制下的中国工厂的制度和结构没有多少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积淀。但对西方的“文化积淀”的理解,却不无启发。
魏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仅是对香港百多位大陆移民的采访纪录。这样的“小口子进,大口子出”,终使人对其材料的代表性和全书的涵盖面不免有些疑问。更重要的是,近些年中国经济改革步伐甚快,魏书出版时,中国大陆的工厂体制已非其研究时的面目。最近的进一步市场化,更大大改变了工厂的结构。对此魏安德是很清楚的。据说他在最近的演讲中强调他的研究已经“过时”。希望不久即能看到魏氏的新作品。
Andrew G.Walder CommunistNew-traditionalism Work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1986 Berke1ey,CA:Uni-Versity of Califocni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