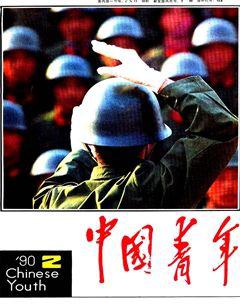生命的邀约
常少宏
听说王华祥在第7届全国美展获得金奖,我连忙跑去向他祝贺。站在美术馆展厅他的两幅获奖作品面前,我问他有什么感想,他好像一点也不懂得谦虚似的回答我:“嗯,我觉得确实画得不错。”
这,就是王华祥吗?
1988年的深秋,我初次踏入王华祥的画室,那时只是感到粘在墙上的那些涂满五颜六色犹如万国旗般的工艺布,特别刺眼,好像在强烈地显示着主人的一种性格。这种性格是什么?一年后的今天我也说不清,好在同时来的还有几个女伴,她们叽叽喳喳地跑来吃“涮猪肉”,又叽叽喳喳地缠着王华祥讲点儿他自己和他家乡——贵州的事。
王华祥就讲开了。
放牛娃
那是黔西北一个只有20几户人家的小村落,村的周围层峦叠嶂地盘踞着座座大山,山脚下一条湍急的大河飞流而过。有一天,一个外乡汉子在这里娶了一个彝族女人,生下了几男几女之后,又去外乡谋生计了。这几男几女之中,有一个就是王华样。
云贵高原是神秘的也是闭塞的,如果不从贫穷这一角度去观察她,你会发现那里极有世外桃源的味道。王华样在几个兄妹中,身体最弱小,可他却牵放了一条壮实如山的大牛。清晨放牧,黄昏牧归,童子老牛十分写意。他记得有一次,老牛来了兴致,不管他如何挥舞着竹条,吆东喝西,老牛硬是向庄稼地冲去。母亲跑了过来,在他屁股上狠狠抽打着。他没有哭,只是满心怒气地拉着牛走到很远很远的山里,把牛牢牢拴在树上,然后用竹条狠狠地抽打牛背,那时他才5岁,任他如何抽打,老牛若无其事地甩着尾巴,而他却为老牛挨打掉下了眼泪。
集日,王华祥总要穿过陡峭的大山来到小镇,花一毛钱买下两个泡粑,边吃边向一条街的拐角处走去。那里有位专营春联、挽联、年画的小店,老店主腕子动几动,白纸上就会现出花鸟虫鱼来,在王华样幼小心灵里,这老店主实在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还有屠夫,他特别喜欢看杀猪的场面。在他眼里,屠夫是一种特殊的人,他们腰板笔直,提着一口明晃晃的尖刀,若无其事地向那捆翻了的、像泼妇一样尖叫的肥猪刺去,血热乎乎地淌下来……他直视这血淋淋的场面,毫无畏意。
当第一天拿到纸和笔时,王华祥本能地描绘起他童年中那些熟悉的印迹:老牛、屠夫、大山大河……记不清有几位老师没收了他多少张“画”,他的文化课一塌糊涂。到了初中,他弄不清今后究竟想干些什么。可这时,艺术之神却在轻轻叩响王华祥的命运之门了。
在镇上读初中时,王华祥住在一位开照相馆的亲戚家,从亲戚那儿他学会了打格子画人像,于是画了许多漂亮得现实中永远也找不到的女孩儿头像。后来学校里搞学雷锋活动,王华样画了张雷锋像,引起一位从中央美院下放来的美术教师的注意。不久镇上传出消息,说省城里有个专科学校招画画的学生,于是王华祥遵着照相馆亲戚的教导,提着一兜子柑桔去登门拜访了那位美院教师,恳请他收自己为徒,好学两手去考“美专”。
两个星期之后,王华祥坐在了“美专”招生的考场上,考试内容是画石膏像。看着周围伙伴们一丝丝地勾着头发,他觉得他们画得真像、真棒。而只学了十来天素描技法的他自愧不如,只好按老师讲过的眯起眼睛,寻找投射在石膏像上明暗朦胧的光线,并尽力把这种光线描绘出来……
在几百个竞争者中,王华祥作为26个幸运儿之中的最后一名被贵州省艺术学校录取了。当时他还不懂绘画的分类,素描、国画、油画、雕塑等等在他头脑中均是一片空白。天知道他为什么单单选择了以黑白线条占主导的“版画”,而且一经沾上,便一发不可收了。也许这是“生命的邀约”。
“四脚蛇”
1984年,在贵州美专毕业后又去一所中学教了3年书的王华祥踏进了权威的中央美术学院。那时的他,周身洋溢着“艺术家气质”,穿最新潮的服装,写最潮流的诗句,谈论最时髦的画派,并想方设法喝酒吃肉,自己请自己。入学才半年,他就同三个哥们儿在学校里合搞了一个“四脚蛇”画展。他们用表现主义的手法尽情宣泄了青春期的热情、智慧与躁动。画展在一个小教室举办,共展出作品40余幅。画展期间,许多人到展室转了一圈,又走了,满脸的不置可否。只有一位当时还在读研究生,如今在中国画坛评论界小有名气的学生抛下了一句话:“这帮人将来会出头。”
一年后,被称之为“85新潮”的中国现代派画展才姗姗出台,可这时候,王华样已开始对那些自诩为“先锋”、“激浪”不可一世的某些现代派画家的浅薄深恶痛绝了。难道一个簸箕只因被挂在了美术馆的墙壁上便也成了艺术品而不再是簸箕了吗?艺术描述的应该是人、是生活。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绝不会沉醉于一时的哗众取宠。王华祥曾狂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转而研究被人轻视的古典和民间的艺术。
大师梦
大概是从1987年起,王华祥做起了“大师梦”。
“我感到艺术必须回到正轨上来,20世纪的混乱将随着世纪的结束而结束,21世纪一定有它自身的艺术,我们将跨入那个时代。我们的任务不是为了给20世纪唱挽歌,而是给21世纪开路。塞尚、毕加索、康涅斯基是20世纪的开路先锋,21世纪的荣光将落在谁的头上呢?我!我一样的人们!”
在王华祥看来,两个世纪的交替之际,必将有一批大师诞生,生活于此间的人们,应该有一种使命感。
“在现存的版画形式中,我找不到我所期待的东西。翻开版画史,我看到了许多精美的黑白版画,再翻,还是精美的黑白版面。版画没有颜色吗?我并不喜欢这样的版画。最起码我为这样的版画感到不足,我试图去琢磨雕刻、油画甚至照片,它们之中有版画可资利用的东西。像布鲁德尔的浮雕、弗兰契斯卡的壁画、古图索的油画……在我看来,简直就是版画。这时候,我感到一种新的,与以往任何版画完全不同的东西就要诞生了。”
王华祥疯魔般地为自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历史使命。毕业实习,王华祥选择了贵州省最穷的威宁县作为自己履行这一使命的起点,一头扎进去,用整个身心再次体会哺育了他的那些高山大川,古朴民风。
威宁县,你能想像20世纪80年代在那里还流行着结绳记事,戴着狰狞的面具驱鬼逐魔的事情吗?那里几乎与世隔绝,人们自成一统地过着接近原始的自然生活。王华样早已脱去了那曾经有着“艺术家风度”的新潮时装,头发也剪成半寸长,在丛林里,在山寨中,在宁静祥和的集市上,他徘徊着、蜘蹰着,一支支苍凉悠长的山歌,一幅幅质朴古老的画面,不断地在他脑海里闪现,潜伏在童年中的记忆复苏了。山坳、河滩、杀猪、赶集……他的刻刀下,流淌出一幅幅内容氛围全新的画面:面目有些呆滞的山妞、面部褶皱犹如丘壑纵横般的老汉、神情庄重肃穆的屠夫……一种充满原始的生命的激情和冥冥宗教的神秘感,跃然而出。
许多年来,一直渴望成功的王华祥,终于迎来了这一天。1989年参加第7届全国美展入选的几百幅代表当今中国画坛创作最高水平的美术作品,经过专家们审慎而苛求的评选,他的“贵州人”系列中两幅版画,获得金奖。
接下来,中国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决定收藏他的作品,河北出版社决定出版他的版画集,《美术》、《美术世界》、《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等报刊纷纷刊登了他的作品,他也被众多的评论家誉为“最有希望的青年版画家”。
最近,王华祥的画室里挂起了一张自画像,看上去一脸苦相,神情有些呆滞地注视着充斥画室墙壁四周的“杀猪屠夫”系列草图——那是一些敦厚古拙的贵州乡民,他们面目的表情和那一头头倒挂着的开了膛的死猪表情一样,木讷而神秘。王华祥琢磨这些乡民和屠猪的场面已许多年了,他觉得这一块活生生的土地,够他开垦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