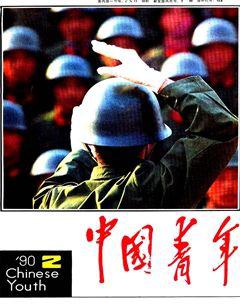走向明天的太阳
曾镇南
回头翻阅1989年发表的描写当代生活的小说,我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那些多少引起读者和评论界注意的比较优秀的作品中,纯粹描写青年题材的并不多;但是,不少题材超轶出青年生活范围的中短篇小说中的青年形象却很有特色,很值得研究。这种文学现象说明: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一度占有突出地位的青年题材的作品——例如至今仍吸引着不少评论家对它作专题研究的“知青小说”——正在日渐消融到更广泛更多面的描写当代生活的作品中去。这种文学题材日益综合化的倾向表明:一方面在现实生活的复杂进程中,青年问题在更巨大、更广阔的社会问题面前,似乎正在失去它的特殊性和单列性,而被卷入统一的、翻涌的生活的旋流之中;另一方面,作家们在观察当代青年的生活方式、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的时候,已经不再单纯地充当青年的代言人的角色,而更多地以“社会书记官”(巴尔扎克语)的身分出现了。
不过,青年毕竟是社会中最活跃、最锐敏、最有生气的力量,归根结底,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敏感多情的作家,在他们广泛地描写当代社会现象,探寻当代生活流向的时候,不可能不注意到处于剧烈的社会变动中的当代青年。所以,在他们那些题旨开阔深邃的小说中,青年形象仍像强烈的光斑一样,闪动在小说展开的生活画面上,牵动人们的激情和思索。
近几年来,一提起当代青年的文学形象,人们立即会想起王朔笔下的“顽主”们和刘毅然笔下的“摇滚青年”。这些放浪形骸,玩世不恭,出入于宾馆舞场之内,歌哭于灯红酒绿之中的都市青年,以他们脱略不羁的思路、大胆刺激的语言、强悍迅疾的行动,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它们像脱离了常轨的自由电子,以自己畅酣恣肆的生存状态,既显示了冲决社会固有规范的活泼泼的生力,也表现出了亵渎美好理想、善良道德的令人怀疑的邪气。在描写这类令人眩目的、极富特定社会时局特色的青年形象时,王朔得益于他那自然、泼辣、强悍的笔墨,刘毅然在铺张扬厉的作风中也取得了声色夺人的艺术效果。两人在才情和个性上虽有不同,但在强调和强化他们所倾心的这类青年形象和这种青年情绪时,却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了某种创作心态上的做作。这类青年形象可以歪打正着地引起人们对某些社会痼疾、隐患的思索,可以宣泄人们的某些积郁和愤懑,颇能耸动一时的视听,但它们却很难持久地吸引读者的兴趣。事实上,所谓“王朔热”在影视界和评论界,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到了去年,王朔虽然勉力推出两部长篇(《一点正经没有》和《千万别把我当人》),但读者的情绪却相对地冷却了。其原因,我想除了严峻的生活掀起的狂涛巨浪不容读者再葆有欣赏“顽主”的心境之外,王朔笔下的这些青年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广泛的基础,它们之于大多数读者的日常生活委实过于遥远了这一点,恐怕是更根本的原因吧?
就在喧哗骚动、光怪陆离的“顽主”们、“摇滚青年”们的侧畔,悄悄地出现了别一种当代青年的形象,这就是冯敬兰的《夏日辉煌》、周克芹的的《秋之惑》、张中海的《青春墓志铭》、许辉的《焚烧的春天》等作品中的一大群沉重而切实的劳动青年的形象。
这是一些还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充分注意却以自己沉实有力的脚步日益走进广大读者心灵深处的青年形象。
来自华北油田的女作家冯敬兰在中篇《夏日辉煌》中,描绘了一群“文革”后期女子钻井队中的青年女工形象。这样富有生活气息的鲜明、饱满的青年女工形象,而且是负荷着沉重的工业劳动的女工形象,在我们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是很罕见的。作者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回顾、凭吊了她的这些可亲可爱而又可悲可悯的青年伙伴们的一段艰辛、悲壮的生活。当她回首女子钻井队的光荣业绩的时候,一方面,对女性身心特殊需要的体谅和理解,使她对那些在特殊的年代里为着一种人为的荣誉而负担起力不能胜的繁重劳动,牺牲了健康、清洁和娱乐,压抑了爱情,磨损了青春的采油女工们的命运充满了悲悯,婉曲尽相地写出了她们身外和心内的种种矛盾和惶惑,从中映照出那个畸形的年代的某些面影。另一方面,对劳动的荣誉感、奉献的自豪感、青春的火炽热情等等的眷恋和赞美,又使她在这一幕畸形的劳动悲剧中,发掘出了属于未来,属于庄严的正剧的东西。在荒谬的形式中救出合理的内容,这就是作者在阴郁的夏日中发现了人的辉煌所循的哲学和美学的思路。这一思路使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马丽的形象获得了某种思辨的深度。在这个严于自律,充满献身精神的女子钻井队指导员身上,人们与其说看到了那个年代的流行观念对一个活泼美丽的女性的禁锢和扭曲,不如说看到了特殊环境下中国女性惊人的毅力和感人的献身精神。已经消逝的夏日之所以显得那样辉煌,就是因为在这些劳动着的青年女性的精神世界中,闪耀着一种崇高的理想的光芒。不论是非常富有女性味儿、娇嗲可爱、渴望爱情的李艳儿,还是颇有棱角、聪明伶俐、好学上进的范宁,或者是纯朴善良、情深心细的老彩,她们虽然和马丽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对自己身受的劳动压力和心受的荣誉压力有不同程度的怨怼,但是,当她们结成一个劳动集体,又面临着大自然的肆虐造成的灾难时,却无一例外地以沉着勇毅的献身者的姿影出现了。虽然罩着浓重的历史阴影,但中国女性的伟大,在这些钻井队女工的形象中,仍然不可掩饰地闪射出来。
在对“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进行反思式的映照时,《夏日辉煌》是别具只眼的。这是女性的呼吁书,又是劳动和奉献的礼赞曲。互相矛盾的双重主题,在真切、细致的劳动生活和女性心理的描写中,浑和地交融在一起。作者完全忠实于当时当地生活的真实,按迹循踪,擘肌入理,写得令人信服。缺点是行文有些滞重,布局过于平实,总体缺乏一种韵味。——这对于一个创作道路比较单纯的作者来说,也是不难理解的。
周克芹的《秋之惑》,把我们的视野,从过去拉回到现在,拉到川南农村的果园里。周克芹是非常善于以细腻而悠远的笔触敏感地勾勒当代农村青年的心理微澜的作家,他的小说以富于诗意和情韵著称。《秋之惑》也葆有并发扬了作家一贯的艺术风格。
在这部小说中,周克芹从农村现实生活中新的矛盾的揭示,进入到对农村青年心理上的惶惑的剖析。尤家山江家的果园进入了丰收的秋天,但经营果园的人们的命运却有了悲秋之叹。江家果园的真正主人二丫,是一个具有《红楼梦》中的探春那样要强的心气和理家才干的农村青年女性。她在经过三年辛苦经营的果园被哄抢摧残之后,陷入了情感失落的惶惑之中,并在这惶惑之中苦苦挣扎。而她深深爱恋着的华良玉,则面临并身受着他那进城自办公司的妻子尤金菊所代表的新的人生价值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的猛烈冲击,也陷入了痛苦和惶惑之中。二丫的惶惑是不敢直面自己感情需要,想挣脱封建守旧的网罗却感到孤单乏力的惶惑;而良玉的惶惑却是敢于直面自己的感情需要,固守自己的生活理想,顽强地对抗凶猛而粗鄙的“生活新潮”时产生的惶惑。这两种惶惑,一见之于感情,一见之于事业,虽然是发生在两个默默无闻的农村青年心里,但其心理内容所折射的时代性却是非常鲜明的。归根结底,这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受到压抑和冲击之后产生的惶惑,是人借以安身立命的情感之泉和理想之光遭到壅塞和遮蔽时产生的惶惑。周克芹力透纸背、细致深沉地写出了这种“秋之惑”,实际上就是从底层生活出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出了当代生活中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即追求完美元敲侧的人生和追求切实不虚飘的理想的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华良玉那种带着泥土味的执拗的理想——用劳动开辟自己的果园,带着女儿呼吸嬉戏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永不离开农村——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他坚决拒绝了妻子提供的到城里去工作的机会,不惜与妻子分道扬镳。这里固然有二丫感情上的吸引,但更内在的原因,是良玉有一种不可移易的人生信念和主见。他从自己的实际条件出发,从自己的个性、气质、专长、兴趣出发,确定了自己朴实的生活理想,站定了自己的脚跟,便具有不被俗流惑乱的力量!他是一个有根基、有气节的中国人,不是那种随风乱转的蓬草,也不是那种善于攀附的葛藤。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着作家对有恒志、有操守的人格的礼赞。
许辉的《焚烧的春天》,以一种质朴到近乎稚拙的语言,叙说了偏远的大草甸子上发生的一幕人生的悲喜剧。和自己深爱的丈夫国柱一起在大草甸子上盖起房屋、安下新家的农村少妇小瓦,最后却毅然烧毁了自己的家,跟上丈夫到城里去谋生了。从表面上看,这个农村青年命运跌宕变化的故事的意蕴,似乎是在显示城市生活对农村青年的吸引,显示农村生活的封闭性正在被时代的冲击波撞破,这诚然是对的。但这个故事的深处,还有更加丰富和激荡的人性内容。小瓦的果决行动,是她对自己的爱情的本能的护卫。她是深爱国柱的,但她发现国柱的长久远离,会使她陷入孤苦软弱、无力拒绝另一个淳朴男人的尴尬境地,也会使她的国柱无力抵抗生活的浊流的侵蚀,这就使她下了焚烧新屋的决心。在小瓦点燃的荒火中,我们窥见了这个农村少妇驾驭自己的命运的魄力——这是从百依百顺的柔弱中突然生长出来的魄力,实在是令人赞叹的!
张中海的《青春墓志铭》,是包括《憩》、《青春不悔》、《秋日辉煌》、《田园的忧郁》等四个分别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一组短篇,几乎可以当作一个艺术的整体来看。和《焚烧的春天》不同,这组小说描绘的是农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在诀别过去、憧憬未来时灵魂撕裂的痛苦。这里也有一种焚烧,那是集地之子与世纪儿于一身的主人公灵魂的自我焚烧。这种焚烧当然不会像小瓦点燃的荒火那样猛烈和爽快,而是一种烤炙心灵的、缓慢、缠绕的阴燃。在这种阴燃中,浸淫着事业的失落、爱情的差错造成的人生失败感。在这种失败感的抒写里,对人生的沉重而丰富的认识一层层展开了。这既是青春的墓志铭,也是生命的里程碑。这地之子与世纪儿的纤细、回旋的倾诉,使我们感到了对人生的那一份严肃,对爱情的那一份珍重,这难道不是当代青年多少有些失落的东西吗?
程乃珊的《祝你生日快乐》与田中禾的《明天的太阳》,是今年中篇小说创作中难得的佳构。这两部中篇都不是着重描写青年生活的,而是从“非常有特色”的时局促成人们社会地位、命运遭逢、心理状态的变化入手,提出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调整问题:正在失落的看似陈旧的东西中未必不曾含着可以通向未来的永恒的因素,而骤然崛起的咄咄逼人的势力也未必像循规蹈矩的人们想像的那样充满邪恶。代与代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正在发生着意味深长的碰撞和融汇,新的相互关系伴随着别扭和痛苦,顽强地在“有特色的时局”的安排下违拗着人们的主观意志产生了。这是对当代生活的旋转和运动的一种洞察底蕴的整体把握。在这种对现实的整体的艺术掌握之中,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青年一代的精神素质问题。
《祝你生日快乐》中的珍珍,已经是45岁的中年人了。在中国,这个年龄也可以勉强归在老青年一类里。实际上,珍珍的心理年龄是比较年轻的。她感到,自己这一代人所熟悉的世界正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价值标准都已改变的世界。她因自己猝不及防而失去了精神平衡,因此未雨绸缪地为女儿嘉茵筹划着、思量着,好让她尽快准备,以适应这个新世界。耐人寻味的是,珍珍面对过得热闹而又快活、活得泼辣而有锋芒的女儿,担忧的并不是她的生存能力问题,而是她的精神素质问题。珍珍自己,是富有艺术气质,常常被艺术中美好的东西感动的。她注意到:快乐的嘉茵,似乎不大有“感动”的时候。“快乐的情绪,是很容易忘怀的。只有‘感动,才会令人铭刻永志。”她希望女儿的精神世界里能有一点深沉的东西。尽管她自己在生活中的优势正在一步步失去,但她还是那样令人感动地关心着精神性的东西。这正是和我们共和国的50年代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的那一代青年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作家对这一代青年、对珍珍,是满怀着同情和祝福的。她不讳言珍珍们面对价值观念急骤变化感到的惶惑,但她认真地护卫着珍珍们精神生活中的那些美好的东西,这些美好的东西未必是嘉茵们的世界所不需要的。
《明天的太阳》描写的是老艺人赵鹞子和他的儿女们在时代浪潮冲击下发生的命运变化。如果说珍珍在生活的变动中对自己优势的失去只是感到一种悲剧的意味的话,那么,赵鹞子则不可避免地扮演了一个在人生悲剧中死去的角色。但是,他的意志、品质中,仍然有着让他那恣睢无忌的暴发户儿子赵清肃然起敬的东西,这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
这篇小说的两个青年女性,小静和小梅刻划得很有意味。小静有点像《秋之惑》中的二丫。她的感情需要一旦被意识到,就如泛滥的春水一样不可遏制。她当然不像农村姑娘二丫那样自抑,但她却像二丫一样,受到了恪守古老家风的长辈痛心疾首的诅咒。与其说她死于偶然的车祸,不如说她死于过于沉重的精神的迫压。她的姐姐小梅在冷眼旁观了家庭成员的各种命运变化之后,也毅然地走上了小静的道路,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她相信明天的太阳和今天一样明亮,充满信心地迎着明天的太阳走去。
看来,对于在生活中有自己确定的位置并从事着紧张的平凡的劳动的广大中国当代青年来说,理想的召唤,价值的选择,爱情的追求这样一些精神性的东西,并没有在万花筒般旋动的当代生活的“迷阵”中失落,它们仍然在严肃的作家的笔下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并且以一种恒久的魅力扣动着当代读者的心弦。这也是“顽主”和“摇滚青年”们决难企及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