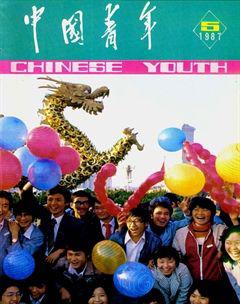论哥们情分与立字为据
米博华
此篇情,探讨的不是诸如族叔以人情之蜜弹击中了“片警”之腹,将罪在不赦的本家侄儿保了下来等等徇情枉法之事。这里说的,是一种在我们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活动中,由于缺乏法的观念而造成的更常见更大量的纠葛,虽不涉及杀人越货,但缠挟起来令人神伤、落泪……
我乡农民老乡亲近年来种梨树致富,很自然地被卷入商品经济的新疆域,而对批发、零售、借贷、利息、资金周转、回扣等等商品交换的诸多环节,颇感陌生,折本赔钱,被“涮”被“耍”的事所在多有。姑举两桩奇事,试作门外谈。
其一,一位大叔,今年收梨甚丰,拟将两万斤雪梨贩到广州,据说那里的价钱看好。经朋友介绍,此叔和广州一贸易货栈挂上了(后来得知此货栈系仨街头崽所为)。大叔亲赴广州,货栈各位“经理”殷勤备至,请大叔住“白天鹅”,吃“大三元”,不几日,便互相之间言必称兄弟。“经理”们称,本货栈阮囊羞涩,资金拮据,请大叔先发货,出手后再付钱。有人以为不妥,买卖不能这样做,即使做也得立个字据什么的。然而“经理”们说得亲切:“老哥您还信不过我?!”大叔觉得此般情分难道还要立什么字据不成,见外了。于是回乡发货。然而悠悠过了半年,连个钱影也不见,再找诸“经理”,皆称绝无此事。呼唤警方,但此案根本无法成立,一句话就把大叔问傻了:“有何凭证?”
其二,一位大伯,找邻村一老乡亲借资金100元买化肥,是请了中人,立了字据的。字据写得简单:“今有马圈村刘大保借王佐村柴又门人民币100元,口说无凭,立字为据。”但过了秋,王佐村柴又门持此据索钱时,借条上的100元变成了1000元。官司打到乡里,柴家男丁多,是大户,中人不敢惹,说记不清了。大保伯吃了亏,却有口难辩。借条上写得分明,乡里首长也难断真伪;告到县上,仍无结果。大伯只好认赔。找到当记者的我,也是枉然。一张毛边破纸能说明什么,大伯所言是真是假,我也说不清。我有个馊主意,但没出。看字面,借和被借的关系十分含糊,借“刘大保借……”一句,就能使大伯变成债主。但那着实太损了。
农民种了一辈子地,做生意是门外汉,连做生意的规矩都不懂,不被坑才怪哩。有没有生意法,我不知道,但没有法,没有规矩,或不懂法,不懂规矩,没准得把命搭进去!这并非危言耸听。听说有本书叫《论契约》,我没看过。作者的名字叽哩咕噜也记不得了。不管此书讲的是怎样的道理,我想,我们的生活中特别是经济活动中,有这种契约的习惯和精神,恐怕是必要的。
我理解,契约不外是当事人双方彼此履行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证明。协议也罢,合同也罢,大概都是这个意思。这东西好象是没有多少人情在里面的,定下来就有约束力。管他侄叔爷娘,谁都不能赖帐。这东西虽然比较可靠,但很可能违碍情面,显得冷冰冰的,故我们的老乡亲或城里的市民们,对此不大习惯。但随着社会生活逐步科学化,尤其是商品经济不断发达,契约的观念应愈来愈来浓。
譬如做买卖,除生意经外,还得有点法的意识。我乡大叔就是吃了这个亏。几万元的东西,怎能用“咱哥俩谁跟谁”之类的醉话结算。不要说上万元,就是几块钱的生意,就是表叔堂兄之间,也应清清楚楚。这不是不讲情分,而是说生意和情分得两下里说。依情分我可以免费供应大叔一顿酒饭,但要到我酒馆里吃酒,对不起,请如数付帐。至于那民间早已流传的“立字为据”,虽不失为好办法,但看来原始了些,远未达到法的水平。几个人坐屋里立据、画押、盖印章、按手印……其约束力也只能在本屋有效。类似的法律文件,似也应逐步科学化。至少要到法律公证处公证一下,大昭天下。我说这些门外论的意思概括起来无非两条:一、无论做什么事都应有法制意识,做生意尤然;二、法是科学的依据或依据的科学,原是应该而且可以做到郑重、严肃、有约束力的。不然的话,吃了冤枉官司都没法去告。它原本就是桩无头之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