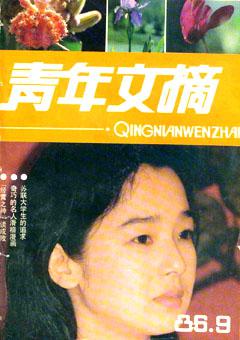心愿
向幼姝
她追求。整整二十年历尽磨难而不改初衷。
她不悔。假如再给她十次百次机会,她还要选择这个职业——当教师。
1979年初春,当她得知自己沉冤昭雪,又能回到讲台,回到学生中间时,竟象孩子一样哭了——自从1958年秋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迫离开学校,她朝思暮想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校园,梦萦魂绕的校园啊,对她,安黎,早已成为生活的世界,不能分割。那小小的讲台,对她有一种魔力,尽管生活的道路充满了坎坷,但她无论何时何地始终恪守着一个信念:要当老师,要当好老师!
她不服老。她沉浸在当老师的幸福之中,这居然有一种魔力……
压担子吧。一个肩膀担不动,就两个肩膀一起担。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跨两个年级同时开课;文科班班主任、高一年级组组长一身兼任,可真够她忙的了。
每周十八节课,要写十几个教案。
从早晨六点多离开家,一直忙到学生上完晚自习,等赶末班车回到家,就差不多到晚上十点了,上下班坐车的时间也利用起来,回忆教案纲目,推敲教法。
这样的生活节奏,即便是年轻人也难以承受,何况她已是年过半百的人。1984年冬,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她的腰部骨结核病复发了。伤口溃疡,长期不愈,她怀揣着病假条,天天到校,节节课不误。“也许有一天,倒下就起不来了,但我是老师啊,倒,也要倒在讲台上。”
她的家离学校有二十多里路。一天早上下大雪,路滑车挤,可她的腰疼得弯不下来,怎么也上不去车。她用两手扒住车门,车上的人连拉带拖,把她拽了上去。但她站不稳,又一下子从车上摔了下来,胳膊和腿都碰破了。当她一瘸一拐地走进学校时,学生们聚拢在她的身边,恳求她:“老师,您就歇几天吧,我们一定好好学习,您放心吧!”
听了学生们的话,她心里暖融融的。以心换心,以爱换爱,她觉得自己是富翁,拥有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宝。这就是当老师的幸福啊!
记不得是哪位先哲说的了:追求幸福比幸福本身更幸福。如果没有这种追求,这种信念,这二十年,磕磕绊绊,沟沟坎坎,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下来呀。
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就开始了这种追求呢?她还记得,她的一位老师对她说:“安黎,去当老师吧,和孩子们在一起你会永远年轻的。”那是1955年,她就要从山东大学毕业了,老师对她寄予了厚望。不过,当时她还从来没想过要当老师。
可党需要她当老师呀。她来到了山东胶县师范学校。在那火一样的建设年代,她深深迷上了当老师这一行。
那时候,自己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爱唱,爱跳,在课上是老师,在课后,简直分不出师生,可不象现在,都成了一个老太婆了……
“安老师,您可一定好好休息。您对我们是不是不放心呀?您就象相信您的儿女一样相信我们吧,我们可是一直把您看作是我们的妈妈……”
做母亲的幸福,也是当老师的幸福啊!她一天一付中药,整整熬了四个月,不知是药力,还是讲台的魔力,她的病渐渐好转了。
教书的艺术,被锤炼了三十年。她固执地认为,自己就是当老师的材料
要当一个好老师,可不容易。但安黎早在1957年、1958年,也就是她刚刚做了两、三年老师时,就以出色的教学被推上了观摩课的讲台。于是她觉得,自己最适合做老师。
重返讲台后,她又推出了“珠珠串联”教学法,使她的历史教学出神入化。用这种教学法,她把基础知识串成线,分成片,自如地将六本教科书压薄、填厚,从时间、空间、人物、背景等各种角度分析讲解,学生掌握起来既容易,又透彻。
有一副老对联:宝刀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也正道出了安黎追求的艰辛。
时间拉回到1956年。安黎随爱人调到济南。生活又给了她一次选择职业的机会。开始领略到当老师的幸福和快活的她,毫不犹豫地去市教育局报了到。她被安排到原济南三中。
然而,她没有想到,1958年“整风反右补课”中,竟莫名其妙地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她在教学上的摸索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安黎个人主义和成名成家思想严重,她鼓动学生考名牌,就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为自己树碑立传!”那时候,哪有安黎分辩的余地。揭发,批判,紧接着又宣布了一份不知何处审批的判决书:开除公职,回家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在三中校门口,她久久徘徊。再望一眼这熟悉的校园,再看一看深深眷恋的讲台,一行行热泪洒落在衣襟。
秋风瑟瑟,经路纬路纵横交错。而她,早已认定了一条路:当老师。她相信,春天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到了1959年年底,那些原来准备监督改造她一辈子的人,主动要求给她搞掉了那顶政治帽子。
安黎真没有想到这么快又回到讲台。回到三中,学校领导告诉她:不需要历史老师,要教,就教高中化学。教化学?安黎心中直打鼓:自己那点儿化学,还是上中学的时候学的,这么多年没摸了,能行吗?
但是,为了当老师,她决定改教化学。她和学生们一起领到化学课本,那上边的化学语言和符号似曾相识,却又是那么陌生。她从头学起,一遍又一遍地演题、做实验,虚心向老教师请教。从课桌走上讲台,试着教了一个学期,出乎意料,这个学期的教学竟得到了一致好评。
这个学期,她的月薪只有三十六元。她知道,自己得到的,却是无法用钱来计量的。那是当老师的幸福,是心灵的升华啊。
刚教了一个学期,到1960年暑假,三中迁往泰安。属留用察看、尚未重新入册的安黎又被迫离开学校。这位能够文理跨科教学的老师,又一次离开她热爱的学生。
她还是相信,自己肯定会再返讲台,自己的事业就在讲台上。
回到家,她又开始了另一种备课:把教案整理成册,节衣缩食买来各种工具书,为重返讲台潜心钻研、刻苦攻读。她能主宰自己,却不能主宰未来。1966年,“文革”开始了。安黎目睹那些被抄家抄出“变天帐”的无辜的人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只得狠狠心,含泪焚烧了苦心积累的教学资料。不久,抄家、批斗接踵而来。
当临时工,卖菜,当保姆,当壮工……只要她能干的,再后来,“清理阶级队伍”,她又被抛到了风口浪尖。街道里甚至她爱人单位里都把她当成了靶子,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把她揪出来批斗一顿。
即使如此,从1959年到1979年二十年间,她从没有放弃一切机会当代课老师。先后有五次,她被聘请为老师。只要能当老师,要她教什么,她就学什么,教什么。在当代课教师的断断续续的几年里,她教过历史、语文、生物、化学……
1974年,她听说解放路二小教师有空缺,便托人联系代课。她患骨结核卧床已经一年,未愈的伤口不时折磨她,无法步行到学校。她让儿子用自行车接送;讲课时站不住了,就趴在讲桌上讲。
童心的纯真,温暖着安黎的心。每当一次老师,她的信念就增添一分:当老师,当好老师。等待春天,决不沉沦!
她的追求不仅仅在讲台上
“身正为人范”,安黎给予她的学生的,是这样一位榜样:数九寒天,她早早赶到学校,点起火炉;盛夏酷暑,她一遍又一遍地在教室里洒水降温;有的同学在家吃不上早餐,她就为他们代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学生们学会了怎样关心别人,渐渐地,她的班成为团结友爱的集体。
学生们懂得这是母亲般的爱,没有一个人不理解她。1984年考取北京广播学院的张斌在给她的信中说:“在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出您和我们相处的情景,不管是严厉的批评,还是慈母般的关怀,都同样使人感到亲切。”老师的爱赢得了学生的爱:“老师,当得知您获得山东省优秀园丁奖时,我高兴得当着同学的面跳了起来,我的心情,就象自己的妈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时一样激动……”
安黎回到三中七年了。她负责的班每年都被评为学校的先进班集体、先进团支部,三次被评为市里先进集体。她本人也先后被评为济南市先进工作者和优秀班主任,1984年获得了省优秀园丁奖,市教育局和一些学校请她作报告,济南电视台还为她录了相。这一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终于,她又登上了讲台。这一回,她相信绝不会再悲忿而去了。这就是她所追求的补偿:把青年时代的理想,中年时代的希望,都做为现在工作的砝码,加在生命的天平上……
(清彬推荐、摘自1986年4月26日《中国教育报》)
(题图:缪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