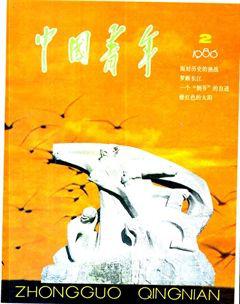成功者的启示
石湾
文学创作是个迷人的事业,尤其对于青年。近几年来,喜爱文学创作的青年人数之多,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代。这既令人高兴,又不免使人有几分忧虑:这么多青年都挤到“文学小道”上来,能有多少可以到达那辉煌目标呢?王银花的“我患了‘文学病吗?”的疑问,正道出千百万个“欲争无望,欲罢不忍”的文学青年那种痛苦、矛盾的心情。
今年仲夏,一家写作函授中心曾邀我去北戴河给参加笔会的学员讲课。我知道,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水平参差不齐,差别是相当大的。讲深了不是,讲浅了也不是,很难“讨好”。于是,我一再推辞。但是,主持笔会的同志恳切地对我说:“您不知道,他们的热情可有多高!有两个农民学员,是一对亲兄弟,为了凑足来参加笔会的费用,卖掉了一头牛呢!……”
我吃了一惊,琢磨了半天,我才下了“讲课”的决心。讲什么呢?就讲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其实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无非是举了一些当代作家如何成长起来的例子。我的用意是很明确的,希望学员们能认真权衡一下自己的条件和境况,如果很难有成功的可能,就赶快刹车,千万不要再为写作耗费精力和钱财。因为,我很为那卖了一头牛来赴笔会的兄弟俩担心,万一此行一无所获,岂不要后悔一辈子吗?
根据我个人的体验和我所接触到的情况,象王银花那样下点苦功夫,“记卡片,记人物思想笔记,注意观察人物和了解人物……”对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是不无益处的。但是,这样做未必就能成为一个作家。同时,文学创作也不象祖传秘方和特种技艺,可以父子相传,师徒授受。各种各样的创作函授中心也未必就能培养出作家来。事情往往是这样,一心想当作家的人成不了作家,而无意当作家的却冷不丁地写出了不起的作品。
我以为,有一个文学现象发人深省:“文革”之前,由大学中文系培养出来的作家(文学理论工作者除外)可谓凤毛麟角;而在“文革”之后,大学中文系却出了一批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梁晓声和王兆军,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毕业的乔雪竹、肖复兴、陆星儿及新近以《桑树坪纪事》而成名的朱小平,竟都是同届同班!我们不否认这两所大学对他们的培养,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作家,主要还在于他们都曾是在十年动乱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今活跃在文坛的青年作家中,张承志、郑义、史铁生、甘铁生、陶正和谭甫成,“文革”前夕原都是清华附中的同学。不用说,他们以前考入清华附中都是为了学理工。而一场动乱却使他们全都改变了志向,搞起文学创作来了。可见,作家并不是谁培养出来的,更不是哪个名作家或名编辑培养出来的,而是接受了时代和整个社会的培养,受了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熏陶,经历了各种生活和政治的磨炼而后才有可能成为有希望的作家。记得著名作家秦牧在“文革”前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现代中国作家中,几乎找不出一个其子女也是作家的例子。“文革”之后,情况有了变化,父子、母女均是作家或诗人的例子已不再希罕但是,这决不是身为父亲或母亲的作家把什么写作的诀窍授给了自己子女的结果。
就说在文坛上传为佳话的母女作家茹志鹃和王安忆吧。曾有人问茹志鹃:“你是怎样培养安忆的?”她是这样回答的:“我有三个孩子,如果我能够培养作家的话,我应当培养三个,而不是一个。事实上我的大女儿是个称职的语文教师,儿子老三是售票员。可见我培养不了作家,作家也绝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够培养出来的。”实际情况也如是,直到王安忆成名之后,她的好些作品茹志鹃都没有读过。阿城的情况也极相似。不少人知道,阿城的父亲钟惦棐是大名鼎鼎的文艺理论家。前些天,我陪一位记者采访阿城,当记者问道“你父亲是怎样辅导你”时,阿城颇为幽默地回答:“去年,我对父亲说,《上海文学》上发表了我的一篇小说,叫《棋王》,有空你看一看。我父亲很惊异,说:‘你会写小说?”我举这两个例子,不是说茹志鹃对王安忆、钟惦棐对阿城在文学修养方面一点家庭的熏陶和影响都没有,只是说,文学创作这件事是不能靠他人传授的,关键是要靠自己。
靠自己,又靠自己的什么呢?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又不在于你如何刻苦地练习写作,而首先在于你究竟为什么要写和有多少非写不可的东西。茹志鹃曾对文学爱好者说过:“千万不要抱着当作家的目的去硬写,一定要有话想说再写,只有这时候再来进行创作实践才是有益的。”王银花的信,只谈她怎样半夜里在被窝里打着电筒写,村里唱戏、演电影都不看,有了病也继续躲在屋里写等等,专一到了连婚姻大事都置之脑后的程度,至于她有什么不吐不快的题材、人物、故事和情感,却只字未提。似乎一切都是为了写,为了求得发表而已。
搞文学创作无疑是一种艰苦的劳动,要想获得成功,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王银花已经写了四年,许多稿子投寄出去之后杳无音信,好象编辑们都瞧不起她,令她感到“心寒”。其实,一篇稿子不被采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真正的好作品一般说来是不会被埋没的。如邵振国的《麦客》,曾多次遭到“枪毙”的命运,后来,他抱着最后一试的心理,投寄给了《当代》,结果被采用了,并获得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那些“一投即中”“一炮打响”的作家也绝不是凭着侥幸成功的。著名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就是“一炮打响”的作家。在他21岁那年,科尔沁草原上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案件,整个破获过程是可歌可泣的。这件事强烈地打动了他,他情不自禁地写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初稿信笔写来,洋洋洒洒,竟有四万五千多字,事件很不集中,主题也不够突出。他改了一遍又一遍,怎么也写不好,没有办法,他只好跟自己“作对”,将所有的原稿投进炉膛烧掉了。焚稿是痛苦的,但终于逼出了新路。写就了的新稿投到《人民文学》,很快就发表了。
我举这两个例子无疑是要说明,向大刊物投寄的稿子,最好是凝聚着自己心血的发愤之作。而王银花呢,四年来投寄出的许多稿件至今未响一炮。这时,我以为她应该审时度势,考虑一下是否应该改弦更张了。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这话,一般来说是对的。但是文学创作毕竟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劳动,假若你不具备合适的“土地”,那么,辛勤的劳动与伟大的成绩就未必是成正比的。这里就用得着“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老话了。因为文学作品是由思想、感情、生活、技法等组成,通过语言文字加以体现的。而这几者之中,生活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常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不是凡有丰富阅历的人都能写出好作品来。就拿近几年出现的“知青”作家群来说吧,较之“文革”中数以百万计的上山下乡的知青来,其比例是微乎其微的。一位也曾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劳动过的青年朋友对我说:“真是人和人不一样。那时候,我和阿城在一块地里干活,一张铺上睡觉,他经历过的事,我都经历过。没想到,他这两年写出了《棋王》、《树王》、《孩子王》,而我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更奇怪的,那时候谁也没见他写过什么。他爱好美术,大家是知道的;可没想到,他还会写小说,成了作家!这小子怕是有什么特异功能。”
阿城真有什么特异功能吗?没有。他在一份“小传”中写道:“……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十多年。1979年退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这样的经历,不超过任何中国人的想象力。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自己的小传?他说:“我是要告诉一些青年朋友,创作并不神秘,我能写出小说,他们也能写出小说,而且会比我写得好。”我说:“与你有相同经历的知青毕竟只有你写出了‘三王(即《棋王》《树王》《孩子王》)。”他笑了笑说:“那当然,有相同的生活经历,在内心未必有相同的感情经历。”我感到,他这句话道出了创作的真谛:要成为一个作家,就必须善于体察和感受生活,在生活中发现文学的美感!我想,王银花同志也是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发的。
最后,还得申明一点:我决不是想给王银花泼冷水,而只是想说,爱好文学,业余练习写作,就象人们业余爱好养花、钓鱼、打球、练拳一样,对陶冶情操、丰富生活是大有好处的,我十分赞成;但是不顾自身物质环境条件,不去认真体验感受生活与感情的内蕴,一头钻进所谓的文学创作里而难以自拔,并且把自己的成败荣辱与亲朋的理解、同情、支持联系起来,一旦无所建树,就怨天怨地,迁怒旁人,甚至失去生活、奋斗的信心,这都是不足取的。要知道,当作家,并不是谁立志要当就能当得成的,当你拿起笔的时候,要好好掂一掂它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