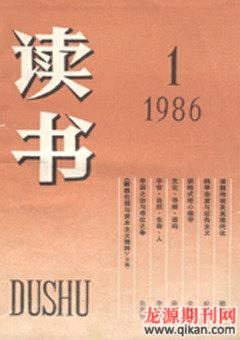科学态度与证伪主义
1.缘起
什么是“科学态度”?对此,波普尔作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回答。他不象通常那样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反面回答的。从正面,科学态度是指尊重证据、尊重事实的态度,也是严格根据经验的检验结果而追求真理的精神。波普尔并没有否定这一些,但他没有停留于这一些,他进一步从另外一面来看科学态度,即敢于怀疑原来的认识、大胆提出新的猜想、并根据经验事实检验的结果消除错误这样一种态度。
这二者角度不同。前者强调用经验事实去支持、证明一种认识,后者则着重以批判的精神为指导,用新的经验事实去怀疑甚至否定已有的认识。也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之为“证实主义”的态度和“证伪主义”的态度。这不过是同一种科学态度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它们都反对主观武断,反对科学上以不变应万变的教条主义态度,要求把人类的认识不断推向前进。证实和批判,只是这同一过程的不同环节罢了。
这一些,本来都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平淡无奇的。但是当波普尔以他特有的尖锐性发展出一种证伪主义哲学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了说明科学态度中的批判的精神、否定的精神,他特别强调了科学认识中也有错误,而且最后总要变成错误而让位于新的认识。他坚持,这正是科学的全部力量所在,也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根本特征。宗教教义中没有错误,玄学思辨中也没有错误,都是“永恒真理”,都不必再经受经验的检验。但也正因如此,它们也不是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经过波普尔把问题这么一提炼,就拉开了同传统观念的距离。当人们说什么是“科学的”,总是意味着它是可靠的,有根据的,经过事实检验过的,也就是说,它是没有错误的。怎么可以把科学同错误并列起来呢?这是对常识的挑战,而常识往往满足于一种面面俱到的、模棱两可的、未经理性反思的表面认识。
波普尔对科学和科学态度的这种理解,在三十年代就激动了国际学术界,但是完全没有波及中国。这大概是因为当时还刚刚对“赛先生”发出邀请未久,还忙于建立一种最起码的看重证据、服从经验事实裁决的科学态度,还来不及进到科学态度的更深层次上。直到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历史才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这时,历史的痛苦的反思使我们不再相信任何万古不变的教义了。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烈火的锻烧,不仅是非科学的或者以科学为装潢的东西是这样,即使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也未能幸免。于是,在这种时代的精神气氛中,波普尔的思想才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第一次在中国的大气层中弥散开来,成为反对教条主义、澄清真理标准问题的一种辅助的武器。
从那时开始,我和我的一些同道们就考虑编译一本《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以弥补现有资料过于零碎的缺陷。后来发生的一点风风雨雨,似乎也从另一方面强调了对波普尔的哲学思想作一些较全面的绍介的必要性。今年,书要付印了,我才想到请作者本人写序的事。多少有点出乎意料,这位年高望重的哲学家很快就寄来了为这本选集所写的《前言》,篇幅虽然简短,却抓住了他的全部科学哲学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他对科学态度的独树一帜的看法。让我先把这篇《前言》全文
2.《前言》
能够应中国译者之请来为这样一本我在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著作的中译本选集写一篇前言,我感到十分高兴。
我的著作是想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犯错误的,因为我们都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因而错误是可以得到原谅的。
这是我对科学的一个方面的看法:夸大科学的权威性是不对的。人们尽可以把科学的历史看作发现理论、摈弃错了的理论并以更好的理论取而代之的历史。
我从未到过中国;最接近中国的是我在香港大学当了几年特邀主考,并在一九六三年到那里访问过几个星期。当我在伦敦教书的时候,以及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我都有过几个很好的中国学生。但这个经历还不足以使我对下述一事作出是否属实的判断:据说中国流行的生活态度都认为犯错误是丢面子的。如果这确实是真的,那么根据我对科学的看法就要求改变这种态度。甚至应当代之以另一种相反的态度。如果有人发现了你的一种错误看法,你应当对此表示感谢;对于批评你的错误想法的人,你也应当表示感谢,因为这会导致改正错误,从而使我们更接近于真理。我说过,我无法判断那种认为犯错误就丢了面子的态度是否真是中国人民的性格。但我确实碰到过很多很多欧洲人和美国人都采取这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如我所说,是同科学态度不相容的。
我发现,欧洲和美国有许多人,其中也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在生活中都采取这种态度,并对改正错误感到十分不快:他们实在忍受不了还要去改正错误。可以把这种态度叫做权威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态度。持有这种态度的人总是认为,他们是权威或者专家,因而有责任认识得完全正确。但如果我的科学观是对的,那么你的认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因为根据我的科学观,任何科学理论都是试探性的,暂时的,猜测的:它们都是试探性假说,而且永远都是这样的试探性假说。
当然,无论在欧洲或者在美国,我的观点都受到非难,现在也仍然有很多非难。有时不仅受到非难,甚至还受到批判,就是说,人们也有时,尽管很罕见,提出一些根据来证明我的观点不可能对。根据之一就是我们的技术和工艺的成就,例如医学技术。但是,没有别的例子比医学或医学技术更能说明我们是怎样通过消除错误而前进的事实了。实际上只有当医学技术学会了自我批评以后,它才成了医学科学,并且通过批判地修正医学教条而取得了伟大的进步。
不应当把我的观点误解为我们不可能得到真理。我不怀疑我们有许多科学理论是真实的;我所要说的是,我们无法确定任何一个理论是不是真理,因而我们必须作好准备,有些最为我们偏爱的理论到头来却原来并不真实。既然我们需要真理,既然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获得真实的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想到这样的可能性,即我们的理论不管目前是多么成功,却未必完全真实,它只不过是真理的一种近似,为了找到更好的近似,我们除了对理论进行理性批判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理性批判并不是针对个人的。它不去批判相信某一理论的个人,它只批判理论本身。我们必须尊重个人以及由个人所创造的观念,即使这些观念错了。如果不去创造观念———新的观念甚至革命性的观念,我们就会永远一事无成。但是既然创造了并阐明了这种观念,我们就有责任批判地对待它们。
人是生物机体,一切生物机体都要犯错误。自然界本身就犯错误。但人又是一种十分特别的机体。我们拥有由我们自由支配的语言。这种特殊的成就,即语言和书写,是我们同其他动物的最大的区别之处。
但是这一点恰恰使我们能够进行批判。把我们的理论化为语言,写下来,就把它们置于我们之外了,既然置于我们之外,我们就可以作为客观存在、即再也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的存在而加以批判了。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成了科学家。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日
3.评论
在这里,波普尔用了一种十分朴实清澈的语言说明关于科学态度的一个主要问题——对错误的原谅的、宽容的态度。这不是出于别的原因,而是由于一个基本的事实:自然界本身就在犯“错误”。这并不完全是拟人化。现代科学已表明,宇宙的演化、地球的变迁、生物的进化都沿着一个大体确定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自然界本身就具有某种增加确定性而减少不确定性的趋势,这也就是方向性或目的性。为了不断趋向于这个目的,自然界必须付出代价。原始物质要经过几十亿年,经过不知多少次碰撞,才能形成最初几个有机分子。生物基因也只有经过亿万次的有害变异,才有概率近于零的变异被选择出来,参与进化的链条。如果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自然过程看作有目的的,那么也就可以在同样意义上把偏离这个目的的自然行为看作是“错误”。这样,这整个过程也就成了波普尔所说的“试探-错误”的过程。这就是说,自然界也象人类一样,也是通过多方试探和消除错误的试探中而进化着。在他看来,这不仅不是拟人化,而且人类和科学的进化正是这个自然界的试探过程在更高阶段上的继续。
试探和错误(或除错)使自然界增添了新的组织形态:新的天体,新的元素,新的物种。这是自然界本身的创造过程,是创造性进化过程。这个创造是从试探开始的,而绝大多数的试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百分之百,都是在后来的选择中被淘汰的,都是有害于进化的,因而也都是错误。但是,一切最终的创造,组成自然进化链条的“正确”的创造,却都是从这些错误的沙丘中涌现的。没有错误也就没有正确。如果为了杜绝错误而禁止一切创造的试探,也就从根本上堵塞了进化的道路。
波普尔所说的科学态度,并不是消极地清扫错误的态度,更不是有的人所误解的姑息错误甚至赞美错误的态度,而主要是鼓励创造的态度,它支持那种为了创造、为了前进而不惜犯错误的勇敢精神。真的,如果上帝也在犯错误,为什么还要苛求于我们这些平凡卑微的人呢?波普尔第一次把科学态度的问题提到了一个本体论的高度上来理解。
这样一种科学态度,是超越于科学本身的范围的。科学无疑是今天所有人类认识中最可靠也最有用的一种认识了。但即使这种认识也只是一些假说和猜想,并不绝对可靠,更不要说永远可靠。在浩茫无垠的大自然面前,在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中,人类认识了多少呢?已有知识/无限,只能接近于零!根据这个事实,波普尔要求我们勇敢地回到苏格拉底式的东方圣哲们的态度:我无知!应当随时提醒我们自己:我是不是错了?如果象牛顿力学那么伟大的科学理论最后都发现有错误,那么我们怎么还能相信自己永远不会错呢?完美无缺的真理是令人痛苦的,因为再也不需要新的创造了,也不需要听取任何别的意见了,任何不同意见都成了真理的敌人。相反,如果在真理面前采取一种谦卑的态度,就可能培育一种高尚的反省精神,激发人类的美好的情操,使人们比较尊重别人,理解别人的选择,包括错误的选择。这显然有助于建立一种人与人平等相待的民主关系。年逾八旬的波普尔近年来反复论述这种科学态度与民主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在一个民主制度正不断遭到损伤的世界上重振民主精神。这里凝聚了他毕生的体验。显然,这样的科学态度已不仅仅是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也是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一种生活态度,人生态度,也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选择的一种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
但是这里也提出另一方面的问题:如果这种科学态度是一种植根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生活方式,那么,它能不能脱离特定的文化环境而孤立地发展呢?波普尔敏锐地观察到中国人的一种国民性:把犯错误看作丢面子的事。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态度问题。人们马上就会想到我们的文化结构中权威主义的悠久传统。这种传统要求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即随时警惕不要违反上天、君王以及古圣先贤们所规定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行为的永恒准则。如果不幸违反了,出现了错误,就往往不仅是认识错误的问题,还要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甚至政治上的惩罚。在历代王朝的权利斗争中,当人们的“错误”也被利用来作为斗争的筹码时,情况就更加如此了。在这样的传统中,错误是瘟疫,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能不丢面子呢?这种遗风传到现在,就集中表现为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生理想(或无理想)或处世哲学:牺牲一切创造性以回避道德上蒙受耻辱及政治上陷入罪恶。我不是说这就是我们文化传统的全部。这只是一部分。我们的传统中也有“天命不足畏”的一面,我们的古代圣人也曾塑造过“闻过则喜”、“过则无惮改”的不怕错误的理想人格,但这一面往往不能占有更大的优势。更多的则是文过饰非、诿过于人那种波普尔意义上的反科学态度,因为如他所说,人们“忍受不了改正错误”。
五四时代中国的一些优秀思想家们曾热衷于邀请“赛先生”来华拯救中国,他们相信只要有了科学,中国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后来的人们则进一步发现,科学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整个传统文化背景中某些因素又在阻碍着科学的发展。因此,建立一种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改变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也即整个文化传统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需要把波普尔的问题倒转一下。
波普尔说,他的科学哲学是想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他试图深入到人类本性中寻求科学态度的心理根源。他相信人类的理性,相信人都有创造的冲动、理智的爱以及对知识的渴望。这就推动了人们可能超越自我,不顾个人利害而追求离开人而外化的客观知识,即他所谓世界了。他用一颗哲学家的童心信赖人类这种清醒而善良的本性,正象中国的圣哲们对于人皆有之的“是非之心”和良知良能的信赖一样。
我想在这里作一点补充。在我看来,人类的这种理性精神又是透过人们暂时的需要、愿望、偏好的折光而表现出来的,这二者也时常发生冲突。科学要求无情的批判,但是一种理论的发明者却往往倾向于坚守原地,无视可能足以反驳他的理论的反证。他往往被自己的偏爱蒙蔽了理性的眼睛。科学的发展总是反复经历这样一些感情的干扰,才曲折地实现着波普尔的“猜想—反驳—新的猜想”那个理想模式。而且还不仅如此。在科学的实际历史中,人们的这种坚韧性或者说顽固态度,在一定限度内往往又是科学所需要的。科学需要一些“顽固派”来保持结构上的某种相对稳定性。如果科学对于现象世界中的千变万化太过敏感,太容易屈服于日常经验的日新月异,它就无法形成某种稳定的结构,从而也就无从充分展现出一种理论框架内部的潜力。看来,人性中也有这另外一面,这也同样是一种理性精神,而且也同样构成科学态度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试想,如果爱因斯坦太过重视某些实验数据,他不是早就放弃了他的相对论吗?
科学是人的本性的外在展现,它也必然表现着人性的不同的侧面,不仅包括它的辉光,也包括它的阴影,它的弱点。当这种坚韧精神发展成为一种教条主义的顽症时,就成了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另一方面,当批判精神被放大为一种失去任何信念的怀疑主义时,也将使科学陷入
人性中的不同侧面,是透过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而实现的,经过这一结构的加工,放大或者缩小,构成一定时期一定民族所特有的典型个性。如果我们把科学态度或科学精神放到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考察,也许会在波普尔的卓越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我们探求它的更为丰富多采的表现形式以及更为复杂多样的发展道路。
(《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纪树立等编译,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