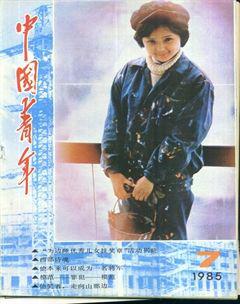“五拐厂”发家记
王泽华
四月,在华北电管局召开的线损会议上,一个拄着拐杖的青年走上了讲台,在众目瞪睽下侃侃而谈。他详细介绍了他们生产的节电“新式武器”的性能、用途、优点和不足,又条理分明地讲述了当前国内各家生产同类产品的状况。短短二十分钟的发言,惊动了满座高宾,引来了阵阵掌声。他吃惊了,眼睛湿润了。节电“新式武器”,还有别的一些“人无我有”的产品,都是从王中才和他的伙伴们手中升起的一颗颗“卫星”。这些“卫星”是怎样升空的呢?
就是要“顺着电光柱往天上爬”
王中才的家乡——河北省任丘县西方八村,人称“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条它都占了。可是一提生产,人们就耷拉脑袋。本来乡亲们盼望靠土地过好日子,可在那极左思想盛行的年头,再好的自然条件也不能为群众致富帮忙。有时日工值还不够买两张八分的邮票。
吃家乡水长大的王中才,因患先天性小儿麻痹腿残在家。他再也呆不住了,拄着拐杖,来找邻居袁震洞大伯。王中才想到自己过去学到的一些无线电技术,说:“大伯,乡亲们全都土里刨食,咋能富起来?你看咱村办个小无线电厂行不?”王中才是袁大伯眼皮底下长大的。老人早就知道这个年轻人有志向,心灵手巧,自学了不少维修收音机、电动机的本事,也拍手赞同。一老一少,便合谋着操持这件事了。
当时,在有些人看来,撸锄杠的手要握电烙铁,这简直是顺着电光柱往天上爬,忘记自己是土性人了。他俩走遍全村十四个小队,结果碰了十二次壁,好歹在各自的小队共借六百元作为本钱,还借用了两间四处透风的破坯房。
无线电厂的牌子亮出来了,各种议论也随之而来。“屎克螂能酿蜜,谁还养蜂呀?”“无线电厂干脆叫‘五拐厂吧,这么几个人就有五个拐子,还想赚钱?”王中才想,走一条新路有时会走岔,会跌跟头,但为了把大多数人吸引到这条路上来,自己甘愿撞大树,磨烂鞋底。他首先带领伙伴们研制高压试电笔。王中才心里早就盘算过,试电笔虽然搞的地方很多,但都是只能闪光。我要以新取胜,既让它能闪光,又要它带响。若能成功,每支笔可获80%的利润。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鏖战,头一炮打响了。试电笔接触高压线时,笔身的氖灯管,不仅顿时闪着光,而且能发出声响。王中才他们抱成一团欢呼着。
紧接着,王中才又带着大伙一鼓作气,试制成功“电子猫”。“电子猫”果然胜过大狸猫。在当地试验时,两小时内,一只“电子猫”共捕杀了193只老鼠。很快,“电子猫”成了畅销货。
第一年,这个被称为“五拐厂”的无线电厂,就向大队上缴了十万多元利润,成为全村由穷变富的转折点。更可贵的是给人们的思想带来的冲击波,连撸了一辈子锄杠的老汉们,也开始琢磨了:“要发家致富,除种地,俺该搞点啥营生?”
有自己的“智囊团”
电子学吸引着探索者,无数的竞争者在这一海洋里遨游。面对现实,王中才思忖着自己的厂情:厂小、人少、底子薄,但也不是无所作为。只要信息作前导,生产那些大企业顾不上,个体户又没法干的产品,就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立于不败之地。他决定到大企业的夹缝中去竞争,把注意力放在搞有自己特色的“独家产品”上。
标杆定好了,收集情报至关重要。王中才下本钱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智囊团”,他明确地向这几个人交待:你们可以“不坐班”,可以“叼水烟袋”,也可以当“甩手掌柜”,不过脑袋瓜里白天黑夜得装着四个字——“标新立异”。“智囊团”的成员们在其位、谋其政。他们绞尽脑汁地设计竞争力强的新产品,四处搜集电子市场的各种情报,使全厂生产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今春,北京某厂的业务员来洽谈业务,喝茶水闲聊时,谈到他们厂单身宿舍有人经常偷电,电流过量造成浪费不说,还常常弄得黑灯瞎火。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智囊团”成员远金池连夜把这个信息告诉给王中才,并建议抓紧试制照明限电器。王中才一拍大腿:“好!你这个参谋当得对,干!”没出十天,他们就搞出了十台照明限电器,并专程送货上门。北京那家工厂的领导正发愁对偷电的调皮鬼没法治,看到送到眼前的照明器,喜出望外,连声叫好。这笔生意做得太合算了,投资少,见效快,产品获得50%的利润。事情传出后,职工们都说:“智囊团”真是咱们厂生产的先行官!
王中才急了,他把拐棍一扔
王中才是以改革家的气魄治厂的。他认为工厂这辆大车,只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还不够,还得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只有两只“风火轮”并用,企业才能腾飞疾驰。
他首先着手改革工资制度,可有人担心会影响——部分人的积极性,思想有顾虑。去年底,厂里又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些人的思想还是拐不过弯来,意见不一,争得面红耳赤。这当口,王中才急了,他把拐棍一扔,拿自己打比方说:“咱们赛跑,谁能得第一名?”众人哄堂大笑。“那我要去领头奖,你们还使劲跑不?”大家的笑声戛然而止,转入了深深的思索……
今年伊始,他们就实行了基本工资与浮动工资相结合的新的计酬方法。全厂按工种、技术程度等制定了五种不同数量的基本工资,根据每人的劳动态度、贡献大小再决定增加多少浮动工资。这样一改,技术好的使出浑身解数,技术差的奋起直追,“九牛上坡,个个出力”,全厂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
王中才还大贴“招贤榜”。邻近的雄县,有两个小伙子,在印刷集成电路板上有“一招鲜”。王中才就把他们纳入麾下,允许他们请了四个帮工,在无线电厂内“私设”了个“小厂”。仅半年来,两个小伙子几乎每人月月挣三百多,高出本厂一些职工工资的五六倍。有人眼红了,找王中才说悄悄话:“这可坏了,你又没藏着个印票子的机器,给他们开那么多钱,咱厂这点利润,慢慢全得被他们蚕食了。”谁知,王中才听完哈哈大笑,掰着手指算起另一笔帐:“事儿不能这么看。你想,咱们印电路板都得往天津跑,印费高先甭说,光路费、旅馆费花多少?更要紧的是,他们出活快,两三天就能搞出来,时间就是金钱呀!”一席话,说得发牢骚的工友直挠后脑勺。
王中才待人,既冷又热。有时他象手里拎着一把黑虎铜锤,“上打天子下打臣”,六亲不认,翻脸无情。一次,王中才的好友姚根宝,在一张线路图上漏画了两个芝麻粒大的备用焊盘,被中才从被窝里叫醒。他只好领命冒雨回厂重新画,他知道,这位可爱的“拐厂长”,把本厂产品的声誉,看得比兄弟情谊重百倍!可有时,这位“可恨”的“拐厂长”又活象一个热心肠的大婶子。职工杨秀芹患急性胆囊炎,疼得正在家打滚,王中才领着医生推门而入,真神了!
有些知心朋友开玩笑说:中才,别看你成天拐着腿瞎忙,说不定哪天政策一变,就定你个“新型资本家”哩!
“党的政策又不是捏泥人。”王中才的嘴角露出自信的微笑。
王中才办无线电厂远近驰名。这时有人开始拉他另立摊子挣大钱。确实,凭他现在的技术水平,一年捞三四万元没问题,可他死活不去。他要和伙伴们一道,使父老乡亲们都富起来。他设想,往后全村三千多人中,得有70%的人搞工业,这才是城市周围有农村,农村里头有城市哩!
何等的气魄!有了王中才这样一批离土不离乡的人,农村的美景就在眼前。
(此稿系本刊通讯员张华英提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