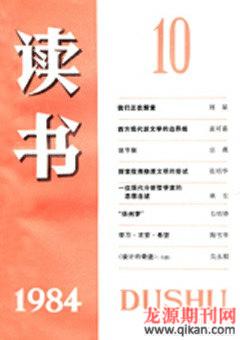学习·求索·希望
陶雪华
这篇小文,不是经验之谈。
仅仅谈谈我的学习生活,我的求索,我
的希望。
也记不清了,我为多少本外国文艺书籍设计了封面。朋友们都说我的封面设计“洋”。但很少人知道我从艺却是从“古”开始的。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令人难思难解。
人生道路上的转折又往往那样奇特。在我读书时期,曾狂热醉心于中国传统艺术。直至在朵云轩(这是家集“古”大成的书画社)实习期间,受到的都是传统艺术的熏陶。它是那样强烈的感染了我,“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多少画意诗情萦绕在我记忆的梦中。今天,当我从事外国文艺书装工作时,仍未忘情于它。
康平路上有座小楼。在我的记忆中,这座小楼永远是那么宁静。
楼前有个花园。春天来了,满园翠滴,白的蝴蝶,黄的蝴蝶,围着不知名的小花翻然飞舞,鸟儿啁啾,空气中荡漾着野草的清香。待北雁南飞,“黄花深巷,红叶低窗”,园中又是一番“飘零的美”。
在这静寂、恬静的氛围中,我沉浸于传统艺术的学习。
自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至元明清,多少稀世灿烂的民族艺术神品融溶于我心际。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楚江碧水,洞庭明月,怎不令人襟意浩荡,神思飞扬。
是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还是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是阎立本的《帝王图卷》还是董源的《潇湘图卷》;是李唐的《采薇图卷》还是马远的《踏歌图》……。
那严谨,缜密的结构,那幽雅、明净、富丽典雅的色彩,那如“春蚕吐丝”般飘逸的线条,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
“润物细无声”。它如春雨滋润了我的心田,培养了我渴求美的心灵。
一九七六年的秋天,在我的面前展开了另一个色彩绚烂的壮丽世界。
译文出版社开始出版禁锢多年的外国文艺作明。
那遥远的国度,我觉得陌生,生疏。
我的路困难重重。
当一本书籍放在桌上,要为它精心设计封面时,收集必要的资料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故事发生的时代,人物的服饰,小至帽子的式样等,也化费很多时间。但资料是死的,困难的是赋予毫无生气的资料以感情色彩,常常令我苦恼。
尽管天隔一方,人类追求光明,诅咒黑暗的感情是相通的。
寻寻觅觅,我寻求富有人情味的感觉。
常常有人问我的封面构思是怎样产生的?我很难一下子说清楚,触动我构思的也许是些毫不相干的事。
“谁知道一次邂逅,一句记在心中的话,梦,远方传来的声音,一滴水珠里的阳光或者船头上一声汽笛不就是这种刺激”,“我们周围世界的一切和我们自身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刺激”。这是巴乌斯托夫斯基说的。我觉得事情正是这样。
那是临近毕业分配的最后一个夏天里,我们是在乡下度过的。有一晚,我和同学们在川沙镇上吃了夜宵,趁兴踏着溶溶月色,朝白龙港走去。是去看日出?也说不清,只是感到在这茫茫夜色里走走很有情趣的。其实白龙港离川沙镇是很远的。那时我们不知道。
将近子夜时分,大地一片深沉,在弥漫苍穹的夜色里,星光闪闪烁烁。远处偶尔有几处橙色的光,大凡是村户人家在守夜。我们一群人也早已融入了周围的苍茫之中。“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仿佛到了另一世界,我们笑着,唱着,说着无关紧要的话。
那天晚上,我们感到特别兴奋,也许是这深蓝宝石似的夜空令人想起了什么……。
当朝霞初升之际,晨星的土地上扬起了牛马羊群的欢叫声时,我们还没有走到海边……。
岁月流逝。但不知为什么那个美丽的夏夜,当我为《卡彼拉篝火》构思封面时竟清晰地浮在我眼前。
它引起了我朦胧的思绪。
也许这是大规模的战斗前夕,庄重而宁静。犹如暴风雨来到之前,总有一段宁静的时刻。
在高高的森林里,稠密的云杉树遮挡了篝火的光,而烟穿过树枝,已化为袅袅的雾。
篝火旁,战士在沉思,唱歌,交谈。
战争的结局难以预料——在战斗遇到不幸的时候,这可能成为最后的聚会。为了明天的事业,战士的心是平静的。
我放弃了表现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我想这样更能揭示战士崇高的心灵美。
这是我寻觅的“情”和“意”。
这是一本诗集,书名《在大海边》。
封面无新奇之感,如果说有特点,那么“宁静”、“纯净”就是它的特点。
飘然欲逝的仙子融化在一泓蔚蓝色中。
生活中,有时看来很寻常的事与景却能引人思绪周匝。
我曾多次到太湖,听湖波拍岸,看水天一色。
太湖美,美在宁静中,美在纯净中。
悄然站在湖岸旁,沧溟空阔,浩渺无际。它把你的情思带向天际,随着点点白帆悠悠飘去……。
这一切都是“宁静”赋予的。
我把这种感觉融进了《在大海边》的封面中,留给读者更多的是遐想的空间。
想象、联想、幻想,在构思中是重要的。
生活中的意境美,需要我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去感受,去捕捉。
只有这样,才可能从生活的河流中淘取闪光的金沙。
立意在先,构图在后。构图依据于立意,是立意的物化。一个是无形的,一个是有形的。这形象思维活动的过程,也是艺术意境不断锤炼的过程。
书籍封面上所反映出来的,可以使读者感受到的,可以使读者联想到的,常常是作者精心安排的结果,也就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作者得于心,览者会其意”。这种精心安排我称之为构图。
画面中一切造型因子的安置,运用,都是为表达一种明确的“意念”服务的。也可以说构图是较注重于理性的思维活动。
中国画论中提出的“临见妙裁”、“经营位置”,其观点是一致的,同样也是把构图作为理性活动来看待的。纳入画面中的一切形与色,要经过巧妙的剪裁和精心的安置。
但精心安排一不等于图解,二不是故弄玄虚。前者不能引人联想,犯了“好尽之病,少含蓄也”。后者使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封面上表达的意念晦涩费解,读者思而不得,惘惘然,也失去了作用。
这是构图中的二忌。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重睹了郑板桥的令人叹绝的竹节书。
我爱郑板桥的画,更喜爱他的题跋。他的题跋借竹石以抒情,情有所发,很有味。这是以前观画时的想法。然而这一次,另有一种闪闪的东西在吸引着我。
纵观画面,他的题跋倏大倏小,忽粗忽细,忽疏忽密,姿意盘屈与画面溶为一体,形成了一种非凡的结构美、形式美。
我心里明白了,吸引我的正是这种特殊的形式美。
题跋引起我的沉思。
其实,诗、书、画、印合一是中国画的悠久传统。它们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相互补充,相互辉映,成为一个艺术整体。
从宋元起,文人画十分讲究题跋。他们认为题跋落款不是随意加上去的,在章法上题跋往往是作为绘画形象的补充而出现的,有的将题跋纳入画面,成为有意识的布局。其次题跋的大小、风格都要求与画风相和谐。“山石苍劲,宜款劲书,林木秀致,当题秀字。意笔用草,工笔用楷”即是此意。
题跋给予我启示。
我惊异地发现,书名的位置,体例的风格,字体的大小作为造型因子溶化在设计意图中,它将产生一个富有表现力的视觉世界,构成一种特殊的形式美。
这一点,我在为《日本俳句史》,《布拉热洛纳子爵》,《国际笔会作品选》设计封面时作了尝试,取得了效果。
反则,设计已定,那儿空书名就往那儿搁,仅仅把书名作为平衡因子来看待,其结果,书名的位置几乎是预定的,大多数是落在横径五二开,直径三二开上。从形式上讲,不免给人以落套之感。当然不是指所有的。
生活中处处孕育着美的形式。
化腐朽的树根为神奇的造型,是作者的慧眼。
它更多的是需要观察,研究,探索。
我希望,我设计的封面能给人以一种“新鲜”感。
探索新的表现形式是那样令人神往。尽管我追求的多,得到的少,但我没有怨言。
每当我的设计意图能被大家理解、接受时,我真感到高兴。
装帧设计在有些人看来是件很轻松的事,一张底色,一幅画,条字。但这种轻松感,我从来没有体会过。
有人曾以“纪律严格的狂想”来形容国际闻名的芬兰书籍设计家安第凯宁的风格。我深深体会到在这“狂想”的旋律中,充满了设计家的欢乐和痛苦,它时而令人惊奇,时而令人精疲力竭……。一幅优秀封面的问世,是作者辛勤地舐吮、润色、浇灌的结果。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
在书籍装帧艺术的天地里,把最美好的形象呈献给读者,这是我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