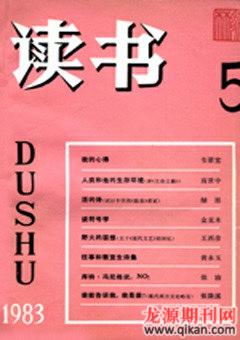野火的联想
王西彦
关于《现代文艺》的回忆
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间,正当震惊一时的“平江惨案”爆发以后,我从湘西南东走浙东,在自己家乡小住了一阵,于当年年底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去主编一个文艺性月刊,它就是一九四○年四月创刊的《现代文艺》。
出版这个刊物的,是一个由国民党省政府官办的改进出版社。不了解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和当地特殊的政治环境的人,也许会惊讶于官办的出版社为什么要来出版这样一个文艺刊物。原来担任省政府主席的,是一位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中的“开明派”。因此,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就有了可以容纳几个倾向进步的文化人和出版几种较为进步的书刊的空隙。当时担任出版社社长的黎烈文,就是和鲁迅有过交往的翻译家。怎样更有效果地利用这个机会,正是我们所考虑的。当我从浙东去闽西北时,当时在金华担任党的文化工作的邵荃麟同志交给我的任务,是到那里去开辟一个战斗的文艺阵地。
永安是个山区小城,从北门横穿市区到南门,大概只有两里左右。就在离北门口只有几百步远的城边,天色刚黑,就会传来猛虎衔走肥猪的惊呼声。而且,那里还是鼠疫流行、疟疾成灾的峦瘴之地。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空袭频繁,出版社的编辑部设在离城七、八里路外一处褴褛小村的一座破倒的小祠堂里,和城内的联系只靠一个工友兼伙夫的老头子每天一次的往返,他的主要任务自然是挑米买菜,所以即使是本地的报纸也要隔天才能见到,更不要说邮件文稿之类了。虽然在充当编辑部的祠堂旁边,相隔两百来步就有一家内迁的小小印刷所,使编辑工作得到一些方便,但毕竟永安地处东南一隅,联系广大大后方的交通极端不便,和当时文化中心的桂林、重庆等地通一封信也颇为渺茫,要按月编出一本刊物并发行出去,的确困难重重。好在荃麟同志答应最初几期稿子可由他在金华征集,记得我是身边带着好几篇文章才启程上路的。
但接着来的问题是,既然是开辟战斗阵地,那么应该选择一个怎样的攻击目标呢?回答这个问题时,就得关联到自己不久前的一些经历。我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在北平听到了芦沟桥的炮声,同年八月在上海碰上了淞沪抗战,到了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就参加了一个“战地服务团”,从武汉跑到鲁南、苏北的战地去做民运工作。当时我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阅世虽很浅,热情却颇高。可是,我在战地看到的竟是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是国民党军队的狼狈溃退和蹂躏百姓,是古运河两岸贫苦农民的深灾重难和哭诉无门。这些众多的战地见闻,就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究竟谁在抗战”的大问号。而在湘西南自己参加工作的一个报社和另一所学校的被查封,回到濒临沦陷的浙东家乡农村时目睹一些叔伯婶嫂们被抽丁加税迫得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更加深了这个急待回答的疑问。现在既然有了一个阵地,首先当然就要运用自己的方式来解答它。而且,这也的确是客观形势的要求。
在决定创办《现代文艺》时,我们就向四面八方发出征稿信。但在当时交通阻隔的情形下,很难在较短的时期里得到反应,更不要说寄来稿子了。何况还要选择进攻目标,真是谈何容易!可是,只经过短期的紧张准备,我们就编出创刊号,尽可能地体现出对“谁在抗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发表在这期刊物上的三个中、短篇小说,有两个是描写国民党士兵生活的,就是荃麟同志的中篇《英雄》和我自己写的短篇《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前者描写一个从抗战前线回乡的伤兵,他原是个给保长家打杂的,胡里胡涂地被送到战场上去,受了伤,被锯掉了一条膀子,回乡后却胡里胡涂被当做“民族英雄”重新送往战场。后者描写忠厚老实的农民在一个残酷的骗局里被联保主任送去当一名野战医院的担架兵,他在一次抢救伤兵时受了伤,结果自己也被放上担架,由别的担架兵抬下火线,一直到死“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躺在担架上的受伤者”,耳朵里还“清晰地听到无数别的受伤者的呻吟和叫喊”。这两篇作品,都是既有揭露,也有控诉。刊物一出版,我们就在等待反应。果然反应很快就来了,国民党省保安处一位处长老爷那个特别灵敏的鼻子,不仅一下子就嗅出《英雄》有“妨碍役政”的嫌疑,还断定编辑部藏匿着“异党分子”,提出要查封刊物和清除“异党”。在这样的时候,就得感谢那位“开明派”的省主席了,由于他拒绝批准保安处长的要求,才使得刊物能够继续生存。即使《英雄》一稿出现了麻烦,我们还是接连发表了艾芜同志的《意外》,描写一个被强拉去冒名顶替的农民士兵在点名时不肯承认自己改变姓名;魏伯同志的《号兵冯玉珂》,描写一个孩子号兵怎样念念不忘自己在战争中受辱而死的母亲,失散了的父亲和妹妹,又怎样在战斗中忘我地向敌人投出手榴弹。我自己也写了题名为《眷恋土地的人》的中篇,描写江北古运河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溃退时,一个被遗弃的船
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应以发表创作为主,这在编辑思想上是很明确的。但在编排的格式方面,我们不愿给自己制造固定的框子,而是尽可能多样化,例如目录和排次上,竭力顾到文章的意义和分量,有时也在字体上给读者以暗示,完全不掩盖主编人的观点。因此,发表理论文章时,也不一定都排在作品后面。创刊号上发表冯雪峰同志以“维山”的笔名写的《论典型的创造》一文时,不仅放在第一篇的地位,还在“编后记”里向读者特地作了推荐,说它“出于一个优秀的理论家的手笔的一篇见解精辟的文章,它指出我们抗战文艺一个最基本的缺点,说明了我们的艺术为什么还不能带来典型和深刻的思想”。当时冯雪峰同志正蛰居家乡义乌的佛堂镇,不久就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就在这期间,他给我们接连寄来了两篇论文,另一篇涉及文艺和政治关系的《文艺与政论》也受到了人们热切的注意。被捕前夕,他在给我的信里,说他正在为《现代文艺》写一篇关于曹禺的《雷雨》、《日出》和《原野》等三部剧作的评论文章,可是到期不见稿子寄到,写了信去催促,接到的却是他夫人何爱玉同志的一封短简,说是“福春先生已于×月×日出外”,我就猜到是怎么一回事情。后来,好象他再也没有把这篇文章写出来。除了雪峰同志的,我们还发表了欧阳凡海同志的《最近文学创作的一般倾向》、石滨同志的《创作实践与生活实践》和《民族传统与世界传统》、张天翼同志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等论文。“石滨”是出版社内部一位编辑的笔名,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很好的修养,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闽北武夷山。天翼同志的文章长达两万言,不仅立论精辟,而且语言生动,形象丰满,保留着他创作小说的那种特有风格,发表时也编排在第一篇地位,刊登了两期。
理论文章在显示刊物的倾向性时,比创作更为直接而明确。我们很重视它。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组织这类稿子很不容易。为了弥补不足,《现代文艺》特别设立了“短论”一栏,每期刊登三篇千字文,纵论各种文艺和创作问题。这个主意,记得是我和黎烈文商量决定的。三十年代黎在上海曾经主编过著名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和另一个《中流》半月刊,这两个刊物都刊登短篇文章,鲁迅有很多杂文和散文就发表在它们上面。三十年代还有个《文学》杂志,也曾辟过一个叫做“文学论坛”的栏目,鲁迅也是一位重要的执笔者。我们的设立“短论”,自然也受到上述刊物的启发。可是,这些短文无法向外地约稿,只能由出版社编辑部里的人自己来写。黎烈文和我两人每期都无法请假,特别是我这个具体负责的人,有很多期要独自凑上两篇甚至三篇。黎烈文写短论时的署名之一叫“尊寒”,是为了纪念他的亡妻严冰之的。荃麟和那位曾用“石滨”的笔名写论文的同志也经常写,荃麟的笔名是“契若”。我写的篇数最多,笔名也就最多,因事隔多年,有些连自己也忘记了,即使见到旧刊物也不能完全辨识。这类短论,大都有分明的针对性,有感而发,竭力做到简明扼要,不作泛论,不说废话。但正因为如此,就很容易犯忌,更难免得罪人。有的在稿子送审时被图书杂志审查处扣掉了,最初我们就留着一大块空白,标明“缓登”二字;有的被删掉了,也按照被删字数加上方框或×。使读者一望而知是怎么一回事情,可以运用自己的想象和推理来填补。可是,很快那些审查老爷们就变得聪明起来了,禁止我们那样做,好象天下压根儿就太平无事。这栏“短论”大概坚持了两卷,时间是一年多,直等“皖南事变”发生以后,环境更加困难了,才不得不忍痛放弃这种短兵相接的斗争。
同属于理论范围的,还有“书评”一栏。东南一隅的新书虽然不多,桂林和重庆等文化中心地区却时有出版,也经常有运到这偏僻小山城里来的。为了使刊物的内容能够稍稍多样,使读者对一些新的出版物有个选择的标准,当然也就是出于战斗的需要,每隔一两期,我们就发表一篇新书评论。这一栏的稿子,几乎近乎由我一人包办。我用了个使读者无法和我的本名产生联想的笔名,从“洪杨之乱”这个词里截取了前面两个字,颠倒了一下,自以为寓有“叛乱者”的意思。我评过艾青的诗集《他死在第二次》,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集《风陵渡》,芦焚的短篇小说集《无名氏》,林柯的话剧《沉渊》和谷斯范的章回体小说《新水浒》等作品,着眼点几乎都是文学艺术的现实效果,它和我们所发表的论文多讨论当前文艺问题,和在短论栏里一再批评有人鼓吹“描写与抗战无关的题材”的观点也都相通。我们的确力求保持理论上的一致性。
但这也不是说,我们要把《现代文艺》办成一个时事性过强的刊物。一则是看到在战局动乱和交通阻隔的情况下,忽略了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二是既然是文艺杂志,总不能不顾及它的多样化和艺术性;三是在出版社编辑部里有几位原来就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包括私人的藏书和几份预定的外国文艺期刊,如英文和法文的《国际文学》之类。黎烈文就是一位法国文学的介绍者,还和鲁迅、茅盾等一起参加编辑过著名的《译文》杂志。因此,在创刊号上,我们就发表了奥地利著名小说家斯丹芬·褚威格(Stefen Zweig)的《托尔斯泰传》的绪论:《托尔斯泰的思想》,并同时译载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人靠什么生活》。当时,褚威格以犹太作家的身份,受到希特勒的迫害,正流亡国外,我们发表他的著作也含有抗议法西斯暴政的用意。第二期更译载了法国古典作家梅里美(P.Mérimél)的著名短篇小说《掷骰戏》,还把它排列在创作小说的前面,更在“编后记”里向读者作了推荐。就在同一期里,为了纪念俄罗斯古典诗人莱蒙托夫,编了一个小小特辑。后来又编过纪念杜思退也夫斯基和高尔基的特辑。有时,没有组织到有份量的论文,我们也以重要的地位发表翻译,例如美国理论家梭罗(H.D.Thorau)的《论艺术与美》之类。还发表了好几篇翻译的作家和作品研究,例如柏林斯基的《论<堂·吉诃德>》。最主要的是,我们连载了两部外国作家的长篇小说,就是匈牙利作家霍尔发斯(O.D.Horvath)的《第三帝国的兵士》,由黎烈文从法译本转译,内容描写正当希特勒在欧洲耀武扬威时,一个德国兵士的变态心理,从它反映出希特勒的理想和方法将把德国青年引上怎样的道路。另一部褚威格的名著《马来亚的狂人》,出自陈占元的译笔。它是作者运用艺术形式来阐释弗洛伊德主义的重要作品,最足以表现褚威格的创作特色。就我个人说,我之所以会对褚威格着重心理分析的作品发生强烈兴趣,直到现在他还是我最爱读的作家之一,最初就由于编辑《现代文艺》时读到了他的一些论文和作品,知道他是一个对当时的法西斯野蛮势力表示抗议的正直的作家,他的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又激动着我年轻的心的缘故。他是一九四二年流亡巴西时自杀于里约热内卢的,在留下的绝命书里说明自杀的原因是“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已经沦亡和自己精神上的故乡已经毁灭”,更说明了他是一个以全生命热爱自己的家乡、祖国和人民的人。我们在译载他的论文和作品时,他还健在人间。即使我读到他的著作并不多,他那种真诚而勇敢的品质却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和影响。
在《现代文艺》上,我们还特地辟了一个小小的“作家短简”的栏目。当时我在文艺界的熟人不多,知道在向外地作家约稿时不能单靠以编辑部名义寄发出去的信件,因此尽可能争取黎烈文的帮助,请求他单独或和我一起署名,给一些朋友们写信。有的朋友很快就寄来了稿子,有的即使不能马上寄稿子,也多半写来了回信。我们考虑到偏处东南一隅的读者渴望知道远在大后方的作家们的消息,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有选择地刊登一些朋友们的短简。现在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这些书信也许已经成为弥可珍贵的史料。
自然,前面所说的种种,都是我负责编辑时的情形。我只编满了三卷,时间大约是两年。在稿件来源等重要方面,我得到多方的支持;但在事务工作上,却几乎等于单枪匹马,除了一位女校对,从征稿,看稿,编排,跑印刷所,开稿费单,等等,都自己动手。往往在一个月里,我要为刊物写好几篇文章,小说,散文,短论,书评,无所不为。不久以前,我托一家书店为我搜集到十多本旧刊物,一边翻阅,一边颇吃惊于当年自己兴趣的广泛和精力的充沛。也许读者会发现刊物上留有某些明显地为了应付政治压力的痕迹,我也不愿推卸责任。不无遗憾的是,由于年轻和经验不足,也缺乏战斗的韧性,并没有遭遇重大的挫折,我就轻易地放弃了那个阵地,离开了那个小小山城,前去当时的西南文化中心桂林。接编《现代文艺》的是靳以同志。这是只要从刊物面目的不无改变上,就不难看出来的。
出版社编辑部所在地的小村子名叫“虾蛤村”,居民贫苦,房屋褴褛,四周都是荒凉的山野,晚间常有野兽出没。我们那个破倒小祠堂,被高达丈余的茅草所包围,即使上只有两百来步远的小印刷所,最初也是用锄头弯刀斩荆断棘地开辟出一条小路,才能通行。村民们告诉说,就在这山麓茂密的茅草丛里,就曾经多次出现过猛虎,要我们散步时别忘记身上带盒火柴,要是发现猛虎就立刻点燃茅草,因为它见火就逃。如果没有火种,带个小锣什么的也成,因为它也害怕锣声。到气氛最紧张时,我们就在房间外面走廊里叠起桌凳,床头上放着火柴,桌子上准备好脸盆,以防万一饿虎闯来吃人。到了冬季茅草干枯,我们就在祠堂周围和进城的通路两侧大放野火。我就曾经被推举为“放火队”的队长,率领几位队员充当“放火英雄”,把熊熊野火一次又一次地从村边一直延展到几里路外去。
这样做时,我脑子里就会产生一个也许并不十分贴切的联想:自己编辑的这个刊物,岂不也是荒凉山野间的一小蓬野火,它将从乱草丛中开辟出一片沃土来播种庄稼、种植鲜花吗?当时我虽不敢把这个联想向人们公开,觉得在这个联想里未免包含有某种过高的自许;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每次回想起那个刊物,总不禁同时也想起冬季茅草干枯时在那个穷乡僻壤放野火的情景。因此,现在提笔写这篇回忆文章时,也就预先在稿纸上写下《野火的联想》这个也许并不十分贴切的题目。
一九八三年二月三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