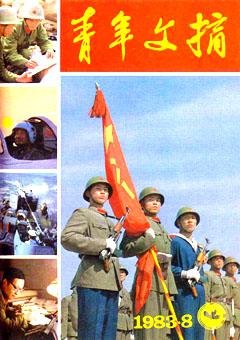漫话文章的开头与结尾
二 马
平淡的开头,难以唤起读者的兴味,而巧妙的开头,却富有引人人胜的魅力,令人一见钟情,读起来欲罢不能。鲁光写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的开头,以诗人的两句诗作开篇:“忠诚,就忠诚自己的土壤;追求,就追求自己的理想。”然后开首就写道:“这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这样的开头,对读者就颇有“引入”的力量。再如《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幽闲鼓吹”篇中,记有一则故事:唐代著名诗人李贺,在他未成名时,曾带着自己的诗稿,从家乡昌谷来到东京洛阳拜谒大文学家韩愈,正值韩愈刚刚会见过忧思满腹的孟郊,心情烦闷,非常困倦,对李贺这个无名后生本不欲接见,但当韩愈从仆人手中接过李贺的诗稿,第一眼看见题为《雁门太守行》的诗,顿时精神为之一振,睡意全消,立即吩咐仆人:“请客人!”原来韩愈被这首诗的开头“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两句所吸引了。这则故事,虽属文人轶事,却恰好说明文章的开头,确也危及全篇的命运。当然,衡量一篇文章开头的优劣,不应仅仅以“吸引力”大小为尺度。文章的开头,和文章的高潮、结局同样,都是通篇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开头,不仅要根据文章内容不同而变化,更重要的还必须与整个文章的主题思想相贴切。托尔斯泰说:“开头总是难下笔的,因为你宝贵你的思想,总怕把这一思想一开头就写坏了。”他还说:“不要认为修改是枯燥无味,应当在同一个地方经过十次、二十次的修改。”他的名著《战争与和平》的开头,就是修改过十五次之多。
文章的开头和结尾,虽然在形式上各居两端,实质上却是对立的统一体。好的开头和结尾,都会给读者以深刻的启示和引导。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通过“引入”,让读者接受感染和熏陶;一个则通过“引出”,让读者在感受作品的基础上,做到举一反三,浮想联翩。
前不久,偶读《梅兰芳与霸王别姬》一文,据作者徐兰源先生说,三十年代梅兰芳在香港演出《霸王别姬》时,每演到项羽见虞姬自刎后念“啊呀!带马!”锣鼓起“急急风”下场,观众就“开闸”,无心再看下场了。什么原因呢?当时有人认为是梅兰芳下场不出台了,可是梅兰芳却说:“观众离地,恐怕不完全是因为人的关系,而是戏的问题。情节发展到这里,整个扣子解开了,再往下演就显得拖和无力了。”他说:“戏,应该给人们不尽有余的感觉才好。”
“不尽有余”——这颇富哲理的四个字,很值得玩味深思。戏的结尾做不到不尽有余,观众就要“开闸”,文章的结尾如果不能耐人寻味,同样也是不会受到读者赞赏的。我国古代一些作文名家,在结尾上那种经过苦心推敲而产生的珍品,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欧阳修写的一篇题跋文字——《跋后汉郎中王君碑》,结尾时作者并没有采用惯常的“矣”“焉”“哉”等,而是婉转迂回,言虽尽,而意未尽。这种“含蓄不尽”“意境深邃”的收尾方式,在鲁迅先生笔下也是屡见不鲜的。如他的《故乡》的结尾就十分脍炙人口——“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好的文章,不应当象候鸟一样,唱完了它嘹亮的最后一句马上就飞走了。巧妙的结尾,既是故事的终结,又是故事的发端。它能扣开读者的心灵之门,深入到人们的心里作巢。。它的力量就在于:不仅能唤起你的重新回忆,而且又象一个浪花,能使你越过故事情节的海洋,掩卷而思,仍遐想不已。
关于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我国古人讲过一些颇为精辟的意见。如元人乔梦符在谈到写作“乐府”(一种民歌性的诗体)的章法时,就概括了六个字:“凤头、猪肚、豹尾”。头要象“凤头”那样漂亮、俊秀;体要象“猪肚”那样饱满、充实;尾要象“豹尾”那样结实、有力。明人谢榛把这问题说得更为形象,他说:“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想想看,文章的开头要象放炮,骤然一响,怎能不令入耳目为之一震;结尾要象撞钟,又怎能不使人觉得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呢!
(摘自《新村》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