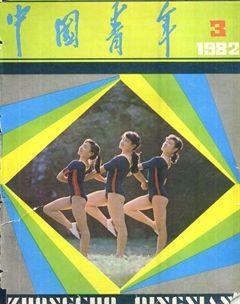啊,朋友
郑万隆
一
张泰安32岁了,还没找上对象。人到了年龄,内心深处一些微妙的变化,冷不丁地就会漏出来。那天,他骑着杨东来那辆破车从邮局取包裹回来,一是骑得太快,二是躲一辆拐弯的汽车,三是前后闸都不灵—把那个女医生撞倒了,把人家的前轱辘撞拧了,一瓶子红东西打破了,那是新鲜的血浆。那个女医生手捂着胳膊肘从地上站起来,热辣辣地望着他,面颊上现出鲜艳的红晕。他等着挨骂。可姑娘的目光却移到地上,深深叹了口气:“我倒没什么,车也不要紧,可这血浆……”看热闹的谁也不说话,看热闹呗。张泰安的舌头好象咽到了肚子里。那位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吼道:“让他赔!把瓶子撞破了,没把他的脑袋撞扁,便宜他了!”跟着哼了一声,完成任务一样开着车走了。张泰安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红着脸说:“我赔吧,抽我的血!我是O型的,抽多少都行!”“抽多少都行?你知道你一共有多少CC血吗?”那个医生噗哧一声笑了:“你扛着我的车,我推着你的车,到我们医院去吧,干嘛让人家象看耍猴似的围着。”那微笑是善意的,温柔的。她十分爽快地解释道:“我只是想让你给证明一下……”人家没让他献血,没让他赔钱,连自行车也没让他给修;而且还问他是否耽误了上班。可他却连人家的姓名都没打听,连句“谢谢”都忘了说。
就这么个事儿,因为在杨东来家里吃饭,多喝了一点酒,象自行车胎漏气漏了出来,说得杨东来的眼珠儿直发亮:“棒槌!你简直是个棒槌!女人的真情从来都不显露出来,她这么办就是对你有意思了。真的,真的!”
张泰安听得微微一笑,眼睛直望着那透明的酒盅。他和杨东来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同学,一起插队又一起进厂的铁哥们儿。张泰安虽说长得黑点粗点,却是要个儿有个儿,要块儿有块儿;在车间里是班长,在夜大学里是机械课代表,上次破格调资升了一级,这次又被提名为生产标兵;但他对找对象的事儿似乎并不摆在心上。杨东来就不同了。他对付姑娘有的是办法,走到哪儿都能和姑娘们说笑到一块儿,仿佛他身上有一种什么魔力。在他们刚进厂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杨东来跑来,兴奋又有些得意地说:“你知道这个厂子里谁长得最漂亮?”“我不关心这个!”张泰安瞪了他一眼走开了。“你这个人!”杨东来追上去,扳着他的肩膀说:“你这个人就是死板,生活中少了这些玩艺还叫什么生活?我可是早就注意上她了,组装车间的,总穿一身白,象一片羽毛。听人说挺傲气的,我可是想碰一碰。你跟我一块去怎么样?不用你说话,你就在一边看着,学一学我怎么征服她。”吃午饭时候,杨东来硬把张泰安拉到了食堂门口,手捏两块钱象等电影票似的站着,有一条腿还弓起来一颤一颤的,象个等待决斗的骑士。“就是那个宝贝!”突然,他喊了一声,冲那片“羽毛”走去:“有富余餐卷吗?换咱一点。”“羽毛”怔了一下:“干嘛找我换,不去找膳食科?”“管理员不在,我看你挺好说话的。”“羽毛”和她的女伴们哧哧地笑了一阵,掏出一个精巧的钱包又犹豫了:“我的餐卷也不多了,你还是找别人吧。”“不多没关系,先借我吃这一顿的,到时候保证还你。我是铸件车间的,叫杨东来……”谁知道她又跟人家闲扯了些什么,张泰安都买好饭菜吃上了,他才和那片“羽毛”一起走进食堂:来到桌前,挺神秘地搓捻着饭票说:“怎么样?这是开始。”可没过几天,杨东来却又对他说:“没戏啦。人家已经结婚了,咱们晚进厂了一步。咱们插那几年队把什么都耽误了,连媳妇都得找剩的!”现在想想这些,张泰安还忍不住暗暗发笑。
“你得追!爱情这玩艺,你得敢爱才行。”杨东来满嘴喷着酒气,那对让酒壮得发红的眼直瞪瞪地盯着张泰安:“我们那口子就是我给抢来的!她原先有个朋友。那小子要相儿没相儿,要个儿没个儿,还是一对罗圈腿。她就是看上那小子的爸爸是副局长,前三门又闹了一套单元房!哼,冲这,我就跟那小子憋上劲了,不能什么好事都让他们占了去!……我说你也得这样。别象那两次,让我作了瘪子。”
——那两次……头一次是在乡下。张泰安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下河南干校几年就留在了当地,在北京没什么至亲的人了。杨东来从小爹死娘嫁人,他跟着伯父过,伯母待他不好,堂兄弟们也常欺负他,因此他对那个“家”根本没什么感情。过年时候,村里知青就剩下了他俩。除夕那天,中午和晚上在公社食堂聚餐,有酒有烟还有花生瓜子嗑。三星正南时候,他俩带着一点醉意回村,有一个邻村的女知青,他俩认识,就是叫不上名字,要和他俩一起走。这有什么问题,同病相怜嘛。到了河边,张泰安提出要把她一直送过河,送到村里,杨东来不想去。一是酒喝得有点多,二是昨天他在村里打扑克(实际上是赌钱)一宿没睡,困得浑身象散了架。这样,张泰安只好一人去送了。第二天,那位女同学送回一盖帘冻饺子以示谢意,他俩留她吃饭,言谈之中杨东来已看出来一点什么;初三那天,他俩在老乡家买了两只兔子,酱了,杨东来让张泰安给那个女同胞送一只去。张泰安说:“干嘛让我去送,你怎么不去?”杨东来捡了一只大个的,用旧报纸包起来,往腋下一夹:“好,我去就我去!为了你,就是跳井我也不含糊!”说完狗皮帽子往下拉了拉,顶着白毛风走了。他回来时候,狗皮帽子没了,棉大衣撕得稀里哗啦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干着一道子黑血。他让人打了。他过河到了村里,那个女同胞到镇上看野戏去了。他以为喊几声她不答应,一定是睡着了,又不知哪一个门,就在知青的排房前,挨个扒窗户往里看。村上的值班民兵以为他是偷东西的,把他好打了一顿,把酱兔肉也没收了,说这兔肉也是偷来的。可他回来一句也没对张泰安说,蒙起了大被睡觉,睡醒了就跟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他并不感到自己委屈可怜,他只是同情张泰安。他认为张泰安各方面都比他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物理尖子一定会成为“清华”的高才生。可下乡来,他身边却一本书都不带,干活睡觉,摇竹签看手相,一天说不了十句话。他觉得他有责任给这位朋友一点欢乐,一点希望。当然,他也没忘了找机会过河去报复一下。后来他找人学了几趟拳,练了几种擒拿格斗的招数,可惜一直也没有找到这种机会。
——第二次是去年,那是在夜大。其实,张泰安上夜大也是杨东来怂恿的。他本来对上夜大没什么兴趣,可杨东来替他报了名,眼睛里放出那种极亮极强烈的光:“凡是有咱们份儿的事,咱们就当仁不让。干吗不上?就老让人踩在脚下当仨孙子?棒槌!”棒槌?他俩在一起十几年了,可对生活的认识总是不一样—那天,立体几何的作业特别多,其中有两道题让他们全班人都冒了冷汗。“嗨,你过来一下。你给她帮帮忙。”杨东来把张泰安叫到一个女同学的桌前。女同学是金工车间的,叫贺小凡,给人的印象挺聪明挺高傲的,可第一道作业题就没做出来。就是从这道作业题开始,他们认识了,不期然而然地好了起来。贺小凡不知是为了表示什么还给他织了一个毛围巾,进而干涉起他的清洁卫生来了。张泰安收下了围巾,却嫌贺小凡的穿着太显眼,时不时要给她挑点儿毛病,敲敲警钟。当他们的关系成了全车间的“花边新闻”时,贺小凡突然不来上夜大了,而且见了张泰安就躲开。“你们俩吵架了?”杨东来发现了这个问题连一分钟也没敢耽误,就找到张泰安:“怎么贺小凡连我都不理了呢?”“不理就不理吧。她这个人生活作风不怎么样,插队的时候有个外号叫‘趿拉板儿。全厂都传开了,就你我不知道。”“是吗?”“我听和她一块插队的、七车间的何政说的。”“何政?那小于没几句真话,你怎么听他的?也许他是吃醋呢!”“我也问了贺小凡,她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没等我把话说完转身就走了。”“你可真是棒槌!”杨东来当天中午就找了何政,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问他:“贺小凡的外号是你传到厂子来的?”何政说:“是我又怎么样?她从插队到工厂搞了有一打对象了。”杨东来拍着胸脯说:“我也搞了十几个,你敢说我生活作风不好吗?你是不是因为她没跟你搞,你吃醋了?”何政话也不软:“‘趿拉板儿给了你多少钱,你这么给她卖力气?”杨东来把石棉工服脱下来往地上一扔:“我是气不忿儿来教训教训你的!以后不许你再给人家姑娘散布这些,把你那臭嘴闭起来!”两个人动起手来,杨东来连续把何政打了三次仰八叉,下巴颏磕破了,鼻子流出了血。何政被打寒了,杨东来还在教训他:“告诉你,我学过两套少林,还练过形意拳,教给你这几下,你以后就知道怎么做人了……”但没等他把何政教训完,他们就被一起叫到了保卫科。这下杨东来忽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还没等何政告状,他就抢先说:“我们不是打架,是他要跟我学拳,不信你们问问他!”在杨东来那种极亮极强烈的目光下,何政连连点看头说:“是,鼻子是我自己摔破的。”但是保卫科并没有放过杨东来。因为杨东来在他们眼里不是一个安分的工人。结果还是扣了他当月的奖金。杨东来不在乎一个月的奖金,他也没有跟张泰安表述这个经过。张泰安从侧面听说后,却既怪杨东来多事,把这本来悄悄的事公开了;又感激杨东来帮他完结了这个本来悄悄的事。所以,当杨东来向他表明贺小凡不是那种人,让他找她道个歉,言归于好时,他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没任何其它的表示。后来贺小凡又来夜大上学了,他也没有再和她谈一谈。
二
在杨东来家吃饭的第二天,张泰安的手指让泵座毛坯砸了—也许是让杨东来两口子咒的,也许是上帝的旨意,第三天感染了,第四天肿得胡萝卜一样。看来非去医院不可了,可他还想忍着。也是啊!那个女医生姓什么,多大年龄了,一概不知,让他怎么开口?说实在,他真是又想碰上她,又怕碰上她……
今天正好是杨东来倒休,车间里有一个人请了病假,张泰安就留下来上班了。这样,至少是不用去医院了。不去医院,就不用去“冒险”,也就不会有什么苦恼,什么麻烦。车间主任当然不会知道这些底里,班后会上,还当着全车间的人表扬了他。
失去的又得到补偿,这是心灵上的;可他的手却没有他那么大的耐性,折磨了他整整一夜。
第二天上班时候,杨东来一看他的手就大叫起来:“你,你怎么还不到医院去?你这个人……”
“嗨,没那严重!”张泰安装出若无其事地笑笑,爬上了化铁炉,用一只手和大伙一起检修。
杨东来叹口气出了车间,走了一个多小时没回来。
他一定又是钻到哪儿聊大天去了。这个人平日有点吊儿郎当,有时爱迟到早退,爱抬个杠出个风头;对领导有意见了,对什么事看不公了,不是玩一通“荤”的,就是泡上几天病假,在全车间也是挺难鼓捅的人物。但是干活的时候他也肯卖力气,哪儿脏哪儿累他在哪儿顶着。有一次化铁炉烧穿了,是他披上两件石棉衣钻到炉子底下打开放料阀的。还有一次铸件返工,他和张泰安两个人加了14个小时的班……再加上他很讲义气,班上的小青年都挺服他的,开口闭口“杨大哥”。然而领导们都不待见他,一说起他来就咂冷气,认为他不安分,浑身是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毛病,好象他们身上一点毛病也没有,什么后遗症都没留下。而张泰安的作用,就是在上下之间抹稀泥,谁也不得罪。领导就是领导,朋友就是朋友嘛。
炉顶活儿利索了。张泰安刚从梯子上下来,杨东来来了:两手举在胸前,右手虎口上有个一寸多长的口子,血还在往外冒。“走吧,我和你一起医院去!”
“你这是怎么弄的?”
“你甭管是怎么弄的了!快走吧,我陪你到医院去。”他那双极亮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笑着,“这回,你不想去也得去了!打胜了那一仗,咱们再回来打这一仗,炉体补膛的活儿我包了,保证下班以前交验。”
张泰安耸了耸肩。杨东来总是对什么都那么有信心,而且让人对他没办法…
到了医院,排队挂号,排队候诊,再排队到治疗室。那位女大夫就在这儿。好象她不管包扎换药,那里面有个观察床,她正和三四个男大夫在商量什么。“是她吗?”杨东来悄悄问过张泰安,骂了一句:“你这小子还挺有福气的!”
杨东来的声音很轻,但是屋里的人好象都听见了,连病人在内都在看他,斜着眼看他。他把下巴颏扬起来,注视着墙上的一张人体骨骼图,仿佛在图上发现了什么。紧贴在他身后的张泰安吓了一跳:“你可别在这儿闹出笑话来!”
杨东来只当没听见,径直向那个女大夫走去。
“包扎吗?坐在这儿等着。”一个脸部肌肉松弛的女大夫拦住了杨东来,命令他坐在一个圆凳上,脸上没一点表情,象个“女牢头”。
“我要找那个女大夫看。”杨东来指了指,皱着眉头说,“她叫什么来着?姓……”那样子好象他和她认识,早就认识。
“你管她姓什么呢!谁给你包扎还不是一样?”
“我就是要找她嘛!”杨东来把伤手举了起来。
“那,你坐下吧!”“女牢头”狠狠地瞪了杨东来一眼,给张泰安下了命令。
“不不,他也要等那位大夫……”杨东来一把拉住张泰安,冲那位“女牢头”咧嘴笑了笑。
“你们这是怎么啦?”“女牢头”扯下口罩刚要发脾气,那位女大夫笑盈盈地走来,温柔而又大方地对杨东来笑了笑说:“陈大姐,就让我给他们包扎吧。”
“你们这些年轻人可真难侍弄!”“女牢头”唠叨着走了开去。杨东来笑了:“我是为朋友来的,不然我才不愿意得罪她。不是吹的,要不是因为我朋友,我还从没进过医院呢。”说着闪开身,指着张泰安说,“我这个朋友您认识吧?”那口气,好象他和这位女大夫早已是朋友了。
“啊,认识,认识。”她笑得很含蓄,还是那么大方、温柔,但是没有去握张泰安伸过来的手。
“你们谁先包扎?”
“他先来。他叫张泰安,我们系统的‘准生产标兵,我们的班长,全厂有名能干的小伙。”杨东来把那个“准”字说得很轻很快,故意不让人听清,接下又介绍说:“他今年32岁,还没结婚呢……”
“呵……”女大夫笑出了声,眼睛眯起来很美,“你跟我说这些干吗?”
“随便聊聊。医生和病人之间应该加强了解。”
张泰安把头低了下去,脖子后起了一层红痧。
“您是刚到这个医院来的吧?怎么过去没见过您?”杨东来扫了一下四周的人,一条腿抖着,那只伤手也跟着颤。
那个女大夫又笑起来,笑得很甜很清脆:“您不是陪朋友第一次到医院来吗?怎么会见过我呢?我是前年从吉林医大毕业分配来的。”
“您也是单身一个人吗?”
“看您这个豪爽劲,您一定是个炼钢工人?”
“不,翻砂的。懂吗?就是铸工,我的朋友张泰安也是……”
张泰安还没等女大夫把绷带的最后一个扣儿系上就走出了治疗室。
“你们那儿的人都象您这样吗?”
“哪样?”
“象您这样直爽,又有点傲慢和不拘小节。”
“您怎么认为这是傲慢和不拘小节呢?我并没有得罪您呀,我只是为了朋友。”
“哟……”那女大夫又笑了,“您误解我了,我是觉得和您谈话很有意思……”
杨东来终于从那对明亮的眸子里看出了一点什么。他没等绷带扎好就站起来,礼貌地说声“谢谢”,头也不回地走了。
张泰安在医院门口等着他。
“算了吧,走吧,人家根本没那个意思。人家是正牌大学生,咱们算什么?嗨,亏透了!说实在,要不是让那个红箍儿套上,咱们不一样上正牌大学,一样有文凭?”他眼里一片阴影闪过以后,又露出了极亮极强烈的光:“没关系,只要咱们自己看得起自己,会有的,什么都会有的!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一个比她好的。真的,一定1”
张泰安淡淡一笑,摊开手来:“我本来就对此不感什么兴趣,是你硬拉我来的。”
“你……你呀!”杨东来盯了他一眼,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
三
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张泰安躺倒了。发烧,躺在宿舍里。大伙都以为夜里下雨,他受了风寒,或者伤口发炎了。咳,愿意怎么以为就怎么以为吧,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白天的宿舍里很静,不象晚上,总有人来看他。就是杨东来一直没露面。
张泰安回城三年了,好象一直没有功夫想想自己的事,这回病了,有的是功夫了,想吧,掰开了揉碎了地想吧。不知为什么,他却感到脑子里是一片空白,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苦闷之中。
张泰安一直觉得自己是把一切都看透了的。自从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父母去干校,他下乡插队,仿佛有一股汹涌的潮流,把他身边那些美好的东西全冲尽了。在这汹涌的潮流中,有的人逆流而上;有的人避得远远的,张泰安一直是裹挟在潮流中,在随着它而浮沉。他没有驾驭潮流的欲望,但毕竟是浮在面上,并没被冲到底层,还在潮流中裹挟来的残枝朽木中得到了一些东西。他觉得在现今世界里,一个有价值的见解远不如使自己得到平和、安宁实际。而要得到平和和安宁就要左右平衡,谨慎处世。其实,生活经验也正是这么告诉他的:论化铁和翻砂技术,论干活,杨东来都不比他差,而且选班长的时候,大伙举手最多的是杨东来。可车间党支部却认为杨东来这个人事多,爱提意见,不安分,让他来干。改进化铁焦化,是杨东来想出来的法儿,他俩一起干的,可推荐生产标兵的时候,车间里却又没提杨东来的名,说杨东来劳动纪律不好,平时吊儿郎当,当选了影响不好。在夜大机械系,杨东来的制图和机械理论都是全班第一名,就因为他说过“上夜校是来玩的,什么都得玩玩儿”,就没当上课代表……
张泰安一直觉得自己是有谱儿的。靠着这谱儿,他确实在潮流中得到了些什么。可在得到的同时也在失去。失去了又是些什么呢?不踏实?心的折磨?时不时的苦闷?每个人都会有得到和失去,杨东来又得到了什么呢?班长,标兵,课代表,党票,他都没得到,可他也决不会有那些折磨,那些苦恼。记得进城那天他就说过:“哈,咱们终于回城了,终于能够象个样儿地生活了!我这个人什么也不图,就图活得痛快,活得对得起自己!”人家整天乐颠颠的,周围总有那么多知心朋友。是的,他心里也有那么个谱儿。
张泰安不由得想起那次他和他为车间用砂子的事吵的一架。那是上个月的事。车间里铸型的砂子一直用的是清河砂石材料厂的,从那个月起不知为什么改用顺义县的了,而且是由三辆农村的大胶皮轱辘车管送。这批砂子质量不合乎要求,砂型使用时间短,损坏率大,直接影响到铸件产量。有一天,杨东来上班来点了个卯就不见了,直到第一炉铁出炉才回来,那脸色就象在外面和谁打了一架。他把张泰安拉到炉子后面说:“我看这砂料里面猫匿儿大了!材料科长的老丈母娘家就是顺义的,送砂料那几辆大车就是科长丈母娘那个大队的。”“你听谁说的?”“仓库磅房过秤的老单头说的。一颗过滤嘴的力量。他还让我保密。那老东西,好象他也吃上挂落儿了。”“你知道了又怎么样?算了,咱们心中有数就行了,科长有的是理由。”“那不行,工厂又不是他们家的买卖!中午那三个送砂子的还要来,我想找一个问问。你和我一块去,就说我们是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让他写个材料,咱们给捅上去。这厂子是国家的,不能谁有权,谁过手,就扒一层皮!”张泰安不去,杨东来脱了工作服,到工会办公室找人借了皮夹克和鸭舌帽换上,腋下夹一个操作记录的塑料夹子,自称是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大队与厂子挂钩经过,矇了那“负责的”,让他签上了字。结果那两个社员找来了科长,三言两语便吵了起来,科长要抢那份证明就动了手。倒霉的当然是科长:他的一个牙被打活动了,上衣的扣子全部被撕掉了…最后,科长的问题由厂党委办公室调查后处理,砂子还照样由顺义大冉各庄送;杨东来冒充纪检人员又打了人,被车间主任在会上批了一通,又扣了一个月奖金。张泰安因为和杨东来是好朋友,事出在他班上又不报告,也扣了一个月奖金。事过以后,杨东来大咧咧地说:“哼,一个月奖金算什么?我相信厂里看了那份材料,起码得给材料科长一个处分,最后胜利的还是我。”张泰安却责怪他多管闲事,爱表现自己。这话要是从别人嘴说出来也许没什么,张泰安嘴里说出来,杨东来受不了啦。他俩吵了起来,象两只斗红了眼的公鸡……但事后,杨东来似乎又把一切忘了,还是那么说说笑笑的,为张泰安的对象发愁。张泰安却总忘不了那一个月的奖金,车间主任大会上的批评和他的生产标兵……
“现在想起来,杨东来的谱儿虽说不实在,却似乎找着了个什么支撑点。而你呢?你总排遣不了那种越陷越深的无聊和空虚。你连自己都看不起,还依靠什么活着?”外面下起了雨,张泰安站在窗前,望着扑打玻璃窗的沙沙细雨,忽然想起要找杨东来谈谈。说实在,两天不见,他还真有点想杨东来了。
天刚黑,张泰安正要下楼去吃饭,想不到杨东来推门进来了,撩开雨帽,两眼闪着极亮的光:“有雨伞吗?”
“有。”
“楼下有人等你,你给她送去。今晚夜大有课,你也穿上雨衣一块儿去吧。吃的我给你准备好了。”
一个面包,里面夹着几片香肠。
“是谁在楼下等我?”
“你下去就知道了。”杨东来不由分说,把雨伞、雨衣还有好几天没动的书包一起塞进张泰安的怀里,“你可真是个棒槌!”
四
宿舍楼门口站着一个姑娘。细雨透过树叶,一阵一阵地洒在她的身上,她一动不动的,好象一座石雕像。
是贺小凡!这个很漂亮很骄傲的姑娘,她怎么会找他来了?
张泰安正要回头问杨东来,杨东来冲他挤着眼睛一笑:“你们一块走吧,今天晚上有事,我不去夜校了。”他象一条泥鳅钻进了雨里,两只雨靴在甬道旁的水洼里呱哪呱唧地响着。雨雾迷茫,路灯闪烁。他真象一个极亮光点飘动着,象发光的流星,耀亮了张泰安的眼睛。张泰安忽然发觉自己有很多对不起朋友的地方,心头就象针尖炙了一下。雨还在下着,他看了贺小凡一眼,发现贺小凡也正在看他。她那张脸让路灯光线勾勒出了一个轮廓,显得那么妩媚、迷人。她不会记恨过去的事了吧?说点什么呢?
“你……你也去上夜大吗?”这张嘴可真笨。
贺小凡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往前走着。
“你……你怎么不说话?”张泰安紧追了几步。
“还说什么呢?该说的,你不都已经说尽了吗?”在明晃晃的路灯下,她站住了:“我不明白,既然有了过去,你为什么还要今天再来找我呢?”
“我?……我……”
“你不是说我爱虚荣、目光短浅吗?你不是说你身为‘典型人物,凡事要注意影响吗?你不是怕和我约会影响了你的事业吗?!”
张泰安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是因为贺小凡翻出了他的往事,还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牵动了那一连串的弦儿?他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地说:“小凡,你听我说,过去……我是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我的心……我……”
“我不听,不听!你的心?还用再作什么表白吗?你怯懦,虚伪,你身上还有什么男子汉的影子?我真不明白,杨东来怎么会瞎了眼,看上你这么个哥儿们!我也真没想到,杨东来说的给我送伞的会是你。你可以走了,把你的伞也拿走吧!”
贺小凡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把伞推给了张泰安,自己站在雨雾中,听任雨水冲刷着她的脸。
张泰安接过伞,似乎想说什么,终于没能说出来。他低下头,默默地往前走去。雨还在下着,路很长。走了一截,他回过头,还看到贺小凡站在那儿。雨丝掉在脸上,凉嗖嗖的,张泰安忽然觉得自己这五尺高的大汉真象这路边被风吹落的一片片树叶,那么小,那么轻飘,随风在地上滚动着。他不由得感到一阵惶惑,仿佛从自己身上发现了什么,是什么呢……
雨在路灯光映照下,成了珠光闪闪的帘子,把一切遮在里面。许久许久,张泰安还在湿漉漉的马路上走着。
前边,那闪出桔黄色光亮的窗口,正是杨东来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