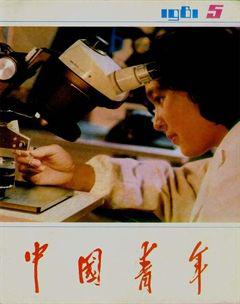从软弱的亚瑟到坚强的“牛虻”
何志云
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的首次出版,是在1897年6月的美国,接着便被译成俄、法、德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195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次在我国翻译出版,始终受到广大中国青年的热烈欢迎。小说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描绘和歌颂了“牛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品质,为了祖国的独立解放事业不惜献出一切的革命激情,以及始终保持着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一切强烈扣动了广大年轻人的心弦,感奋与激励着他们。尤其是小说真实而令人信服地刻划了“牛虻”从一个软弱的青年学生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斗士的过程,又给了广大正在选择人生道路的青年读者以深深的教育和启发。
《牛虻》由三卷和一个结尾组成。第一卷开始的时候,正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当时,意大利被俄、奥、普、英等欧洲列强分割成许多个小公国。奥地利成了意大利实际上的主人。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利用宗教,为奥地利统治者和封建势力效劳。意大利四分五裂,人民在痛苦中煎熬。1831年,以玛志尼为首的青年意大利党人,以“上帝和人民”的名义,呼吁意大利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奥地利侵略者,推翻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一个统一和独立的意大利共和国。这一口号得到了青年学生、爱国知识分子、职员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热烈响应,反抗斗争在全国纷迭而起。但是,几十次武装起义都被反动统治当局镇压下去了,无数青年意大利党人和爱国志士惨遭监禁和杀戮。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比萨神学院的青年学生亚瑟参加了青年意大利党。
亚瑟出身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他是神父蒙泰尼里的私生子,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在家中又倍受兄嫂的冷遇,为人多愁善感、狂热而略带神经质。亚瑟抱着“把我的生命献给意大利,帮助她从奴役和贫困之中解放出来;要把奥地利人驱逐出去,使意大利成为一个除了基督没有帝王的自由共和国”的信念,投身革命,生动表明意大利争取民族解放事业深入人心,也表现了亚瑟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基本思想品质。但是,他把基督作为自由共和国的标志,甚至盼望由蒙泰尼里神父来领导解放和统一意大利的革命事业,又暴露了他的天真、幼稚以及思想上、认识上的严重缺陷。对于一个“以上帝和人民的名义”为行动口号的青年意大利党人来说,这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对于把蒙泰尼里奉如上帝,以宗教为生命归宿来说,亚瑟的这一思想缺陷,则带有浓重的个人原因。冷酷的现实终于无情地教育了亚瑟。当他从卡尔狄神父的告密和蒙泰尼里的欺骗中清醒过来后,他比其他人更看清了教会的本质,认识到“他之所以会遇到这么许多羞辱和愤激以及绝望的痛苦,原来都是为了这些东西——为了这些虚伪而卑鄙的人,和这些不会开口,没有灵魂的神道,”这使他深感羞悔和痛恨,由狂热的宗教信仰和对蒙泰尼里的崇拜奠基的大厦轰然倒塌了,他愤怒地一锤子砸碎了耶稣蒙难像,伪装自杀,流亡国外……
第一卷的结束,表明了亚瑟和宗教的彻底决裂,迈出了向坚强的“牛虻”发展的第一步。需要指出,在他的成长史中,这一步虽然带有关键性,但严格地讲只是一种契机,远不能使他就此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正如“牛虻”自己在回顾往事时所说的,“拿起锤子打碎一些东西似乎是很容易的。”信仰的破灭固然痛苦,但打碎一个偶像,毕竟只需举手一挥。亚瑟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和教会的彻底决裂,更在于他在信仰破灭、以往崇敬的一切变得那么丑恶和令人憎恨之际,并没有去自杀或变得懦怯退缩,也没有就此消沉,甚至以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报复人生,而是依然保持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坚守拯救祖国人民于危难之中的信念,主动而坚毅地去承受一切艰辛和磨难。小说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回叙了亚瑟出走后所经受的非人遭遇。在十多年的南美洲生活中,他在肮脏的妓院洗碗碟,给恶毒的农场主做马夫,在走江湖的杂耍班里当小丑,在斗牛场中干苦役,在海员俱乐部当听差。为了生活,他被人踢过脖子,吐过唾沫,在脚底下踩过,打得遍体鳞伤……支持他坚忍地走着人生之路的是什么呢?就是为意大利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坚持不懈地同反动势力斗争的信念和决心,用他的话说,就是“杀老鼠”。琼玛曾问他:“你为什么没有自杀呢?”他回答:“你想,我的工作怎么办呢?谁能代替我去做呢?”在狱中,针对蒙泰尼里的诱骗,他坚定地表示:“除了跟教士们战斗以外,生命对于我已毫无用处。”在小说结尾时,他在给琼玛的遗书中说:“明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我已经尽了我工作的本分,这次死刑的判决,就是我已经彻底尽职的证明。”坚定的信念作为毕生的精神支柱,鼓舞他忍受苦难生活的折磨,同时也得到了丰富的生活馈赠:他对黑暗、污秽的现实生活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更加接近了人民,锤炼了自己的意志、勇气和毅力。软弱的亚瑟就是这样痛苦地实现了向坚强的“牛虻”的转变。生活的辩证法就是如此。13年后,当亚瑟化名范里斯·列瓦雷士,以“牛虻”为绰号,重返意大利故国的时候,尽管脸上带着长长的伤疤,身体蕴藏着各种病痛,瘸着一条腿,但他已成长为严峻、成熟、坚毅的政治活动家。这时的意大利由于资本主义的新兴和发展,自由资产阶级统一国家的斗争有了加强,封建势力日益不得人心。罗马教会为了缓和与意大利人民的矛盾,在格利哥里主教去世后,不得不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和同情意大利统一运动声誉的枢机主教玛斯太·菲烈提继任教皇,这就是庇护斯九世。庇护斯九世上台后,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如释放政治犯等,一时迷惑了相当多的群众,也在青年意大利党内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牛虻”一方面运用他清醒的头脑和诙谐而犀利的语言,发表了许多激励人民打消幻想,以实际行动拯救祖国和人民的言论和文章。针对人们对庇护斯九世存有幻想,他“把意大利比成一个醉汉,搂住一个扒手的脖子在哭,而那扒手正在掏他的口袋,”这扒手就是庇护斯九世。对新任红衣主教蒙泰尼里,“牛虻”揭露他“即使不是一个流氓,也是流氓掌握中的一个工具”,“非把它一脚踢开不可”。“牛虻”这些一针见血的言论,揭露了反动教会的虚伪面目,唤醒了人们,对那些“已经过分沉醉在宗教的游行,并且拥抱着,高叫着爱啦、和解啦这些热烈的场面里面”的自由主义分子和大部分玛志尼党人,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他又积极投身实际斗争,紧张地筹运军火,组织武装活动。“牛虻”的所作所为,立刻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和咒骂。在不幸被捕入狱后,他坚持斗争,把军事当局的统领菲拉里上校比成一头笨驴,对审判官公开加以嘲讽和揭发,把敌人搞得狼狈不堪。在蒙泰尼里的父子之情的感化面前,他坚定地宣告:“你我之间不能有任何别的关系了,除掉战争、战争,还是战争……只要你还相信你的基督,我们就只能是仇敌。”小说生动地描绘了“牛虻”坚强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和惊人的革命毅力。在旧病复发,难以忍受时,他咬紧牙关,不愿吞服有毒的鸦片;越狱前夕他不幸再次发病,他忍着难言的痛楚,激励自己:“我并没有害病,我没有功夫害病,我得去锉那些铁条,我决不准备害病,”顽强地锯断了狱窗上的铁栏;在刑场上,他临死不惧,慷慨激昂,不断地讽刺刽子手,一次又一次地命令士兵朝自己胸膛开枪……读着这些感人泪下的篇章,“牛虻”这一形象象一座巍峨的巨碑,屹立在我们心中。他那“只有我们才是生命和青春,只有我们才是永恒的春天,只有我们才是未来”的人生警句,久久地回响在我们的耳边。“牛虻”不是无产阶段革命者,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他和宗教势力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强烈感情,无疑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把宗教当成“一切混乱和错误的大根源”,却是不正确的;他的由少数革命家举行无数次的盲目起义或恐怖暗杀的革命途径,也是错误的。在对待琼玛和绮达·莱尼的关系上,他一方面过于冷情地对待琼玛,另一方面,又赤裸裸地玩弄绮达·莱尼,更是我们今天的青年所不足取的。小说没有简单化地去刻划人物形象,而是力求真实,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小说巧妙地安排“牛虻”与蒙泰尼里这样一对人物关系。他们是父子,可又彼此处于敌对的营垒;他们相互深沉地爱恋着,可又各自坚守着信仰。小说通过这一对人物的鲜明对照和强烈冲突,揭示了阶级性是怎样制约了人物的性格,改变了彼此的关系。但也应该看到,小说有个别细节,过分注重对人物心灵的痛苦的描写,因而在一定程度损伤了“牛虻”的完整形象。据说,“牛虻”一词,源出于希腊。希腊神话中,天后赫拉嫉妒天神宙斯偷偷爱上的少女安娥,放出牛虻日夜追逐已化成了牛的安娥,咬得她几乎要发疯。后来,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讲到自己不断针砭社会,以求改革时,把自己喻为牛虻。显然,伏尼契以“牛虻”为小说的书名和主人公的绰号,在意思上有所生发改造,是生动贴切的。正如“牛虻”在遗书末尾写上一首小诗所唱的:“不论我活着,或者我死掉,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虻!”“牛虻”身上洋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我们今天的青年,也将产生很大的鼓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