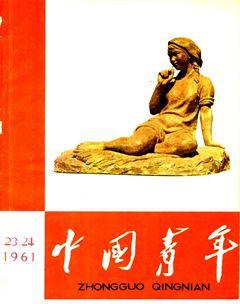在渣滓洞集中营(二)(长篇小说《红颜》选载)
罗广斌 扬益言
(第十二章)
一连几天暴雨,逼退了暑热,渣滓洞后面的山岩间,日夜传来瀑布倾泻的水声……
微风拂进跌窗,带来几声清脆的鸟叫。余新江一早就醒了。这时,他象被微风和鸟语惊动了似的,睁开眼睛,翻身起来,坐在楼板上。退烧以后,他的精神渐渐恢复,刑伤也好了一些,在这清晨略为凉爽的时刻,更显得神智清醒。
天才meng meng 亮,人们都静躺着,还有人微微地打鼾。铁窗边,一个起来最早的人,正悄悄地迎着金色的朝阳,徒手练习着劈刺的战斗动作。一看他那身整齐的军装,余新江便认出他是龙光华。这个新四军战士,始终保持着部队里的生活习惯。余新江喜欢这种性格的人。他不想惊动他,站起来独自向铁窗口走去。铁窗在牢门的对面,窗外有一片荒土,再远一点便是电网高墙,墙外,耸立着一片峭壁悬崖,遮没了视线。抬头望去,碧蓝的天空一丝云彩也没有,预示着一个雨后的大晴天!
转过身来,余新江看见蜷伏着的人丛中那个脑顶光秃的老头子蠕动了一下,这人的面孔好熟悉!可是余新江一直记不起在什么地方曾见过他。余新江还不知道他的姓名,只听到大家都尊敬地称他叫“老大哥”;虽然他病得沉重,很少讲话,但是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这间牢房里最受尊敬的人。
老大哥咳嗽了两声,慢慢撑起上身,依着墙半躺半坐,两只枯瘦的手摆在胸前,缓缓揉弄隐隐作痛的肺腑。余新江注视着他的动作,心里反复搜寻自己的记忆,这个人确实见过,一时却想不出他的姓名和与自己的关系。
铁门哗地一声被推开了,一个特务探头进来,恶狠狠地大声喊叫:
“起来,楼七室放风!”
满屋的人都被惊醒了,特务狞笑着走开。
“他妈的,狗熊!”
“你们骂谁?”被叫作狗熊的特务,突出然又撞进牢门,气势汹汹地问。
龙光华顿时上前两步,站在狗熊面前,盯住他的脸。狗熊发现满屋怒视的目光,慌忙一退,缩出了牢门。
“天不亮就放风,又是狗熊故意作怪!”一个声音对着特务的背影大声说。
刘思扬也在人声中站了起来,定过去提便桶。龙光华一伸手挡住他:“这个给我,你和老丁去找水。”说完,提起便桶就飞快地跨出去了。
“要得嘛。”丁长发含着空烟斗,不慌不忙地招呼刘思扬。“我们两个去找水。”
“咳咳……”老大哥咳嗽几声,喊道:“老丁,万金油还有么?”
丁长发往口袋里摸了摸,找出一个万金油盒子,随手递给余新江,就和提着水罐的刘思扬,一前一后出去了。
牢房里久病的人们,趁着雨后的清晨,都慢慢翻身起来,走出去透一口空气……
余新江把万金油拿到老大哥面前,打开盒子一看,已经空了。他把空盒子,凑近老大哥的鼻孔,让他闻闻残余的万金油气味。这时,他便清楚地看见老大哥左耳根上长着一颗大大的黑痣,痣上还有一撮长毛。这个特征使余新江立刻记超了十多年前的往事——老大哥不正是那位喜欢摸着痣胡讲书的夜校老师?
“你叫余新江?”老大哥看出牢房里只有他们两人时,便慢声细语地问他。
“嗯。”余新江点点头,应了一声。时间隔得太久,那时自己才十二、三岁,他还认得十多年前的学生吗?
“你是哪里人?”老大哥又问。
“武汉。”
“怪不得说话带着湖北口音,到四川很久咯?”
“武汉失守前随汉阳兵工厂搬到重庆的。”余新江有意提起汉阳兵工厂,因为当时的工人夜校办在厂区里。
“哦,是个好地方。龟山、蛇山、黄鹤楼,有机会去观光一下倒不错……”老大哥仿佛暂时忘题了病痛,抬头凝眸,心旷神怡地咏诵起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
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你多象个老师。”余新江有意把“老师”二字说得很重,希望引起对方注意。
“我是教师。1940年被捕以前,在成都当了多年国文教员。进狱以后,大家尊称我老大哥。”
“老大哥!”余新江叫了一声。
老大哥笑了,两只浮肿的眼睛眯在一起,望着余新江。
“老大哥!我也认识一位老师,”余新江有意地说:“他姓夏,十年以前在武汉被捕的。”
“哦——”老大哥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
“夏老师被警察抓走以后,我们夜校的工人子弟,天天想给他报仇,每天晚上掷石头打警察!”余新江放低了声音说道:“到现在我还记得夏老师的象貌。”
“这些事谁也不应忘记。”老大哥的声调也变低了,在余新江耳边说道:“我也记得一个学生,他爸爸是共产党员,二七大罢工时受过伤,我一直惦记着这个学生的成长!”
“老师!”余新江紧抓住他枯瘦的手,低声叫道:“夏老师!”
“我现在不姓夏。”老大哥在他耳边轻轻说道:
“过去的历史,敌人不知道。后来,我在成都又一次被捕,和罗世文、车耀先①同志一道押来押去,息烽、白公馆都关过,没有暴露身份……你以后就叫我老大哥。”
余新江默默地听着,心情十分激动。
“你们一来,我就认出了你。你长得和你爸爸当时一个模样。嗳,你爸爸,老余师傅呢?”
余新江说:“爸爸在三·二三斗争中牺牲了。”
老大哥听余新江简要地讲了他爸爸牺牲的经过以后,沉默了片刻,然后才说:“你爸爸是个好同志,十多年前,我和他曾同在一个支部;现在,你继承了他的事业,我们又聚在一起了。”
“渣滓洞也有党组织?”
“哪里有斗争,哪里就有党!”老大哥简单地回答道:“你和刘思扬被捕的情况,监狱党组织已经了解。党指定你们和龙光华、丁长发编成一个党小组,丁长发同志担任你们的小组长。”
余新江喜出望外地又抓住老大哥的手,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你进来的时候,有什么重要消息?”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件——《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指出革命已经发展到转折点!……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我全都背得出来。”
余新江正想说下去,一阵梆声惊动了他。
“囚车来了。”老大哥听听梆声,便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出去放风、找水、倒便桶的人们,一一回进牢房,铁门咔嚓一声,锁死了。丁长发把从积雨中舀来的半罐浑身黄的水,放在屋角,又回到他惯常倚坐的墙边,咬着空烟斗,默默坐着。
“梆,梆梆,梆梆梆,……”
竹梆声一阵比一阵敲得更紧!
“小余,你听!”刘思扬喊了一声,后边的话还没有说出,就被山谷间暴起的一阵汽车引擎的噪音打断。
梆声刚刚停住,汽车喇叭声又突然响超,从喇叭声中,使人感到那疯狂急驶的汽车正向集中营快速猛冲!余新江立刻翻身起来,挤向牢门口。
“看见了吗?”离签子门较远的人,只能凭着听觉,望着站在前面的背影发问。
“看见了,看见了,……”
“吉普车,后面……”
“后面……还有十轮卡……停了。卡车的帆布篷揭开了……啊,啊!……一副担架!……特务抬下了一副担架……”
“担架!?看清楚了?……”
暂时没有回答。
“听说过么?有个叫成岗的硬汉子……”有个声音在说:“他受了重刑……现在下落不明……”
余新江的心突然巨烈地跳动起来,担架上抬的,该不会是在二处见过的,快要咽气的厂长成岗吧?
黑压压的人影,挤向每间牢门,集中营的人全被惊动了。沉重的皮靴,踏响楼梯,几个挥动手枪的特务,跑上楼来。地坝前面生锈的铁门吱呀吱呀地响着,缓缓地开了……一群持枪特务,押着一副担架,冲过地坝,径直朝楼口抬来了。楼梯附近,传来一障嘈杂声,担架上楼了……
成群特务粗野的脚步,杂乱地踩得楼板吱吱地响。
“当啷……当啷……”繁杂的脚步声中,夹着一种迟钝的金属撞击的音响。余新江踮起脚尖,朝外边看了看,什么也没看见,那牵动人心的金属碰撞的响声,仍然继续着。
(①罗世文同志,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车耀先同志,中共四川军委负责人,同于1941年被捕,先后被办中美合作所息烽、白公馆集中营;于1946年10月10日被害。罗世文同志就义时,遗诗一首:“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那是什么声音?”后边的人禁不住问。
“不知道……”
“也许是脚镣……等一会儿就晓得了。”
“过楼三室了,到楼四室了……”
隔壁的楼八室,传来特务开门的声音。
余新江尽力踮高脚尖,从探望的人头缝里,朝外望着,望着,终于看见了……一床破旧的毯子盖在担架上,毯子底下,蜷曲着一个毫无知觉的躯体……担架从牢门口缓缓抬过,看不见破毯蒙住的面孔,只看到毯子外面的一双鲜血淋漓的赤脚。一副粗大沉重的铁镣,拖在地上,长长的链环在楼板上拖得当啷当啷地响……被铁镣箍破的脚胫,血肉模糊;带脓的血水,一滴一滴地沿着铁链往下流……担架猛烈地摇摆着,向前移动,钉死在浮肿的脚胫上的铁镣,象钢锯似地深锯着那皮开肉绽的,沾满脓血的踝骨……
担架抬进了空无一人的楼七室隔壁的牢房。走廊外边的楼板上,遗留着点点滴滴暗红的血水。
“是谁?”楼下牢房冲打着楼板,传来了焦急的讯问。
脚步声在牢门外响,似乎又有人在走动。龙光华报告了一声:“狗熊抬来了靠背椅,……还有手肘①,绳索。”
“受刑这样重,多么坚强的同志!”余新江心情激荡起伏,不安地挨近签子门向楼八室那边凝望着。
朝霞渐渐消逝,一轮骄阳,又从群峰顶上冉冉升起,散别着暑热。远处,荒草复盖的山顶,近处,密密麻麻的岗亭和电网,象一张木然不动的照片,永嵌在签子门外。
楼八室门口,守着几个特务,刺刀在朝阳中闪着凶光,连放风的时刻,也不让人接近那间囚禁着昏厥中的重伤者的铁门。
一个特务端了半碗稀饭,从楼七室走过,到隔壁楼八室去了。过一阵,又原样端走了……黄昏时分,又一次送饭,但隔壁的战友仍然没有吃喝……
余新江一连几天守候在风门边,急于知道那位战友的消息。可是什么也没有得到,闷热的夜义来了。蚊虫象一团团漆黑的元雾嗡嗡地卷进铁窗……梆声一遍义一遍,从黑夜敲到天明。
天刚破晓,余新江又固执地站在风门边,守候着金色的黎明,守候着隔壁战友的信息,他心里充塞着一种不安的预感:那位血肉模糊的坚强战士,一定是落到敌人手上的党的重要干部。
一只矫健的苍鹰,缓缓地拍击着翅膀,地翔在清晨的碧空,它在这阴森荒凉的山谷间盘旋,盘旋,义陡然冲过岗峦重迭的高峰,飞向远方……从高墙的电网中望着渐渐远逝的雄鹰,余新江抚摸着胸前逐渐平复的刑伤,激跳的心头霍然浮现出对于自由的渴望,思绪随着翱翔的雄鹰,飞向远方:肖师傅、陈松林。无数熟悉的面孔在闪现;外边,火热的斗争,不知又发展成怎样波澜壮阔的形势了?解放战争的前线,不知又推进到哪些省份,哪些城镇?多么希望听到胜利的号角啊,多么希望重新回到工人兄弟战斗的队伍!余新江心情激动,又怀念着老许和成岗,谁知道他们此刻关在什么地方?
黎明的旭日,在期待中,渐渐露出了光芒。“当——啷,当——啷——”音节明朗的响声,在晨曦中,忽然顽强地从风门口传了进来。“当——啷,当——”这声音出现在渣滓洞最宁静的早晨,这钢铁的声音,使楼七室的人都坐了起来,肃静玲听。好象一个勇敢的战士,在弹奏着一只战斗进行曲!
这有节奏的声响,是从囚禁重伤者的楼八室传出的!
清晨,惯常的宁静消失了。虽然室内悄然无声,可是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激情。谁也想象不到,隔壁新来的战友,竟有这样超人的顽强意志:被担架抬进牢房时,已经是奄奄一息;才过了短短的几天,谁能想到他,竟能挺身站起!哪怕拖着满身刑具,哪怕即将到临的更残酷的摧残!哪怕那沉重的铁镣钢锯似的磨锯着皮开肉绽沾满脓血的踝骨!那充溢着胜利信心的脚步,正是对敌人的极度轻蒽!迎着初升的红日,从容不迫地在魔窟中顽强地散步!他象在用铁链碰响的当啷之声,在向每间牢房致意,在慰解着战友们的关切;并且用钢铁的音节磨励着他自己的、每一个人的顽强斗争的意志!
声音愈来愈响亮,愈来愈有力!“当一一啷!当——啷!”铁的链环,重甸甸地敲击在粗糙的楼板上。随着那刚强的脚步移动,不断碰撞出战鼓般的鸣响1这钢一般的响声把看守们也惊动了。一个浓眉大眼、面目可憎的特务,从办公室撞了出来,那只鹰爪似的手,紧抓住腰皮带上的枪柄。
“这家伙是谁?”刘思扬挤过来,靠在余新江肓头,轻声问。
“特务看守长,猫头鹰。”龙光华代为回答。
“两手血腥的刽子手……三百多人!”丁长发补充了一句。
余新江看出,那个叫猫头鹰的刽子手,两眼正盯住楼上第八号牢房,一步步跨进地坝里来。
“猫头鹰想干涉隔壁战友散步!”
(①手肘是一种把双手固定在胸前的铁制刑具。)
“听!这就是答复……”
靠近牢门的人们,听到在铁链叮当声中,出现了轻轻的歌声。渐渐地,歌声变得昂扬激越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
歌声,象一阵晌亮的战鼓,击破禁锢世界的层层密云!歌声,象一片冲锋的号角,唤起人们战斗的激情!这声音呵——象远征归来的壮士,用胜利的微笑,朗声欢呼战友亲切的姓名,更象坚贞的人民之子,在敌人的绞刑架下,宜扬真理必然战胜!
高昂的歌声,战鼓,号角,象春雷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粉碎那旧世界的锁链……”人们应声唱着。“奴隶们起来起来!……”更多的人放开喉咙唱了起来,楼上楼下汇成一片,四面八方,升起了雄壮庄严的歌声。
“不准唱歌!”猫头鹰嚎叫了一声,成群特务也跟着嚎叫。
“谁再唱,马上枪毙!”手在枪上一拍。
可是,那春雷一般的,万众一心的声浪,一旦升起,怎会被这嗡嗡的蚊蝇的阻扰而停歇?潮水般的声浪在不知姓名的,重伤的战友激越的歌声鼓舞下,变得更加高昂豪迈,震撼着魔窟附近的山岗!
猫头鹰脸色铁青,突然冲着楼八室狂喊:
“不许你唱!住口!许云峰!”
“许云峰?”突然有人惊问。
“老许!”对面女牢里,飞出一声尖锐的叫唤。
“老许!老许!”余新江猛然把头从风门口伸出去,凝望着楼八室。老许——他就关在自己隔壁!余新江满怀激动,张大了嘴巴,迎着老许坚强无畏的歌声纵情高唱: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许元峰站在铁门边,望着天边的繁星。夜已深了,他一点也没有睡意。除了时起时停的竹梆声,间间牢房的战友们,都已经进入梦乡。黄昏时又一次爆发的歌声,还在他的耳边回响。虽然这歌声早就停歇了,但他总感到具有无穷力量的声音,还久久地在夜
空里荡漾: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勇敢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
昏黄的狱灯,照见许云峰目光闪闪的脸,他从晕厥中醒来以后,就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力量。这力量正团结着集中营里的战友。虽然这个力量是看不见的,然而确实存在。从那些病弱的战友的脸上,从毫无怨言地承受任何考验的斑斑伤痕中,从显示每一个人的意志与决心的合唱里,都可以感触到这无形的、但是百折不挠的东西。
这,和他被捕以前,市委反复地策划着和这座集中营建立联系时的估计完全一样!
许云峰希望迅速找到党的组织。他确信,这是一定能够做到的。因为,这里的党组织必然和他的想法一样,也急于与他建立联系!他也知道,敌人把他单独囚禁,正是想把他和自己的战友们隔离开来,以免他在敌人疯狂迫害下和艰苦斗争的战友建立联系,增强这里的战斗力量。但是,这有什么用呢?他才刚刚开始行动,同志们不是就发现了他吗?战友们的心,是隔离不了的;战友们的歌声和活动,早已超越了层层牢墙的封闭!
许云峰提起脚上的铁链,转身离开牢门,慢慢回向那铺着一张破旧带血的毯子的简陋地铺。他不愿在静夜里,再让铁链当啷的响声,惊醒入睡的人们。在这单身牢房里,他久久地怀想着自己的战友,怀念着党,不能入睡。他确信,地下党不会因为这次挫折而中止斗争,但是,党一定会总结经验教训,改变某种斗争策略,今后对敌人的斗争将更准更狠,但也将是更加隐蔽和安全的,想到这些,他是满怀信心的。他也没有因为自己再不能参加外面的斗争而痛苦,因为他现在又负担了新的斗争责任:千方百计保护党的组织,决不能让敌人嗅出老李,老石和市委的其他同志!同时,他得在新的环境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找到这里的党组织,团结群众,加强斗争,粉碎敌人的迫害、分化等等阴谋。
“梆!梆!……”
隐约听见一阵嘈杂的人声,许云峰抬起头来,朝铁门外望着。昏暗的狱灯,象鬼火一样,四周全是黑黝黝的。
巡夜的特务,踏着重甸甸的步伐,在牢门外走来走去……朦胧中,一声尖锐的啼声,惊醒了他,接着
又是几声啼叫。许云峰渐渐听清楚了,那是从女牢传出来的一阵阵乳婴的啼哭!
“一个新的生命,降生在战斗的环境里了!”许云峰从婴儿的啼声中,感到生命的脉搏在跳跃。他翻身起来,提着脚上的铁链,走到牢门口,透过夜色,向下望着,心里充满了喜悦。
隔壁牢房的人,也被婴儿的声音惊动,楼上楼下,人声闹嚷起来。风门边,传来一阵阵激情的低语:
“男孩还是女孩?问问楼下!”
“女室回答了,是一朵花!”
眼前,彷佛晃动着一个甜甜的婴孩的笑脸。“给她取个最光采的名字!”许云峰心里愉快地想。他对这初生婴儿的前途,就象对这集中营里战友们的前途一样,满怀希望与信心。
……
天边出现了一抹红霞。许云峰迎着曙光,衷心欢畅地凝望着女牢那边,虽然他此刻还看不见那幼小的生命。
许云峰回过头,目光扫视了一下空空的牢房,便提着脚镣走向简陋的地铺,揭起那床带血的破布毯,叉回到牢门边,他把布毯从风洞里扔下楼去,带着命令的语气,对着守在地坝对面的特务看守员说道:“把毯子送给女牢,给孩子撕几块尿布。”
说完,许云峰抬起头来,看见最先出去放风的战友们,也正在女牢门口放自愿送去的衣物。那些在地坝中散步的人们,脸上闪耀着激动而幸福的喜悦!楼七室出去放风了。许云峰忽然看见余新江的背影:他手里拿着水罐,急急地走过地坝,理直绕过这一长列牢房的尽头,转到牢房后面去了。
许云峰昨天就注意到,已经不止一次,有人到牢房后边寻找水源。人们似乎对牢房背面那片荒坡的每寸土地都仔细研究过,最后还是看中了一处地方,离他的铁窗不远。那里的土地比较潮湿,地面复盖着一层青苔,雨后,渍起了一些浅浅的泥水,浮着一层肮脏薄膜的水面不断鼓着水泡,孑承和沙虫很快地长满了。从那里挖下去,下面很可能找到山泉。
大概,人们也都是这样设想的。昨天下午放风的时候,就有人在那里挖过土。轮到放风的人,带镣的战友,跛腿的女同志……都轮流到那里去了。没有任何工具,人们就用指尖去掏挖泥石,艰难地但是一心一意地扩大着水坑。使他难以忘怀的是,一个断了一只腿的女战友,不顾指尖滴着鲜血,边挖,还低声唱着一首歌。娓娓的低音,激昂高壮的感情,在他心里引起了深深的共鸣,使他清楚地记住了那充满战斗激情的歌词:
……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颠倒的乾坤扭转,
我们要把不合理的世界打翻!
今天,我们坐牢了,
坐牢又有什么稀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到昨天黄昏时,坑渐渐挖成了,只是还没有水。也许,过一夜,或者,再挖深一点,会有地下水的。如果有了一潭清泉,渣滓洞几百个战友,就不会再为干渴所苦恼了。不过,许云峰感到,敌人决不会听任这种行动,因为这将直接破坏他们故意断水的迫害活动!而且,找寻水源也还是一种简单的反抗办法。但是,挖掘水坑也还是必要的,这能有力地团结战友,锻炼斗志,鼓舞信心……
许云峰离开了铁门,定到牢房后面的铁窗边,把头伸在小窗的铁柱间,向外探望。果然,正象他昨夜想象的那样,山泉巳浸满了土坑,一池清水,映着碧天,闪勃微微的涟漪。
余新江正蹲在水坑边出神,他把双手插进清泉,捧起水来喝了一口,然后他把水罐伸进水里舀了一罐。许云峰勃了一下脚镣,发出一声当啷的音响,余新江回过头来,目光正和许云峰的融合在一起!
“老许!”余新江叫了一声:“我住在你隔壁!”许云峰微微点头。
“你要保重!”余新江仰望着铁窗,一动不动地站着。
许云峰一笑,目光闪勃了一下,权当回答。余新江留连着,放风的时间过完了,还不肯走。直到许云峰用目光叫他离开,才怏怏地走了。
这时,女室也来人舀水。许云峰又看见那个头发上扎着鲜红发结的姑娘,轻盈地走到水边。昨天傍晚,挖土的时候,她就伴着断腿的女战友出现过了。她用一只漱口缸,舀了一缸水。迟疑了片刻,又蹲下身子,把缸里的水,往水潭中倒出一些。许云峰看出,这位姑娘,不愿把水舀得太多,要留给更多的战友取用。
那姑娘站起来了,伸手掠了掠头上的一绺乱发,目光一闪,发现了跌窗后边的许云峰。她尊敬地轻轻把头一点,微笑着向许云峰表示问好。许云峰也点头微笑,望着她轻盈的身影离开。许元峰不认识孙明霞,但他完全了解这年轻战友的坚强。
转角处,忽然跑来一个全身灰布军装的人,差点把姑娘手中的水缸撞翻了。那是龙光华,他抱歉地点点头,便大踏步走向水潭。许云峰看他戴着褪色的军帽,有着一双火一样热情豪爽的眼睛,衣袖高高地卷起,露出两只黝黑的手臂,他大步走到潭边,毫不犹
豫地用水罐满满舀了一罐,就埋着头跑了……
不到一分钟,龙光华又出现在水坑边,他又满满地舀了一罐。
他又来了,又去舀水……
许云峰不知道这位战士为什么这样匆促地舀水,但从他正直的目光可以看出,他舀水决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且许云峰完全相信,人民的队伍里培养出来的子弟兵,只能是为着高尚的目的,才接速地取走那么多的水。
“你躲在这里?楼七室早就收风了!”
敌人的干涉出现了,尖锐的斗争就在许云峰眼前展开……
“唉!你在这里挖坑?”被唤做狗熊的特务,把几团污呢,踢进了水坑。
“你干什么?”龙光华象在保卫人民的利益,挺身上前,质问特务:“天气热,你们故意断水!这个坑是我们挖的,不准破坏!”说完,战士瞪了特务一眼,又蹲下身去,舀了一罐清水。
“把水送到哪里去?”
“你管不着。我给缺水的牢房送水!”狗熊劈手夺下水罐,丢在水坑中。
“把水罐捡起来!”龙光华愤怒地命令。
“捡起来?”特务走到他面前,想要动手。
“你来!”龙光华握着拳头,迎了上去。
特务退后一步,踩了一脚污泥,突然亮出手枪,恶狠狠地叫着:
“龙光华,你要造反?走,到办公室去!”
“走!”龙光华一挺身,昂然迈开脚步。
一个暗影倏地掠过许云峰的心头:他不能不为龙光华的遭遇感到耽心。而且,他已看出,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斗争的尖锐的暴发!斗争既已暴发,就再不能犹豫,只有坚持到底,才能胜利,不管为了胜利要付出多大代价!但他却无法把自己想到的一切,告诉给自己的战友们……
“不准打人!不准打人!”
“不准特务行凶!”
一片呐喊,从四面八方传来。许云峰关切地转过身来,走向人声喧嚷的牢门,站在风门口,他看见一个身体肥硕的特务,从办公室踱了出来。这个特务正是渣滓洞集中营的特务头子——被大家称为猩猩的所长。这特务,长着人的面孔,穿戴着人的衣冠,讲着人话,摹仿人的动作,象人,却没有人的心肝,而是一头类人的刁诈的动物,所以都叫他猩猩。
“龙光华白昼挖墙,图谋暴动,并且公开殴打看守人员,这还了得!”猩猩拖长了声音,安图制服每间牢房的呐喊。
敌人在公开挑战,而日造谣污蔑!
女牢中,头上扎着鲜红发结的姑娘,突然从牢门冲出来,望着楼上楼下所有的牢房,驳斥猩猩:
“这完全是假话!我们亲眼看见,龙光华在后面舀水,特务故意撞去行凶!”
“孙明霞,你亲眼看见的?!”猩猩阴险的目光,象要把这姑娘一口吃掉!
“我们都看见的!”几间女窒的战友,突然冲出牢房,在屋檐下站成一排,齐声说道:“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面对着女室的对证,猩猩发出一声冷笑。
“你们看见了什么?龙光华已经全部招认了!”
正在这时,满身鲜血的龙光华,突然从铁门边冲进地蹋,摆脱了特务的追赶。几分钟的时间里,龙光华已经遍体鳞伤,几乎认不出他的面目。龙光华摇摇摆摆走到地坝当中,高举手臂挥动他的军帽:
“特务破坏水——”
“坑”字没出口,龙光华侧了侧身体,摇摇晃晃地跌倒在地上,鲜血从他嘴里不断涌流……
女室的战友,眼里喷出怒火,她们扑向前去,救护血泊中的战友。
“你们看见了吧?”猩猩狞笑着,“马上把水坑填平!凡是挖过水坑的,出来自首1”
“不准特务行凶!”几百人的声音,象决堤的洪水,象爆发的地雷!“谁敢填平水坑?!”接着又是一声炸雷:“谁敢填平水坑?!”猩猩连速后退,阴险的目光,打量着间间牢房里愤怒的人,他突然直起颈项怪声嚎叫:
“啊!你们要暴动?……把机枪给我架上!”猩猩凶横的脸上露出冷笑,向着牢房逼视着。”谁敢暴动?谁在这里指挥?嗯?怎么没有人说话?有勇气的就站出来!站出来呀!”
几个特务气势汹汹地提着重镣,四处张望着,为阴险毒辣的猩猩助威。突然,“当啷”一声,楼上一个牢房传来的金属碰响铁门的声音,使猩猩猛然一惊。紧接着,一个洪亮的声音出现了:
“住口!停止你们这一切罪恶活动!”猩腥慌忙一退,他不知道是谁,敢于蔑视他的权威,用这种命令语气挑战!定睛看时,他不由得周身猛烈一颤。楼八窒的牢门,出现了一个人影。“许元峰?”他惊惶失措地朝后便退,禁不住怪叫出声:“你、你、你要干什么?”
这时,神色自若的许云峰,已经倔立在牢门边,元所畏惧地逼视着连连后退的特务。元数的目光立刻支持着他的行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