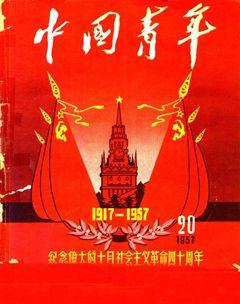列宁的中国卫士李富清
李兴沛
离开了亲爱的家乡
1898年,李富清诞生在沈阳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里。父亲是个木匠,妈妈是个瞎子。李富清十二岁就替财主家放猪;十三岁又替另一个财主放牛;十六岁去沈阳一家饭馆学手艺。这年,家里的人口增加到八个,光靠父亲一个人做工维持生活,当然非常困难。家里三天两头掀不开锅,娃娃们饿得哇哇叫,李富清在馆子里每个月才能挣一块钱,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且受骂挨打成了家常便饭。李富清年纪虽小,生活的折磨,已经使他体会了一般少年所体会不到的人生滋味。他不能看着家庭的重担把父亲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要替父亲分担一部分负担,因此在第二年他就和表哥一道上千金寨(即现在的抚顺)去替资本家装煤事,想赚些钱接济家庭。谁知这个工作也比当学徒强不了多少,仍然不能减轻父亲的担子。他多么希望有一个能养活半家人的“好”差使啊!
1916年4月间,煤矿工人中忽然流传着俄国人在沈阳招工人的消息,有很多工人已经报了名,并且领到了二百个卢布。李富清立刻跑回家去和父母商量,他决定要去报名,父母是同意了,但祖母不同意,她悲痛地说:“两百个卢布就把个孩子卖掉吗?我不能让他去!”
李富清说:“奶奶,只有两年就回来了啊!那怕什么?再说,又不是我一个人去,表哥也去哩。”
经过父亲以及亲戚们的一再解释,祖母才勉强答应了。李富清就和姑表哥陈智荣、姨表哥吴志华一道到沈阳西关老爷庙去报了名。检查的结果三个人都合格,各找了个铺保,领得了二百卢布交给家里。就这样,刚满十八岁的李富清,坐在上了锁的俄国闷罐车里,离开了亲爱的家庭,离开了生长的国土,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
沙皇是个国际大骗子
火车,拉着三千名中国苦力往西去,走呀!走呀!好像铁路没有个尽头。停停又走走,走走又停停,火车竟在铁路上转了二十多天,谁也不知道离家有多远,谁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有人感到奇怪,去问领队的翻译,翻译说:“俄国大着啦!又不叫你们跑腿,慌什么?”
闷罐车里黑黝黝的,除了吃饭、屙屎、拉尿开一开车门以外,老是锁着的;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还有很多苦力做着美丽的梦,他们把将要去到的地方,想像成解救自己一家贫困的乐园。
火车最后停下了。带队兼翻译(实际上就是把头)说了一声:“到了!下车吧!”大家下事一看,哪里有什么工厂,除了一些木头房子以外,连人家都没有,眼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森林。
有人去问翻译:“工厂在哪里?”
翻译说:“工厂在林子里!”
大家感到很奇怪,设在林子里,这是个什么工厂呢?更奇怪的是翻译不叫大家走,而是叫大家住在那些生了菌子的木屋里。
翻译说:“先给工厂伐树、修路。路修通了,工厂就到了。”中国苦力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开始给“工厂”伐木、修路。晚上,木屋子不够住,有的睡帐篷,有的只好睡在露天下。吃的是黑面馍或土豆。
四、五天以后,忽然从西方来了许多沙皇的军队,他们一到,立刻逼着中国人挖战壕。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国苦力开始不安起来。
原来,这是一个大骗局。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欧洲的时候,俄国与奥、德作战方酣,沙皇为了搜
罗炮灰,就与中国东北的军阀勾结起来,玩弄了这个“招工”的把戏。
现在,中国苦力挖战壕的地点就在俄国与奥匈帝国的边境。沙皇的军队非常凶狠;中国苦力稍有怠慢,立刻就会遭到皮鞭、枪托的毒打,很多人想逃跑回家,但往哪里逃呀?连中国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哩!又何况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口袋里一个铜子也没有。
有个苦力累病了,躺在床上,几天不能工作,沙皇军官便说他有意怠工,硬逼着他挖战壕;这个苦力实在受不了,就在这天晚上自己吊死了。还有个姓王的也因为不愿再受这个罪,就故意把自己手指斩断了。这类令人心酸的事情,每天都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里,劳动人民没有祖国,这一批中国苦力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有谁来替他们作主呢?有谁来保护他们呢?
没有多久,忽然传来了炮声,中国苦力更慌乱了。这时有个绰号叫吴二虎的中国苦力组织大家罢工,很快就得到全体的响应。吴二虎和其他四个代表去向总领队说理,要求把大家送回中国,但结果这五个代表都被抓起来了;直到两天以后,德军包围了这个地区,中国苦力和沙皇军队一同成了德军的俘虏,这五个代表才回到大伙一块来。
德军把中国苦力赶进了集中营,中国苦力由十八层地狱掉到十九层地狱。德军对他们比沙皇军队更凶狠,每天发的食粮,只有一块茶杯那么大的黑面包,咬起来沙子扎牙,但却强迫他们白天黑夜地修监狱、修道路。德国人是从不吝啬皮鞭、马靴和刺刀的;多少人被打得死去活来,多少人被过度的劳动拖死;每天都得用卡车向外运死尸。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带给人类的“恩惠”!
星星之火
1917年春季,绕幸活着的中国苦力在受尽被人奴役的痛苦以后,谁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德军把他们释放了。他们和俄国战俘们一同返回俄国,但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却是饥饿和死亡。他们一踏上俄国领土,就谁也不来管他们了。这时的俄国由于连年战争的破坏,正处在极端贫困、异常混乱的状态,当时的政府一方面忙于对德战争,一方面要镇压革命运动,它自身难保,哪里还有力量来照顾这批被释放的俘虏呢?
正当这群饥饿的人在乌克兰的草原上到处流浪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团星星之火。有一天,有个叫伊凡诺夫的俄国人唤住了他们:
“同志们,我们要活命,就只有组织起来,去打沙皇军。沙皇军仓库里有麦子、有衣服。要不然,就只有像现在这样毫无目的地瞎走,就只有饿死。”
李富清这时已能听懂几句俄国话了,他认为这个俄国人说得很对,于是他就和陈智荣、吴志华商量,三个人都决定跟着伊凡诺夫走。当时,共有一百七、八十个中国人,还有三百左右的俄国人组成了一支队伍,伊凡诺夫就成了这一队的队长。他们靠着从战场上拾来的几支枪,先围攻了一个小镇上的警察局,夺得三十多支旧枪,以后又打垮一连沙皇罩,夺得了近百支枪。这样,队伍就装备起来了。
在游击队里,中国人和俄国人相处得非常友爱。队上得到了白面,总是先分给中国人吃,好的衣服也先给中国人穿,能够住上房子的时候,也总让中国人住好房子。最初,中国同志还没有察觉这种伟大的友爱精神,以后次数一多;大家就懂得了;于是中国同志在得到白面以后,也做成面包送给俄国同志,有的还帮助俄国同志缝补衣服。虽然国籍不同,语言不同,但彼此之间团结得真像是一家人。
李富清后来渐渐地明白,这支队伍是属于布尔什维克的。这就是最初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带成立的红军游击队。星星之火,终于点燃了草原和森林。
三月间,队伍打到了明斯克附近。有一天,游击队决定去破坏居卡兹车站。下午四点多钟,天色慢慢暗下来,游击队就由森林里出发。
当游击队走出森林的时候,天空已闪烁着星星,森林外的田野像死样的沉静。队伍在黑夜里悄悄地行进。大约八时左右,到达了离乌卡兹事站约三公里的小树林
里。队长布置任务了。
事先,游击队就得到情报,知道这个车站上有两百多白军,其中五十多个驻在离车站五百公尺的地方守护水塔。另外也知道今晚九时,敌人有一列弹药车开往前线。
当时队长决定派一百人去打弹药车,派八十人去攻水塔,其余的人攻车站。
李富清被分配在夺强药车的一百人中间。他们到了车站前面两公里的地方,小队长就命令李富清等八个同志去撬铁轨,其余的人去选择有利地形,并掩护撬铁轨的同志。李富清等八人接受了任务,就扛着撬棍等工具摸上铁道。他们中间有两个是最近参加游击队的铁路工人,所以干起这个活来非常熟悉,不大一会工夫,一根铁轨就撬掉了。他们就伏在地坎子后面等待列车的到来。
初春的夜晚还是很寒冷的,握着枪的手冻得发木。等待,这是使人感到时间过得最慢的时候;但由于这是等待胜利,所以战士们的心情特别兴奋。仿佛过了很久很久,隆隆的列窜声终于由远方传来了,声音越来越大,战士们的心也越跳越快。当那火事到了拔轨处,只听得轰的一声,车头栽倒在路基下面了,后面的车箱紧跟着哗啦啦一阵子挤出轨外,有几节车箱还被抬到空中才掉下来。车上的弹药爆炸了,在火光中,只见敌人抱头鼠窜,车辆上翻下来的战局惊得在敌人中间乱冲乱踏。
就在这个时候,游击队向敌人开火了,那些侥幸没有跌死压死的敌人,大部分却难逃这一阵子弹。不到二十分钟,这里就结束了战斗。
这时,车站方面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李富清他们就赶紧转移阵地,去支援进攻水塔的同志。不到一个钟头,车站被游击队占领了。游击队缴获了一些枪支和弹药,把水塔和车站破坏以后,第二天就撤退到另一个森林里去了。
游击队就是这样英勇机智地打击着敌人。
但是,不幸得很,有天晚上去攻打一个火车站的时候,队长伊凡诺夫牺牲了。同志们深深地怀念着这位引导大家摆脱饥饿和死亡的同志。但由于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队伍并没有因此涣散;相反的,队伍更加壮大了。那时候,农村里有大批饥饿的农民,城市里有数不尽的失业工人,当游击队经过他们身旁的时候,就像吸跌石挨近跌末一样,把他们纷纷吸引到这支队伍里来了。到秋天的时候,中国战士已发展到五、六百人,单独成立了一个支队,支队长就是吴二虎。
一次意外的收获
有一次,游击队在别尔哥罗德附近攻下了一个千来户人家的小城。纵队司令部就驻在小城里,三个支队分驻在小城周围的村庄里,彼此相距十至十五公里。中国支队驻在城西的小庄上。
一天傍晚,纵队的通讯员骑着快马飞奔而来,到了团部(当时中国游击队员习惯地称支队部为团部,称吴二虎为团长),交给吴团长一份通知,通讯员就飞马走了。
吴二虎当时不识俄文,恰巧翻译在昨天作战的时候受伤住院去了。团里有个老陈,过去曾在哈尔滨俄国洋行里当过工友,能识几个俄国字,团长就找了他充当临时翻译。老陈拿了那份通知看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大概是叫咱们明天上午十点钟去领给养。
吴二虎一听说是领给养,就把通知放在一边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吴二虎就命令一区队去纵队部领给养。李富清就在一区队当组长。他们五十多人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问小城进发。
这条河床西边是个树林子,东边是一人多高的岸坡,岸坡上向东去,就是一马平川的田野,田野里有公路,公路以东还有一条铁路。
大约走了七、八公里,李富清他们发现公路上有一大队骑兵由纵队部驻扎的小成向西南方向前进,可是穿的服装不像是自己人;区队长就命令部队进入南边的树林子准备战斗,并派李富清等六人前去侦察。
李富清等爬上岸坡,借着麦田的掩护,向着公路潜行;到离公路大约三、四百公尺的地方,看见那队骑兵的帽沿下,仿佛有一道白边,当时他们还不能断定这是谁的部队;等了一会,发现了一面旗子,旗子是上半边白,下半边黑,这才肯定是敌人。李富清把探得的情况报告区队长,区队是一面叫同志们监视敌人,一面叫人去向团长报告。
一个多钟头以后,吴团长带着队伍来了。公路上敌人的骑兵已经定完了,现在走着的是步兵。据估计,敌军大约有五、六千人。
同志们现在都知道小城已经落在敌人手中了。纵队部怎么样了呢?是撤走了呢还是被敌人包国了呢?大家都非常担心。吴二虎派去联络其他两个支队的人回来说,两个支队都撤走了,不知上哪里去了。这一来,大家都像掉在闷葫芦里,不知该怎么办。
吴团长略微考虑了一下,说:“不管它,先打了再说!”他就命令部队潜伏在树林子里严密注意敌人。
下午三点钟左右,公路上的敌人过完了;当太阳沉落在地平线后面的时候,部队就分北、西、南三路向小城发动了进攻。
李富清随着一区队由东北攻进城去。城里只有五、六百敌军,游击队的突然袭击使得敌人大为慌乱,只打了半个钟头,由北边进攻的游击队已冲进五、六条街了。
一区队南边从一个小巷摸进城去,便直向城中心插
去;快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个楼上有人向北边街上射击,区队长立刻命令李富清、陈智荣等十几个战士从小楼的后院攻进去。
这十几个战士翻过了一人多高的围墙,到了小楼的后院;敌人只顾对付前面的游击队,所以没有发觉后面进来了人。李富清等十几个人就挨着院里的树木迅速地冲向楼下。
这座楼只有两 层,楼前一排房间临着大街,楼后一排房间靠着后院;楼下的房子黑黑的,好像没有人,楼上的窗户里还有灯光。这座房子的楼梯设在楼后的屋檐下,上了楼梯是个长廊,长廊一边临空,一边靠着二楼的门窗。李富清吩咐四、五个同志在楼下掩护,他自己带着七、八个同志上了楼梯。他们冲到窗口,把枪伸进窗户,大喊:“举起手来!”
室内是敌人的几个下级军官,他们正在灯下慌乱地收拾文件,看样子,正准备逃走;游击队的突然出现吓得他们手一撤,文件落了一地,身子像筛糠似地抖动起来,双手战战兢兢地举到头上去。
临街的那间房子里还有枪声,陈智荣和另外两个同志穿过与长廊成丁字形的甬道,到了前楼,他们哗啦一下子踢开了房门;房子里黑洞洞的,只是窗外的天空隐隐约约地衬出三个黑影。当门被猛然踢开的时候,这三个黑影迅速地闪开了,突然啪的一声,从黑角落里射来一枪;陈智荣感到腿上吃了一家伙,他知道自己受伤了,便依着墙壁,端起连珠枪朝房里齐腰横扫了一梭子,只听得那几个家伙呜哩哇啦地叫喊起来,一会儿就没有声音了。
有个游击队员大概是从下级军官那里搜来了一支手电,到前楼一照,只见一个士兵模样的白军倒在楼板上快断气了,另一个士兵模样的家伙倒在地上,双手举在头上表示投降,还有个家伙却不见了。游击队员用手电往床底下一照,只见一个肩上戴着金板板的家伙,像条癞皮狗似的缩成一团,脸上流露出绝望和恐惧的神色。游击队员们把他拖了出来,他低着头,木人似地站着,头向前垂着,似乎有点害羞;从他的服装和举动看来,他大概是个大官,那两个士兵大概是他的卫士。
城里的残敌刚肃清不久,白天从公路上过去的敌人听说后路被人截断,就立刻溃退下来。吴团长又马上下令阻击;敌人因为不知道游击队有多少人,只得从东南面退去了。
原来纵队部的通知是要中国支队在头一天晚上撤退,但是那个临时翻译把通知看错了,才发生了这次误会。这天纵队还没撤到预定地点,忽然听说敌人向后撤退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又听说是因为敌人的后方被人掐住了才撤退的,于是就发动了一个反击;敌人腹背受攻,只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走了。但这时候纵队部还不知道是哪一部分游击队干的这件漂亮事。直到第二天天微亮时,城里的中国支队和城外的纵队会师以后,才把这个问题闹清楚。
这次战斗,打死打伤了八百多白匪军,缴获了机枪二十多挺;那个在小楼上被俘的戴金板板的军官,就是敌人的司令。从此以后,中国支队就出了名;敌人一听中国人来了就吓得胆战心惊,因此也特别恨中国人。
事后,纵队还派了专人来慰问,并给每个中国战士发了一条毛巾。
这次误会,却造成了一场意外的收获。
我们要打得更坚决
1918年夏季,游击队改编为红军了。有一天下午一点钟,红军由罗汉斯克附近下火车,去攻打斯组尼目里哥夫克;他们走了两小时,就发现前面有敌人的骑兵侦察,于是缸军就摆开了阵线,准备战斗。没多久,敌人的哥萨克骑兵冲过来了,开始了激烈的战斗。打了两个多小时,双方死伤都很重,到了天快黑的时候,由于有一部分由旧军官指挥的队伍的叛变,红军被哥萨克包围住了。当时司令员就下令撤退,为了照顾中国部队,司令部决定由苏联骑兵在前打冲锋,中国部队在中间,后面由苏联步兵阻击和掩护。当天晚上,部队撤退到罗汉斯克附近,但是仍有三分之一的同志没有撤出来,陷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了;吴二虎、陈智荣、吴志华都没有冲出来。
三天以后,红军的援军开到了,于是便向哥萨克展开反击。红军节节胜利,一直打到了斯坦尼目里哥夫克。
红军在进军途中,看见路边、田里、村子里,到处是被敌人惨杀的红军尸体;野狗在啃啮人的肢体,乌鸦在啄食人的肌肤,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沿途的树上和木椿上吊满了中国战士的尸体,有的耳朵被割掉了,有的眼睛被挖掉了,有的舌头被割去了,有的肚子被戮穿了,肠子拖在地下,有的手心和脚踝上都被粗铁钉钉在木椿上。当时天气非常炎热,苍蝇成群地在尸体上嗡嗡乱飞……在这些尸首旁边,大部分都写着标语。翻译同志说,标语的内容大都是:“这是红军的下场!”“布尔什维克完蛋了!”
中国战士们看到这些,又气愤,又哀伤。部队一边前进,一边收尸,一路上共收了二百多具中国战士的尸体。但是李富清却没有找到他两个表哥的尸体,心里非常难过;他想到将来回去怎样对姑父和姨父交代呢?他又想到自己和表哥们一同离开亲爱的家乡,一同坐闷罐火车,一同在皮鞭的抽打下伐木,挖战壕,一同在俘虏营里吃过苦,一同打过游击,抓过敌人,出生入死,从来没有分离过,现在他们却落得如此惨死,连尸首都找不到……他想到这些,不由得痛哭失声。
红军到了斯坦尼目里哥夫克车站不久,就有几个农
村妇女跑来告诉中国战士们说,在车站厕所后面的高粱地里,还有一个中国伤兵,他在那里已经躺了三天了。
李富清和其他十几个中国战士一听到这消息,立刻就去找寻。但当他们走到他跟前的时候,都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个战士满身满脸都是血污,附近的地上还有一大滩干了的血,他的左眼珠吊在眼眶外面,右耳没有了,左腿从膝盖以下已全部溃烂,伤口里还有蛆虫在来回蠕动。他,已经被折磨得完全不成人形了。当他看到同志们来了,就失声大哭起来,一会儿就晕过去了。在场的人看到这种情景,没有一个不流泪的。他们小心地把他抬上担架,立刻送到医院去了。
据那几个农妇说,她们看见哥萨克抓来了十几个中国战士,就连夜审讯。这位战士也是其中之一。大概因为审不出什么名堂来,就用刀子把他的左眼挖了出来,并把他拖到田野里去枪毙;哥萨克打了一枪,他就倒下去不动弹了,但等哥萨克走了以后,他却醒过来了。原来那一枪只把他那只右耳打掉了,他的左腿则是在作战时受伤的。后来她们把他藏在高梁地里,每天偷偷地给他送些吃的,他才没有饿死。
那几个妇女还说:哥萨克在临走的时候叫她们转告中国人,如果中国人不离开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那么被他们抓着的话,就只有这种下场。
中国战士们听了这些话,没有一个人不咬牙切齿的!他们不但不惧怕,而且都表示了自己的决心:“我们决不离开红军,我们要打得更坚决,为亲人报仇!”
跟列宁当卫士
1919年年初,李富清和其他二百多人(其中有七十多个中国同志),得到了无产阶级战士最大的荣幸:他们被调往彼得格勒担任列宁的卫士。在彼得格勒,李富清同志朝夕见到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列宁,并朝夕保卫着他。
李富清当时是卫士队的小级长,每次四个人,李富清就是带班的。他们站岗的地点就在列宁的办公室外面台阶下,列宁出出进进,都从他们身边经过,有时列宁还停下来和他们谈话。李富清当时还很年轻,才二十岁哩!
有一次,天气很冷,树上堆满了雪花,在列宁的办公室的台阶下,站着四个精神饱满的警卫战士。他们鼻孔呼出来的白气,被冷风一吹,都在粗呢大衣的衣领上凝成了白霜。这时,列宁从外面回来。列宁穿着一件白皮领的黑色皮短大衣,带着黑皮帽,神采突突地走来,李富清用响亮的嗓子喊了敬礼。列宁点着头,微笑着说:
“不用啦,不用啦,天气这么冷,还站在风里,快!快!快站到过道火墙附近去,里面暖和一些呀!”
四个卫士都不肯进去,列宁一再叫,他们中站到过道里去了。
又有一次,列宁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换换空气,碰到李富清和几个中国战士,就和他们聊天。列宁问他们:
“生活过得惯吗?吃得饱吗?住的怎么样?”
李富清说:“生活过得挺好,也吃得很好。”
王才说:“这比咱们以前的生活强多啦!”
列宁说:“是呀!生活比以前是好一点点啦,但是,这很不够。等咱们把白匪和外国军队完全赶跑以后,咱们建设一个繁荣的国家,那时候,咱们的生活就会更好起来的。”
随后,列宁又和他们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不知怎么的就谈到说话这个问题上来了。列宁说:
“你们的俄国话说的不错了,不过还应该学习识字,这样就更好一些。”
列宁又问中国话怎么说,于是,这几个中国战士就告诉列宁说中国话:你好、吃饭、喝茶……等等。
列宁一边学着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笔和本子,迅速地记下来。这时,真像是年是的父兄,和年轻的子弟在叙家常,那么亲切,那么欢乐。
从这以后,列宁见了这几个中国战士,就用中国话说:“你好,你好。”
春天来了,将要化雪的时候,每个警卫战士领到了
一双马靴,但李富清和王才的马靴太大了。他们去找管理员换换,管理员说:“不能换,发什么就穿什么吧。”
王才和李富清就商量着去找列宁解决。
李富清说:“走,咱们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
王才说:“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定能替咱们解决。”
于是,这两个人就满怀信心地去找列宁。但是一个工作员不让他们进去,说列宁正在写东西。他两个人一定要见列宁,工作员就用电话去问列宁,结果,他们两个进去了。他们两个找着了列宁办公的房间,先按了一下电铃,只听得列宁在里面说:“好,好,请进来。”
李富清和王才脱了帽子推门进去,只见列宁伏在房间右边的一张办公桌上正在写东西,见他们进来,就很关切地招呼他们:“坐,坐下。”
李富清和王才没有坐就说:“发的靴子大了,不能穿,想请求换一双。”
列宁说:“还有什么事情?”
李富清说:“没有了,就想换双合适的靴子。”
列宁说:“行,行,”说着,就拿起笔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他们,并告诉他们说,如果有事情,还可以来找他。
李富清和王才拿着列宁写的纸条去找管理员,管理员就带着他两个,打开库房,让他们两个各挑一双合适的靴子。
李富清到彼得格勒只住了一个多月,就跟列宁一道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富了。到克里姆林宫以后,李富清见到列宁的机会就较少了。
1919年夏天,白匪军邓尼金在南方战线发动了对苏维埃政权的猖狂进攻,托洛茨基瓦解了南方战线上的工作,红军接二连三地失败,到10月间,白军占领了乌克兰全境,侵陷了奥勒尔、图拉,直向莫斯科进逼。苏维埃共和国处在极严重的情况中。这时,列宁出了“大家都去与邓尼金斗争”的口号。列宁的卫队也调往南方,于是李富清就随卫队开到了前线,他被分配在骑兵一军六师三十三团担任侦察班副班长。临离开克里姆林宫以前,列宁还召集了卫队全体同志讲话,勉励战士们要英勇战斗,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把白匪军彻底消灭干净。——从这以后,李富清就没有再见到过列宁。直到1924年列宁逝世时,李富清正在莫斯科军事学校学习,他是学生代表,去给列宁守灵时,他才见到了列宁的遗体。
一次重伤
红军骑兵一军三十三团来到伏龙涅什地方与白匪邓尼金决战,把邓尼金打垮了。十月下旬,红军解放了伏龙涅什,邓尼金残部向南逃窜。红军骑一军紧紧追赶,1920年正月又解放了罗斯托夫,三月底就把邓尼金赶到黑海里去了。
李富清来到黑海岸边一看,只见海中停泊着几十艘帝国主义的军舰,由海岸到敌舰这一片海面上,黑鸦鸦一片舢板,舢板上载满了逃命的白匪军以及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而岸上却有更多的白匪军当了俘虏。当时红军用大炮问敌舰猛烈轰击,只打得敌人叫爹叫娘,有八艘敌舰中弹沉入海底,其余的敌舰就没命地逃走了。那些已经上了舢板,但来不及登上兵舰的白匪军和地主、资本家们,只得回岸向红军投降。
隔了两天,红军的舰队赶来了,李富清随着部队登上舰艇,向帝国主义军舰追去,他们一直追到土耳其边境才胜利反航。就在这个时候,波兰地主军侵入了乌克兰,李富清就随部队去乌克兰回击波兰白军。红军节节胜利,把波兰白军赶出了乌克兰。
有一天傍晚,红军骑兵三十三团把波兰白军从一个树林里撵跑了,缴获了几挺机枪,并且就在这个树林里宿营。
这树林的北边是个宽长各几十公里的大泥潭,看起来像是块草地,其实人踩上去,立刻会向下沉陷,根本不能通行。树林的南边七、八公里的地方,就是通往华沙的公路。
第二天天刚亮不久,红军发现敌人的骑兵沿着公路从西北直插向树林的东南。显然,敌人想利用那个泥潭来包围三十三团。
敌人的阴谋很快地就被红军识破了,司令部立刻命令红军骑四师从敌人南方插向北方与三十三团会合,形成一个反包围圈。
李富清所在的连队,奉令扼守临近公路的一段树林,阻击敌人逃窜。
战斗非常激烈,敌人冲了几次都没有冲出包围。打到中午,敌人派来大批飞机,在林子上空穿梭似地轮番俯冲轰炸,炸弹雨点般地倾泄下来,林子里到处有炸弹爆炸,枝叶纷纷截落,树杆齐腰斩断,尘土弥漫林间。
趁飞机猛烈轰炸的时候,敌人的骑兵又准备冲锋了。红军指挥员也命令战士上马,准备反冲锋。
李富清从战壕里跳出来,牵着自己的马,左脚刚踏上马蹬子,右脚还没提上来的时候,突然轰隆一声,一个炸弹在马身边爆炸了;李富清仿佛觉得右脚抖动了 一下,像给马踢了一蹄子似的;在同一时间里,帽子也飞走了。那匹马卟啦一倒,压住了李富清的双脚。李富清动弹不得了,幸而这时马明特跑过来了,他喊道:
“班长!你头上受伤了。”
李富清伸手一摸头,弄得满手是血,原来右后脑勺中了弹片,正在流血。这时李富清才感到有些疼痛。
马明特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那匹炸得只剩半边身子的死马从李富清的腿上移开。李富清想站起来,又感到右腿也有毛病,仔细一看,右腿也中了弹片。马明特把他扶在树根下,就替他包扎。这时,担架和护士上来
了,马明特把李富清交给护士,自己骑着马冲上去了。
李富清躺在担架上,只觉得昏昏沉沉,弹片长在肉里,像尖刀在翻搅;走了一段路,他就昏迷过去了。他仿仿佛佛觉得有一群波兰白军围着他,用火烧他,一会儿他又像是坐在黑海的舰艇上来追邓尼金匪帮,风浪把舰艇颠簸得忽上忽下……。
忽然他听到有人在喊:“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随后又觉得有一只亲切的手按在自己的额头上,他睁眼一看,两张黑黑的、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他脑子里忽地闪过一个念头:“这不是军长和委员吗?啊,布琼尼!伏罗希洛夫!”他正想去握那只手,但眼前一黑,又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经过多长时间,李富清醒过来了,他发觉自己正躺在火车上,身旁躺着很多伤员。一个护士在忙着替伤员换药。
李富清想支起身子,但感到头有千斤重,无论怎么也抬不起来,他着急地问道:“我们往什么地方开啊?”
护士看了他一眼,还以为他在说昏话,没有回答,又继续干她的工作了。
“护士同志,”李富清说:“火车往哪里开哟?”
护士见他的确清醒了,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她喃喃地说:“他真的醒过来了!他真的醒过来了!”李富清又问了一遍,护士才回答说:“我们到基辅去。你先别管这些,你应该休息。”
“为什么要上基辅?”李富清着急地问:“难道波兰鬼打过来了吗?!”
“不,不,不!同志,你的伤太重了,需要到后方医院去治疗!”
“我这不醒过来了吗?同志,我需要留在前方啊!”
“不行,你头上的弹片还没取出来呢!前方医院设备不够,无能为力,只有到基辅去才能取出来。”
李富清还在恳求留在前方,护士就严厉地制止他说话了。护士告诉他,他这次伤,没有两个月复不了原。
两天以后,李富清到了基辅后方医院。弹片取出来了。经过医生的细心治疗,一个多月以后就能够行动自如了。在伤口还浚有完全复原的时候,医院经不住他再三请求,就让他重回前线了。
“我不老”
李富清返回前方以后,积极地投入了战斗。他参加了格里彼奇尼的战斗;在华沙外国,他参加了攻打波兰白匪军的战斗;当华沙还没有完全攻克的时候,他随着部队调往南线打弗兰格尔匪军;在钦哈斯克地方消灭了弗兰格尔匪军,他又随着部队去肃清马赫诺残匪,把马赫诺匪帮全部消灭在乌克兰的山区中。——以后,苏联就开始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
在这些战斗中,李富清曾经三次负伤,他坚持不下火线;他曾经多次出入敌军心腹之地,侦察敌军情况——在一次侦察中他差一点儿牺牲了;他曾经多次端着炸药包,炸毁敌军的碉堡和桥梁……。他表现了十分英勇的气概。
1922年春季,李富清在骑六师部队文化学校念书,并在这时加入了共青团。一年以后,他又被调往莫斯科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顿巴斯矿区工作。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北,成立了所谓“满洲国”。李富清同志正好在这个时候回家省亲;因为伪满洲国当局不允许他入境,他只得随当时退入苏联的东北抗日军转入新疆。……
李富清现在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工程处工作。他今年已经五十九岁了,虽然门牙都脱落了,但精神还挺旺盛。谁要说他老,他就会大声地说:“我不老。你能干什么,我也能干什么!”
(李国靖插图)
(本文将在“红旗飘飘”第四集同时发表。本刊作了一些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