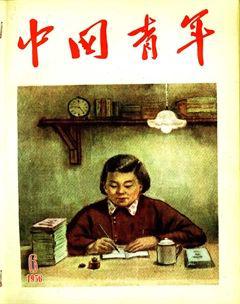真实与完满的典型
钟惦斐
我曾经有过一种现在看起来是很天真的想法。我以为,黄色炸药(就是电影“董存瑞”中的那个炸药包)在中国近十年的革命历史中所起过的作用,是值得诗人们写诗去赞美它的。因为据我记得,这炸药包是一九四六年开始在前线使用,在这以前,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就一直面对着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和后来又是蒋介石的碉堡政策。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以至解放战争初期,在军事上主要就是碉堡与反碉堡的斗争。在那时候,我们要摧毁敌人的一个碉堡,得从几百公尺外挖坑道,然后把黑色炸药做成的地雷,放到敌人的碉堡底下。这样做当然很费时间;有时挖到了,敌人的援兵也赶到了。而且还常常有把地道挖错的时候,不能把炸药准确地放到敌人的碉堡底下。
一九四六年以后,解放区各战场普遍使用了用黄色炸药做成的炸药包去摧毁敌人的碉堡,这就大大地加快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
但这样说,便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难道炸药包自己会跑到敌人的碉堡跟前去么?不会。拿着炸药包到碉堡跟前去的,是人。是那些具有高度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战士。他们真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明明知道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是争着去,抢着去。“董存瑞”这影片有一场很动人的戏,便是选爆破队长。有人赞成五班长王海山,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经过一场激烈的很有意思的辩论,才选上了董存瑞。而后来董存瑞也正是在炸碉堡的事情上,完成了他的英雄事迹。
这就说明,该歌颂的到底不是黄色炸药,它只是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一个条件;而是人,只有人,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条件。
董存瑞这部电影最出色的地方,便是它始终没有离开对于人的描绘。像“英雄司机”那样去描写“锅炉的水上得太满”、“开车的时候汽门开得太猛,汽室里进了水,造成汽水共腾,才把韦鞴杆折断了”等物理活动的内容是没有的。像“在新事物面前”这出戏中把“团结矿”和“烧结矿”的化学成分当做戏剧的冲突点也是没有的。
便是在描写人方面,这部影片的最大特征,还在于它是大胆地破除了那许多不必要的清规戒律,硬是很真实地按照人物所可能想和可能做的事情描写出来。其结果,就使我们从银幕上看见一个活生生的董存瑞、活生生的郅振标和赵连长,活生生的牛玉合、王海山和罗志英。
据说是有这样的书呆子,他们不爱活人,而是一心想到“书中自有颜如玉”,他们不盖房子,而是向往“书中自有黄金屋”。“不可救药”这四个字用来形容这种人,真是最恰当不过。而我们,还是爱活人。因此我们要求我们的故事电影少去描写那些在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理想人物”。这些人物固然没有缺点,但也不爱生活。他们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也只是为了要发现物理学的公式,为了证明“下坡要使劲,上坡就容易得多”的道理!或者逛逛公园,随便看见一个孩子,也一定要牵扯上小学教员便是园丁,在培养后代;公安干部也是园丁,在拨草除虫等深奥的道理!真正是苏格拉底,是黑格尔或恩格斯,也未必会成天生活在这样的哲学气氛中的!?
我们要求电影应该真实地描写先进工作者,英雄人物,乃是因为我们想效法他。而“董存瑞”,在看过这部影片的青年中的第一个反映便是:像董存瑞这样的英雄,我们是可以效法的,能够效法的。从银幕上的第一个镜头——董存瑞瞅着那些神气活现的八路军新战士,自己也想当个八路军的新战士起,到他拿着爆破队的大旗,最后用眼睛在全场梭巡着,想立刻决定把“火力”的旗子交给谁这样一些重要而且有趣的情节中,谁只要不是生活中的落伍者,就也会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发现在自己的性格中。那些足以在革命事业中燃起火花的部分。扮演董存瑞的演员张良同志说,他不仅早先不认识董存瑞,而且便在决定扮演这个角色后也没有去过董存瑞的家乡,没有访问过董存瑞的连队。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的表演。这便是因为剧本中所描写的董存瑞,是一般人都能够了解的。在一般人和董存瑞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东西。
在我看来,这便是董存瑞这都影片平易真实的地方,同时也是它能够普及,能够为许多人所爱好的地方。
这样说,“董存瑞”好像只不过是一部普通的、平凡的影片罢了!或者说董存瑞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人而已。但又绝不是。人们爱好“董存瑞”这部影片的全部理由,除了董存瑞这个角色有着一般革命青年所共有的地方以外,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有着许多人所没有、或者说现在还没有的地方。
拿我们刚才提到的、也是“董存瑞”这一影片中最动人最富于表现人物个性的情节来说吧,在经过一番争执之后,董存瑞当了爆破队长。当他把“突击”的旗子交给牛玉合,“支援”的旗子交给郅振标,而剩下“火力”的旗子不能立刻决定交给谁的时候,影片停止了音乐,全场没有任何动静,通过银幕上董存瑞的近景,我们看见他的眼睛在困难地搜寻着!而接着的镜头是从郅振标、牛玉合等人摇向王海山。把旗子交给王海山!王海山几乎是从董存瑞入伍的第一天起,就对他有意见!一直到影片刚才发生过的争执。在影片中,王海山和董存瑞几乎是对头。但是董存瑞还是最后决定把“火力”的旗子交给王海山。当董存瑞叫着“五班长王海山”的时候,王海山几乎一时还不能够相信这叫的就是他!当董存瑞又重复说:“五班长王海山接旗”的时候,据导演郭维同志告诉我,在摄影场中,这时扮演王海山的演员王枫,眼泪止不住刷地便流出来了!演员和角色都同时被感动了!
甚么原因使得角色、演员和观众都在这样的情节中变得异常激动,并从这里得到教育?因为它确实是从政治上总结了董存瑞的全部生活历史。它使我们回忆起董存瑞和郅振标还在儿童团站岗放哨的时代,就被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八路军所吸引。他们拚死拚活地要追寻这个部队,但是他们却不十分懂得这个部队。郅振标只看见新枪、新军装,而董存瑞则想到“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那一套。从思想本质上说,是农民的。后来是区小队的政委王平同志教育了他们。董存瑞经过许多奋斗,入伍了,但是娇气得很,也稚气得很,为了十发子弹的事,竟至激动得不能自持!第一次战斗没有缴获,连是批评他,他竟至哭了。其中有一场极有戏剧性的戏,便是他和郅振标为了在火线上自动出击的事互相在连长面前争着承认错误,直到连长说这不是错误,还拿出团部的一枚奖章时,董存瑞又赶紧说功劳是郅振标的。这该足以说明董存瑞是一个不平凡的战士了吧?但他究竟是在郅振标面前,是在他儿童时代的朋友面前。现在决定要把“火力”的旗子交给谁的问题,却面临着一个总是反对他的人。在这时候,决定的权利是属于他的,他虽然没有作威作福的权利,但他却有着作威作福的条件和可能。在这里,影片所表现的内容,对我们有着极深刻的教育意义,便在于它通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告诉了我们:伟大的性格,虽然常常是环境培养的结果;但是伟大性格的完成,却一定要依靠自已。所以我以为并不是一定要董存瑞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他才可以叫做伟大的战士,便在这一场戏中,他的伟大的战士的性格,便已经确定地形成了。
我们这样来估价影片中的这一情节,而且着重从这个角度来估价这个影片的思想性,那么,是否说董存瑞后来炸碉堡的事倒是无足轻重的呢?是否说一个伟大的战士的性格,只表现在他能够正确地对待同志和朋友的关系上呢?是否说在严重的对敌斗争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他们反而是不重要的呢?不是的,绝不是的。如果一个人的伟大,只表现在他对同志和朋友的慷慨上,而不表现他在困难中的进取精神,危难时挺身而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或者正如伏契克所说,在决定性的关头做他所应该做的事,那么,我们的所谓英雄,只无非是些新型的道学先生,值不得夸奖的。但是问题还在于,这部影片如果没有关于选爆破队长的情节描写,我以为就不能说董存瑞在政治上是一个已经成熟了的战士。他后来的牺性,当然是可贵的,但是从整体上看,如果没有前面所说的情节,影片要塑造董存瑞
这一英雄的形象,就还是不很完整的。董存瑞在授旗给王海山之后而又在炸桥中牺牲,这就加深和发展了他的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伟大性格。
我们认为有一种意见始终是不正确的,这就是认为写英雄一定要写他的缺点,不然就不真实,不可爱;竟至有人还说英雄在牺牲之前一定会有三分钟的动摇,不然也就不真实,不可爱。
我们称持有这种意见的人为“犬儒主义者”,这就是因为他们非常不幸地无论从实际上和想像中都不能够理解英雄,特别是不能够理解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英雄。因而他们也不能够了解,在一个真实人物的生活中,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缺点,而什么不是。在我们看来,董存瑞的“走南闯北”思想也好,容易激动并且还有些执拗的脾气也好,这算得是什么英雄性格的缺点呢?董存瑞不也是人么?不也和其他人一样扛着一杆大枪行军作战么?不也时时刻刻在接受党的教育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么?如果这些也算做是英雄性格上的缺点,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便是所有的人都是有缺点,而且都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从“董存瑞”这部影片中,我们当然不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我们所指的一个革命者的缺点,主要是他在对待革命、对待集体和真理的问题上是否怀着个人的偏见,而且坚持这种偏见。董存瑞在经过一阵内心斗争之后还是决定把旗子交给王海山,便说明他没有这种偏见。
董存瑞对于王海山是否也有意见,显然是有的,不然他就不会在授旗的时候还要加以考虑了。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对王海山有意见,重要的问题在于当他在考虑决定革命的重大问题的时候,是否因为这种意见,便完全不顾革命和集体的利益,而让这种意见占上风,因而使得战斗遭受损失!董存瑞从事实上表现出来,他不是这样的人,因此就不能说董存瑞对王海山是怀有偏见。
如果影片在这样的情节上对董存瑞的处理不是现在这样,而是真正表现出他的偏见,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董存瑞在性格上真正是有缺点的。
因而我们所谓的缺点,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是有关革命品质的缺点。那么有人问:“还有什么是无关革命品质的缺点的么?”我们说:有的。董存瑞在这一英雄性格完成之前所表现出的一些缺点,便是属于这一类的。而我们要求作品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真实地描写人,我们就绝不应该回避,而且也绝不可能回避这样的缺点。
再说,英雄如果临到牺牲之前都有三分钟的动摇,那还叫做什么英雄!?你们看,当董存瑞看见部队在前进时遭到桥上敌人严重的杀伤,因而决心自己去炸掉这一堡垒时,郅振标曾阻拦他,说:“班长,我去。”而董存瑞害怕郅振标不能完成这一困难的任务,还是决心自己去。并且说:“如果我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桥上的堡垒炸掉!”在这种时候,董存瑞有什么一丝一毫的动摇!?你们又看,当董存瑞拿着炸药包在桥下找不到依托,但是部队已经吹起了冲锋号,他的战友们已经开始冲锋时,他把炸药包举在手上,点着了导火线!导火线迅速地燃烧,并已接近他的手掌时,他有什么动摇!?他的声音像钢铁一样坚定:“为了新中国,前进!”
当这部影片将要在全国上映之前,我以为对青年朋友们谈谈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第一,我们表明:文学艺术一定要真实地去描写英雄人物,而不是把英雄人物理想化,描写成在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理想人物”。如果你们读过“真正的战士”这本书,你们也许会发现,影片有许多地方是和这本誊不一样的,这就是说,影片在情节内容上、艺术描写上有许多假想的地方。但这是应该被允许的。这许多假想的地方,并没有把英雄人物“理想化”,而是更真实地表现了英雄人物。因而在这影片中的所谓“假想”,实际上是艺术描写上所必需的“想像”,是艺术描写过程中必需的“概括”,使影片能够按照人物所想到和可能想到、做到和可能做到的事情真实地描绘出来的。第二,我们又表明:在对待描写革命英雄人物传记的作品中,我们不只能够看出他和我们有着相似的地方,我们的任务还在于能够看出他和我们不相似的地方;这就是说,不仅能够从英雄身上看出我们已经有的,还要能够看出我们所没有的。而“董存瑞”这部影片的可贵处,正在于它不仅是真实的,在董存瑞的性格中,有着普通人所共有的东西;还在于它是完满的,在董存瑞的性格中,有着普通人所绝没有的东西,有着普通人需要极大的努力才能达到的东西。董存瑞的形象,是普通人的伟大形象。而这一形象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它是优美的、动人的、令人向往的,能够使我们在为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把我们的思想感情确切地提高一步的。
在这篇文章里,我只着重谈了董存瑞这一英雄形象的真实和完满的地方,至于这一形象和“董存瑞”整个影片的优美和动人的地方,最近看了“董存瑞”的最后完成片,我准备以“第四次激动,第四次喜悦”为题,比较详细地说出我这方面的意见。
三月八日
编者按:作者关于影片“董存瑞”,拟写一组文章,第一篇题名“一个真实的战士”(初谈影片“董存瑞”),发表在今年的:“文艺报”第三期上,读者如有兴趣,可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