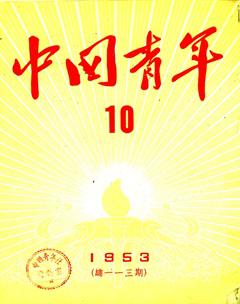我们一定能学会的——记建设鞍山的人们
陆涧
仅仅是几天没有到安装透平鼓风几的现场上来,这里的样子已经大变特变了。那风管、汽管、油管等各种管道,已经漆上了各种不同的颜色,地上玉石般的磁砖已经铺好,那满身铁锈的旧铁管已经拆去,工人们也已经安上了白金般的耀亮的栏杆。在这一座新的透平鼓风机的旁边,那蜷伏着的几座旧鼓风机,现在就更加显得黯然无光了,蒸汽吹击着汽轮的叶片正发把吭吭的声音,彷佛在诉说着自己年遇陈旧的命运。使人看来那来自苏联的第一流的自动化鼓风机,活像一倍精神充沛的青年,那旧鼓风机,真好比一个衰弱的老人了。
也许一个年轻人,或者是一个陌生人到了这里,不会联想到许多别的问题,但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老的钳工们来说,对外我们的安装鼓风机的全体同志们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惜。想不到只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这世界上第一流机器的安装工作,经过他们的手,竟保证了头等的安装质量。
安装鼓风机工程段的夏树林队长和几个年老的钳工们,他们过去在伪满时期,曾经在这里参加过安装鼓风机的工作。那时候,他们干这工作,是听日本人和德国人的使唤,干些要气力的活儿,扳扳螺丝,拿拿大锤,跑腿而已。弄得不好,吹胡子瞪眼,挨骂受打,也是平常事儿。在自己的土地上,人们连挨近机器看看的权利也被剥夺尽了。年轻的工人们更不用说了。他们对于这样的机器,不但没有见过,甚至连名词还是第一次听说。技术人员的情形也是一样。技术员胡兆森是去年暑假上海交通大学动力系毕业的毕生。在大学里他读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课本,他曾经见过一些美国的、瑞士的,或者是日本的透平机,但像这样自动化的苏联鼓风机,他也是第一次才看见。在这些人们的面前,要安装这样新式的机器,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呵。
正在我们困难的时候,苏联专家沙巴少夫等同志从列宁格勒来到了鞍山。他们是专门来到这里帮助我们安装鼓风机的。沙巴少夫同志到了我们的现场。就开始给我们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讲课,现场很快地变成了一个课堂。他从机器的设计讲起,一直讲到机器的构造、性能和安装的过程,讲到难懂的地方,便拿出许多苏联的透平挂图,照图讲课。有时地和听课的人一块到仓库里去,把一箱一箱还没有打开的机器,一件一件拆开来讲。他常常自己讲一遍,第二遍让技术员胡兆森和大家讲,他在旁边听,胡兆森有讲错的地方,他就指出来,自己再重说一遍,一面说到大家明白了为止。
那时候天气正热。专家沙巴少夫一面讲课;一面就带领大家进行机器安装的预备工作,他常常脱去上衣,抡大锤,拿锉刀,和工人们一块动手干活,有时候一直工作到半夜。有几次,沙巴少夫同志白天黑夜,一步也不离开现场。到了星期六,工人们看他实在太累了,对他说:“就是机器也该歇歇了,你明天不要来了。”但第二天,沙巴少夫同志又来上班了。正在安装工作最紧张进行的时候。沙巴少夫同志因为过度的劳累病倒了,工人们听说后,大家买了水果罐头去看他。他们去时,沙巴少夫同志正发四十度高烧,神志不清,一看见工程段的同志们来看他,他就急着问现场上的工作情形。第三天,沙巴少夫同志又带病来上班,工人们知道专家病还没有好,都一致要求他继续休养,但沙巴少夫仍是带病领着大家,坚持工作,不离现场。
由于苏联专家的来到,我们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们好像进入了一座技术的学校。有些老钳工们,他们现在不但知道应该这样做,而且还努力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并且知道了怎样计算就能得出这样的结果。他们有时侯,自己还捉摸着书图,譬如画个小零件,让专家帮助修改,看那条线对,那条线不对。他们什么也想学学,什么也想会。现在有很多人说:这几个月里学到的东西,比过去二十年学到的东西还多呢。十八岁当钳工,今年四十九岁的夏树林队长,他好几次病了,但第二天,他又早早地到现场来了。人们劝他休息一下,他总说:“专家这样教咱们,咱们拼死也得学会它。”有时看他实在无法支持了,工地主任只好下命令让他去休息。苏忠孝是个钳工组长,他的组担任过安装油泵的工作。油泵像人的心脏一样,弄不好,鼓风机就不听使唤。他们的工作,专家每天都要看好几次。后来,专家就放心不再看后。苏忠孝请专家去检查,专家说: “我信任你的工作,可以不必再看了。”后来,当填写安装纪录的时候、专家看了安装油泵的全部工作,果然百分之百合乎标准。最近这个当了十几年钳工的苏忠孝,正满怀信心准备去
参加录取技术员的考试。这真是一个努力的人,他和另外一个钳工组长丁成志,一个是负责安装透平的; 一个是负责安装鼓风机的。他们不但努力学习自己安装的技术,而且都使劲留意对方的机器怎么安装。现在透平鼓风机安装完毕了,他们希望:在下一次新的机器安装工作中,可以担负透平鼓风机的全部安装工作了。
学习是这样狂热地引导着人们在工作中前进。我在鼓风机现场上认识的王久泰,他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共产党员。有一次,轴瓦的疏油槽和油箱要清洗,清洗的标准是要用洁白的手绢擦不出黑颜色来。有的人就发愁说:“这擦到什么时候才能擦干净呢。”他和另外四个年轻人挺身而出,把这个工作包了下来。那大热天,吃冰棍也不觉凉,他们钻在机器里头工作,动也不能动,一身又一身的汗把衣服都湿透了,头发也湿得滴下水来。他们先用钢绳头刷,用砂轮打,然后再拿煤油洗,洗后又用旧布擦。有的地方拳头也放不进去,只能伸进手指头。擦了几天,把洗干净的手放进去一摸,拿出来,手上还是有黑印子;但他们一直不灰心,坚持努力,经过了二十天的功夫,他们的工作终于圆满做成了。我问王久泰:“你学得怎样?”他把自己的肚子一拍,笑呵呵地说:“过去什么也不懂,现在全装在我这里头啦!”
在学习和工作中。技术员胡兆森成了工人们热爱的朋友,他不但是自己学到了很多从来没有学过的东西,而且,他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把过去和现在学到的东西教给工人们。专家说过的东西,他在一天工作之后,领着技术员们熬夜编成讲义,然后再讲给大家听,当安装透平鼓风机的工作进行到轴承找中心的时候,胡兆森就成了工人们一步也不能离开的人。找中心的工作是安装工作中最精密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是要离分精确地调整透平和鼓风机的四个轴承,使轴的中心在一条线上对起来,高低左右都不能超过二、三“道”(一根头发的粗细是七“道”或八“道”),专家亲自给大家做了一遍以后,就交给工段的同志们自己做了。于是,大家的心,一跳一跳,都好像和这个轴系在一起似的。大家每做一次,胡兆森就帮着计算结果,看离中心还差多少。那时候,真是紧张极了,胡兆森每计算一次,人们都围着他,眼睛都死死地盯住他的脸孔,有时候,胡兆森跑到屋子里去计算,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跟着跑进去,每逢胡兆森宣布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加接近中心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找中心的工作进行到第三天,胡兆森快乐地向大家宣布说:“同志们,只差半道了。“就是说,过去在日本侵略者统治时期要做两三星期的工作,我们费了三天时间就把它做成了,特别是轴承的公差做到只有一根头发的十六分之一了。但工人们并不满足,他们问苏联专家:我们要不要做到一点点公差也没有。沙巴少夫同志笑了笑,满意地说: “可以不要做了,这已经超过原来的标准了。”
当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有些日本工程师在离开鞍山的时候,他们曾经说:“再过三年,鞍山的工厂都要长满高粱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事实是我们在苏联无私的帮助下,伟大的工程正在鞍山紧张地进行,各种各样的自动化机器已经开始在我们这里安装起来。我们的鞍山,不久以后,就要成为全世界第一流的钢铁城市之一,这座新的透平鼓风机的安装成功,虽然只是我们鞍山开始进行的千百件工作当中的一件,但它却是象征着我们正在胜利地开始举步走向这个日子了。
(图片见原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