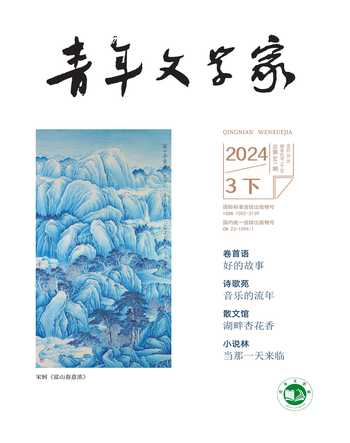历史叙事中的生态观照
胡涛
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称历史著作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指出:“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可见“历史”是可以存在于叙事中的。中国文学传统中自古就有“文史合一”的创作理念,足见历史与文学叙事关系之密切。然而,当代历史叙事中,作家如何用文学去观照历史,是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对于书写武陵地区土司历史的贝锦三夫而言,长篇历史小说《武陵王之皇木遗恨》在尊重土司历史史实的前提下,其生态书写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重要价值诉求。作者在历史记忆中,对武陵地区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展开了独特思考,其作品中流露的生态意识体现了作者对当代生态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贝锦三夫在其小说中,以酉水河畔的盘顺土司王向景春和朝廷木政指挥使徐珊为原型,引入了明朝嘉靖年间重要的历史素材—“卯洞的皇木采办”与“阳明心学的传入”。作者在讲述历史事实的同时,不乏文学想象,深刻地反映了武陵山区的地域风情、毕兹卡的民俗文化和社会活动。作者在小说中的生态观照正是通过对毕兹卡“原生态”文化的书写和阳明心学指导下的生态实践,以此来展现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
一、历史叙事中“原生态”的民族文化
所谓“原生态”文化,指的是“在大工业文明来临之前还存在着的那些自然的生活方式、艺术形态和宗教信仰”(徐兆寿《一种新的写作现象:原生态文化书写》)。原生态文化内涵的重要特征是“地方性知识和民间色彩”。研究者通常用“原生态”来形容少数民族地区原始的自然环境和当地独特的民风习俗、自然崇拜等民族文化。
“原生态的自然美是一种自然的大美。”(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贝锦三夫笔下的武陵地区,位于湘、鄂、黔、渝交界处,那里山高水远,地理位置复杂,保留了最为原始的自然美。也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毕兹卡文化较少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保留了较为原始的一面。而长期生活在武陵地区的贝锦三夫,在讲述历史的同时,用自身体验向读者展示了毕兹卡“原生态”的民族文化。
丧葬习俗是毕兹卡人重要的民俗之一,其丧葬仪式最能凸显毕兹卡独特的民族性格气质。毕兹卡人对于丧葬特别讲究仪式,“升幡竿,打锣鼓、打绕棺、跳丧鼓,破血湖、解枉死结、祭奠青山”(《武陵王之皇木遗恨》)。畢兹卡人认为,举办隆重仪式才是祭祀故人的最好方式,场面越热闹越有意义,这种隆重的丧葬仪式并不是以表达在世者的悲伤为主要目的,而是表达一种特殊的意义—“以悲为喜”。对死亡持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是毕兹卡人对生命的特殊理解,另外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在世者能够幸福、团结。笔者认为这才是隆重仪式的最直接体现,试想一个家庭、一个族群内没有稳定、和谐、幸福的关系,而是经常矛盾不断,怎么会有丧葬仪式的举行?怎么会有如此热闹的祭祀仪式?可见,毕兹卡人对生命的独特理解,是集体无意识生殖崇拜的结果,他们希望子孙万代团结幸福。
舍巴日是毕兹卡人自己的节日,在这天毕兹卡人会举办文艺体育和祭祀二者兼得的活动,即跳摆手舞,来祭拜祖先、崇拜自然。盘顺土司普舍树下的宽阔院坝是盘顺土民们庆祝节日的重要场所。普舍树作为盘顺土民心中的特殊文化符号—福,“它是观世音菩萨送给你们漫水人的福报,它能为整个漫水坪百姓普施幸福!”(《武陵王之皇木遗恨》)普舍树更为奇特的是它能辨识族人,因为它的花瓣只会落到盘顺族人身上。每年舍巴日,盘顺土司王都会在普舍树下与民同乐,为了表达对祖先的崇拜和对自然的敬畏。
另外,毕兹卡人对神秘的自然有着独特的崇拜。首先是对神木的崇拜,盘顺境内翔凤山上的九阳金丝楠木是盘顺向氏的祖迹神木,据说曾庇护过被追杀的向氏先祖。此后,每年夏至日便成为向氏祭奠祖宗、拜祭神木的大典之日。焚香祭祖,载歌载舞是常规仪式,以傩祭祖是此次活动的中心,包括傩祭、傩技、傩戏、傩舞、傩歌。这隆重的祭祀仪式一方面是为了表达族人对向氏先祖的追念,希望得到神木的庇佑,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提高族人的自信心与荣誉感,维系族群关系,加强族群的凝聚力。
总之,贝锦三夫在向读者讲述历史的同时,书写了毕兹卡居住地优美的自然生态,呈现了毕兹卡“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从这些民族文化中可以看出毕兹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在丧礼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歌舞中亲近自然、热爱自然,在崇拜中敬畏自然、保护自然。当然,推动毕兹卡地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用生态理念指导实践,则离不开两位重要历史人物—王阳明及其弟子徐珊。
二、阳明心学指导下的生态实践
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于明朝正德元年间,得罪宦官刘瑾,被贬贵州龙场,并顿悟出“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事上练”等心学理论。他在当地创办龙岗书院,广收弟子,通过讲授心学来传播阳明心学思想,这对当地土司“蛮夷”有一定教化作用。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正是西南土司制度上升时期,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当时土司领域内广泛传播,“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对土司社会的治理与教化”(苟爽《阳明学说对贵州民族社会的影响》)。而阳明心学在盘顺土司境内的教化与影响则离不开王阳明的弟子徐珊,他是阳明心学的积极宣传者和实践者,是践行生态理念的重要人物。因此,徐珊与阳明心学思想传播成了贝锦三夫历史叙事中的重要历史素材。
徐珊作为朝廷官员来卯洞督查木政采办工作,在与盘顺土民的交往过程中,将阳明心学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徐珊用阳明心学指导采木,其生态理念也得到传播。盘顺土司在阳明心学的指导下,不仅如期完成了朝廷的采木任务,更是把采木“后遗症”控制到了一定程度范围之内,“皇木砍伐,以明朝为甚,湖广土司地区为害尤烈!”(《武陵王之皇木遗恨》)皇室采木,实质上就是封建徭役,对武陵山区环境危害巨大。但徐珊用阳明心学指导的采木工程,对盘顺土司境内的环境破坏有很大程度的降低。
“明代兴起的皇木采办,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大致可分为勘察、采伐、转运、运解交收、储备等五个环节。”(谭庆虎、田赤《明代土家族地区的皇木采办研究》)其中转运树木最重要的是“找厢”,即“先由石匠开采巨石,形成简易的路基;架长空中地段,做好支架,然后以两列杉木平行架设在路基和支架上,形如今日的铁路”(谭庆虎、田赤《明代土家族地区的皇木采办研究》)。在此过程中,为了寻找宽阔的路基,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新开路、砍伐障碍物,为了保护环境,盘顺土司王和徐珊多次商议运木路线,徐珊多次上山勘察最佳路线。徐珊作为阳明心学的传播者,自身始终在践行着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即“知行合一”,也就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徐珊自来到盘顺土司后,秉持着“食君之禄,必事君之事;为民之官,必言民之言”(《武陵王之皇木遗恨》)这一为官信条,坚持忠君亲民,所以在采木时,始终在做保护环境的努力。
而早期同作为阳明心学的传播者费度,他的采木做法与徐珊截然不同。此时的费度已经被权力和欲望冲昏了头脑,为了早日运走皇木而腾出手去寻找通天神木,他随意下令,让散毛土兵带着火枪对沿途进行拉网式搜寻,破坏了当地环境;运送皇木时,同样不听取漂木工的意见,坚持首汛漂木,最终导致卯洞被堵,死伤十余人。可见,二人的做法截然不同,在“致良知”方面,费度被欲望蒙蔽了双眼,在实践中没有良知,而徐珊真正做到了“心即理”,不为外界影响,遵循天理,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
土司境内,各司对于“王室子弟”的教育比较重视,如果土司内没有学堂,就要去外地州县庠序学习,以此来学习孔孟儒学、汉家礼仪。盘顺代主夫人向凤阳自小就被送到外地辰州府求学,更有幸亲自受到阳明心学弟子徐珊的教导,这对她回族代政有重要影响。“知行合一”的思想一直指导着她践行生态理念。
三、在历史叙述中回望与反思
作者在后记中写到,该作品是“重点展示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物命运,突出历史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着墨于当时毕兹卡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妙,着墨于艰难的生活景象和向往文明的追求,弘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历史小说《武陵王之皇木遗恨》聚焦盘顺土司地区的皇木采办事件,塑造了众多真实而又典型的历史人物,向我们展示了武陵地区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其中流露的生态意识更是具有现代意义,值得读者反思。
首先,对历史的反思。作者的历史叙事,始终坚持着理性,向我们展示了毕兹卡历史文化,同时也发挥了文学的想象力。不论九阳神木是否真的存在,这在不影响历史真实的同时,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与反思性,让读者真正认识到历史上的皇木采办对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武陵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其义在于羁縻勿绝,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政治上巩固其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纳贡。因此它是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压迫少数民族的制度”(《明朝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特定历史时期,推行土司制度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另一方面它也对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压迫。拿皇木采办来说,它不仅浪费物力、财力、人力,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而且对武陵地区的森林植被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导致大量珍贵树木被采伐,使其难以恢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当然我们也需要辩证地看待历史,在惊呼京都地区古建筑、皇室宫殿等文化遗址时,我们能想起武陵地区皇木采办这一段艰辛的历史。
其次,对欲望的反思。生态破坏与人类欲望的无限膨胀始终分不开,小说中的费度与徐珊同是阳明弟子,接受心学的洗礼,是阳明心学的重要传播者,但后来渐行渐远。这便是各种欲望侵蚀的结果,费度不仅想抢夺采木的先功,而且与朝廷要官严嵩勾结,私谋九阳神木,方便为自己安置一副死后不腐的棺椁。另外,土司境内看似平静如水,实则暗潮涌动,各种矛盾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当地生态的破坏埋下了隐患。可以说,作品从多方面给我们展示了权力私欲对自然生态美的摧毁,在自给自足的土司境内,山水虽美,但庙堂、江湖终究抵不过欲望的侵蚀,自然生态的破坏不可避免。阳明心学虽主张“心即理”,但需要人们有正確的主观意识和认识能力—用生态意识来指导实践,否则便会同费度一样,与真理渐行渐远。细读作品可以发现,贝锦三夫在作品中流露了鲜明的生态意识,一方面讴歌了武陵山区多数土民有节制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觉生态意识,这是他们千百年来与自然共生总结出来的经验;另一方面通过皇木采办对武陵生态毁坏这一事实的展示,反映了自然生态与占有的问题,实质上是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疏离只是生态危机的表层显现,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反映的是隐藏其后的人类自身精神生态的失衡”(赵树勤、刘倩《从“浅绿”到“深绿”—新时期生态文学研究综述》)。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生存与占有、人类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值得现代人思考。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贝锦三夫用传统章回体的形式,在历史的叙事中,向读者展示毕兹卡神奇秀美的自然生态以及“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并通过皇木采办和心学传播特有的素材,酝酿出了独特的生态意识,有意地体现着对封建王朝、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无意地在作品中流露出对自然的崇敬和对生命的敬畏的自然生态意识。小说悲剧的结尾无法掩饰作者内心的惋惜与无奈,九阳神木“含恨”被掩埋和心学传播者含恨沉潭的悲剧结尾,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仅是对毕兹卡历史的反思,更是对现代生态状况的焦虑与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