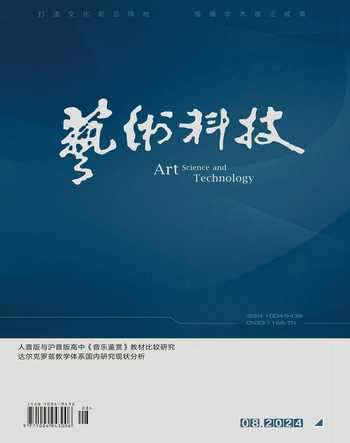《封神演义》中的替罪羊理论研究——以“哪吒”角色故事为例
摘要:目的:文章试图从比较神话学的视角解读中国经典文本《封神演义》中哪吒的角色故事和人物形象,分析其人物故事中呈现的替罪羊机制,由此探讨中国神话文学中替罪羊机制的呈现方式与特点,并尝试探索对中国神话和传统文学文本进行比较神话学等多元化跨学科视角分析的可能。方法:替罪羊机制是法国人类学家、文论家、思想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提出的理论。基拉尔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审视文学文本,创造性地发现替罪羊机制的广泛应用,将含有替罪羊机制的文本称为迫害文本。文章认为哪吒的故事符合迫害文本的结构范式,拟以勒内·基拉尔的替罪羊理论为切入点,采用替罪羊理论阐释哪吒从出生到封神的人物故事。结果:哪吒的原型源于佛教,在宗教及文学文本中逐步本土化。在《封神演义》中,哪吒的形象被进一步文学化、戏剧化,身份确认、迫害过程、迫害结果三个阶段与替罪羊机制的呈现相吻合。在中国古代伦理忠孝等传统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人物故事,融汇了跨越时代的文化与思想价值,从身份的生成与身份的递进两个方面体现成熟文明中神话对于暴力仪式本质的隐藏和秩序生成的过程。结论:《封神演义》文本符合替罪羊机制作用的普遍混乱、指控罪行两种范式,哪吒的故事更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哪吒故事作为迫害文本,揭示了历史背景下集体无意识的迫害惯性特点。
关键词: 《封神演义》;哪吒;替罪羊理论;勒内·基拉尔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4)08-00-03
0 引言
《封神演义》作为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的经典代表,融合“讲史”“神仙”“灵怪”等类话本特色,以历史事实为主干,讲述了商灭周兴的历史故事。《封神演义》虽是一部神魔小说,但大部分故事取材于民间文学,并融合大量民间信仰,展现了创作时期三教并行的社会文化特色,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意义[1]。作者结合佛道中的典籍故事以及民俗传说,构建了哪吒从出生到成圣之间的完整故事。近年来出现了改编封神人物故事的潮流,其文本为当代文学与影视作品的改编输送了大量养分,也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学不朽的生命力。不少学者开始重新研究文本,带来了多重视角观照文本的新热潮。
用替罪羊机制研究中国文学的论文并不多见,选取的文本一般为《西游记》《淮南子》《三国演义》《白鹿原》等。刘海丽从替罪羊理论分析《红楼梦》中的黛玉之死,认为其死亡的情节是一个具有替罪羊象征意义的仪式[2]。也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替罪羊理论入手分析以神话形式写就的《封神演义》文本。苏勇在《多重视角下的<封神演义>》中提出,妲己替罪羊式的角色设定是小说的叙事者苦心经营的一个文本策略[3]:小说最后借姜子牙之手,通过斩杀这只象征恶的替罪羊平息众怒,净化城邦。孙博的《基拉尔替罪羊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典文学文本研究》,试图总结替罪羊机制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并在分节中引用《封神演义》文本。他认为,基拉尔所强调的是一种神话思维,在中国文学的迫害文本中,替罪羊只會在不以人为对象的迫害文本中发生二次转化(神圣化),在以人为对象的迫害文本中发生一次转化(驱逐或死亡)[4]。而在研究哪吒的论文中,常常将哪吒人物故事作为独立叙事文本,对其人物形象构建与流变的研究占多数[5]。除此之外,还关注跨媒介或跨文化叙事、传播中的哪吒形象[6]。
立足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重新进入《封神演义》这一暴力文本,用替罪羊机制重新分析其人物形象。不同于以往学者的研究路径,本文聚焦于《封神演义》中的“哪吒”这一经典角色,采用替罪羊理论分析其人物故事,并试图总结和解释其作为迫害文本的独特之处。
1 迫害范式中的身份确认
在《封神演义》中,可以找到基拉尔所言迫害文本的踪迹。从所处环境看,当时社会秩序混乱,面临严重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原文提到“何为乎辟纣哉?辟纣之杀僇忠良也……民不聊生,死亡略尽”[7]。由此可知,文本记录或构建了一个由于少数统治者不作为而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时空环境。
哪吒在《封神演义》第12回“陈塘关哪吒出世”中第一次正式出场。哪吒出世及成长的整体环境为纣王无道,天下大乱。而哪吒出世的节点也有具体的危机:纣王失政,逼反天下四百诸侯,生民涂炭。因此,哪吒的父亲背负着守关和平反的重任,可见家庭所处环境之混乱;而作为儿子的哪吒的出生“吉凶难料”,似乎与这场混乱和危机相呼应。
基拉尔曾论述道,“社会存在着一种异常……社会的‘平均数被认定为社会的‘正常。从社会最正常的位置偏离越远,受迫害的危险越大”。所以,“异常”是社会选择替罪羊的首要标准[8]。而哪吒的“异常”不是后来产生的,而是一开始就被标记好的命运,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大部分替罪羊形象共有的属性。
哪吒尚为胚胎时就是异类。“殷夫人后又怀孕在身,已及三年零六个月,尚不生产。李靖时常心下忧疑……”此时,哪吒已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特点,也在无形中遭到家人的排斥。这样,哪吒个人的异常属性不仅属于个人,还扩散到整个家庭,带来混乱。哪吒作为“灵珠子化身,神圣下世”,来做“姜子牙的先行官”,某种意义上并非出于个人意志。太乙真人于哪吒出生前夜托梦给李夫人,在次日上门道喜时先假装不知,亲口告诉李靖“此子生于丑时,正犯了一千七百杀戒”。作为凶时出世、身负不定命运的将军之子,家庭却并未为他提供适当的教育,让他免于走上之后的道路。可见,从儿童成长的角度来说,哪吒的父母、师父等是缺位的,因此文本里的哪吒一直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对社会准则和道德缺乏清晰的认知。这种道德上的混沌则构成他隐藏的第二重“异常”属性。
2 替罪羊哪吒受迫害的过程
基拉尔论及替罪羊机制时,指出替罪羊具备的双重属性,即罪恶性与神圣性。在迫害者看来,替罪羊一方面能造成社会危机,另一方面又能平息社会危机。这一特性在哪吒受迫害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哪吒的诞生当然是神圣的,他本身就是神圣之物的转世,注定要成为封神榜中的神、姜子牙座下的大将,塑成金身后成为伐纣立周、平乱安民的大功臣。他出生时“一团红气,满屋异香”,太乙真人托梦迎接他的出世。哪吒天生神力,形貌异常,而且能使用神仙所用的兵器。哪吒的能力和外貌似乎并不源于父母,而是源于他的身份。这为他后续受到迫害的情节作了铺垫。如上文所述,哪吒虽然拥有超越常人的天赋,却并没有接受配套的教育,这是对他无形的放纵,也是社会准则从未接受他的表现。除了出生时在家庭内部引发的焦急和混乱,他第一次外部恶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自己能力的无知和失控。天气炎热,儿童下水嬉戏实属正常,但哪吒身怀异宝,混天绫“摆一摆江河晃动,摇一摇乾坤震撼”,陈塘关和东海龙宫就此结下深仇。
龙王来到陈塘关质问李靖,李靖找到哪吒询问情况,而哪吒坦诚相告,正证明了这一点。在迫害的初期,哪吒并不觉得自己“有罪”。“三子七岁,大门不出”,表明哪吒并没有被给予合适的对外身份。
第二次恶行基本与此同构。敖光为报儿子之仇不得不去天界陈情,而李氏父子正在家中烦恼。为避免触怒李靖,母亲让哪吒独自一人去后院,没想到院中又有“陈塘关镇关之宝,乾坤弓、震天箭,自从轩辕黄帝大破蚩尤传留至今,并无人拿得起来”。面对这种上古神兵,哪吒想起师父说自己会成为姜子牙先行官,就突然生出提前操练的想法,进而搭弓射箭,一箭射死石矶娘娘门下的童子。这实际上是无可避免的混沌之恶,是异常之力不加管束的自然结果,自然会引起混乱。
在神明眼里,哪吒的出生和成长只是他获得身份的过程,最终目的是通过考验肉身成圣,为伐纣立功。哪吒的不教养招致自身的不幸,同时是群体性混乱的原因。而深层原因是神对人个体生命的蔑视。在整个文本所构建的社会背景中,人类与替罪羊都只是天意显灵的工具,而替罪羊则承担着所谓的“民意”。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牺牲成为必要且合理的选择,而对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说,迫害就这样层层传递。
3 替罪羊哪吒身份生成特点与迫害结果
正如上文所述,文本中存在神对人个体生命的蔑视。神明的最终目的是掌控天下发展的轨迹,因此在社会陷入混乱时需要选出其在人间的代言人,这类人处于人与神的边界。他们身份模糊,对于其所处的人类社会而言是异类,不能融入。同时他们又身怀神所赋予的特殊能力,适合被确立为讨伐最终替罪羊、对其实行制裁的代表。文本中所呈现的能力与法力,实质上是人的构想,是群体對不同寻常、能救人民于水火的英雄的普遍期待。这就意味着哪吒异于常人的特征正是迫害者欲望的具象化表征。
同时,哪吒又并非普通的人类英雄。从起因来看,他是神圣之物的转世,并非完全属于人类,他从未被人类社会所接纳。因此,他是可以复活的,他所受到的暴力行为对其生命自然没有不可挽回的影响。从过程来看,哪吒并非人类,作为迫害者的群体赋予了他超乎常人的能力,同时具象化超乎常人的惩罚,让他能够承担的暴力结果更具戏剧性,也使神圣化转化更有说服力。从结果来看,选取一个非人类对象作为替罪羊,一定程度上似乎减少了人的牺牲,进一步削弱迫害者的罪恶感。从对人的暴力转向对非人的暴力,文本展现了人类思维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自私,也为替罪羊机制中暗含的暴力思维给予了又一重掩护。在《封神演义》中,这样的手法并不少见,而哪吒形象的构建更是其中的典型。
在替罪羊的所有版本中,替代物都具有典型的净化功能,通过对其驱逐或杀害,可平息上天或神的怒气,避免灾难降临。从个体角度看,这些人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作为一个最终命运相似的群体,他们代表着一种平缓冲突的力量[9]。文本暗含对哪吒“一人做事一人当”行为的肯定与鼓励,这正强化了“替罪羊”模式背后的集体无意识。在这一环节,他人的失职、规则的不完善不再被追究,混乱通过个体牺牲得到解决,逐渐强化群体对仪式内在的信仰。
哪吒的受迫害过程并不终止于他为了平息龙王的愤怒,解救陈塘关于水火之中而自尽的行为。李靖将哪吒的庙宇烧毁,正揭示了其遭受的迫害并未结束,哪吒的使命没有完成,身份无法被承认。而他需要参与灭商伐纣,擒妲己杀纣王,才能获得名义上的认可,呈现出层层递进的特征。文本将一切迫害行为与结果书写为“命该如此”,将暴力的缘由交给超验的形而上,如此可以省略对其必然性的解释。因此,《封神演义》中的哪吒故事既符合基拉尔的替罪羊范式,又为其内涵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延展与阐释提供了更多可能。
4 结语
神话的表面叙述各不相同,但其深层结构具有一致性,而对其进行结构与机制的分析,为人类反观民族与人类的思维逻辑、认知机制提供了可能。替罪羊机制的研究因此具有跨学科与跨文化的意义。哪吒的形象具有天然的替罪羊属性,其身份的产生与群体的社会心理机制有关。当群体陷入危机与混乱,就需要少数人或者个体为之接受惩罚、承担责任。《封神演义》中替罪羊受迫害过程中身份的生成特点,从身份的生成和身份的递进两个方面体现了成熟文明中神话对于暴力仪式本质的隐藏和秩序生成的过程。而对哪吒形象进行替罪羊范式研究,或许可以启发读者从全新的角度思考其人物形象产生的缘由及其命运背后的深层逻辑,揭示人类跨越时代的思维惯性,也为其形象的改编提供更多结构性的灵感。
参考文献:
[1] 欧阳溢.中国影视文化中的哪吒形象演变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22.
[2] 刘海丽.从文学人类学角度探析《红楼梦》中的仪式[J].学术探索,2007(4):128-132.
[3] 苏勇.多重视角下的《封神演义》[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0-13.
[4] 孙博.吉拉尔替罪羊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典文学文本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21.
[5] 付方彦.哪吒形象流变研究[D].长沙:长沙理工大学,2016.
[6] 成容.跨媒介叙事下哪吒形象的多元形态与重构[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23.
[7] 许仲琳.封神演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2:86-121.
[8] 勒内·基拉尔.替罪羊[M].冯寿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5-35.
[9] 刘国枝.论福克纳小说中的替罪羊群像[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7(4):99-103.
作者简介:胡丹阳(2000—),女,湖北黄冈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20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与希腊的文明起源神话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0SJZDA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