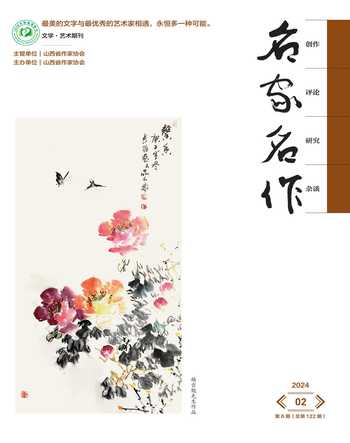论《局外人》的荒诞感与真实性
[摘要] 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中的陌生化角度出发,分析加缪小说《局外人》中“现实社会的荒诞感”和“人物形象在荒诞外壳下的真实感”。其中“现实社会的荒诞感”分别从语言的陌生化、形式的陌生化和关系的陌生化三部分进行分析;“荒诞外壳中人物的真实性”部分论述主人公默尔索在现实困境下呈现的陌生化人物形象的真实意义。
[关 键 词] 《局外人》;加缪;陌生化;荒诞感;真实性
一、浅论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
陌生化理論是什克洛夫斯基首创的,最初作为诗学的概念和雅克布逊提出的“文学性”共同成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两个核心范畴,在俄国形式主义内部产生了广泛影响。什克洛夫斯基强调文艺不是对外部生活的模仿和反映,而是有其自身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文学理论不应只研究文学的外部关系,而应重点研究文学作品本身及文学的内部规律。
陌生化手法打破常见的表现形式,呈现生活之为生活的本真状态,唤起读者最真实的审美感受。在艺术中,为了引人注意而“人为地”创作成这样,使得读者接受过程受到阻碍,达到尽可能紧张的程度和持续很长时间,拓宽读者的审美视野;同时作品为了更好地恢复对生活的感受,不间断地被接受、观察、感受,通过揭露和重建矛盾,在本无区别的素材中重建区别。对陌生化的研究不仅限于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差异,还旨在建立一种能够概括文学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将陌生化理论延伸到叙事领域中去,即叙事手法陌生化问题,这是用技巧或者手法取消语言及文本经验的“先行性”,创造出“复杂化”和“难化”的过程,进而割裂传统经验给予阅读主体的审美期待,促使阅读主体以全新的视角去审视文本的内涵。
二、陌生化手法下现实社会的荒诞感
(一)语言的陌生化——短句的使用以及缺乏常规逻辑
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任何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都在处理各种语言问题。作家在借助语言同读者交流时又深刻地感受到语言带来的束缚,正如詹姆逊所说的“语言的牢笼”。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指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古代文论对作家语言困境的最好诠释。作家处于这种“语言的牢笼”之中,必须有意识地突破语言的便捷,以表达自己的独特感受,他们要做的是“用语言挑战语言”,这意味着作家要不断尝试用陌生化语言来突破日常语言的边界,进入一个崭新的审美境界。
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语言是实现陌生化过程的重要保证与条件,艺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陌生化。更有学者认为,真正的文学语言就是陌生化的语言。陌生化理论在语言上的运用就是要通过语言使情节陌生化,并创造与众不同的手法使作品的呈现更具吸引力,使读者产生阻滞感。正如该范畴的理论内涵所呈现的特质——创造性。
《局外人》这部小说中语言的运用包括大量短句的使用、句法缺乏逻辑性以及语言的反复性等。小说基本上没有出现过长难句和复杂的语法结构,而是经常有这样一些短句“这与我无关”“我无所谓”“怎么都可以”。这样短小精悍的句子,在文中占据重要地位,理解也没有难度,可是当它们在文中反复出现且并不合时宜时,就会使读者不得不注意它们在小说里独特的意味,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不得不对语言本身加以怀疑,力图层层揭开语言背后的真相。从陌生到理解,又从理解到困惑,收获了不一样的“新”的体验,这无疑是加缪将陌生化应用在语言上的成功之处。
小说中语言缺乏逻辑性也是陌生化手法运用的表现。故事的叙述具有较大随意性,故事情节似乎是随手拈来,句子顺序毫无逻辑性可言,进而导致情节缺乏逻辑性。因此“要想让故事给读者以荒诞的感觉,达到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打破传统的叙事逻辑性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叙事一旦失去了逻辑性,就会带领读者领会到荒诞性,进入不曾预料的世界,这是对传统叙事结构的有力背叛。加缪刻意打破了小说语言的逻辑性和连贯性,让叙事不以时间的先后顺序展开,也没有围绕一个中心点有条理地来叙述,情节的发展仅仅是随着主人公的思绪游走。
(二)形式的陌生化——荒诞与虚无
形式主义原本指的是一种只看事物的表象而对其本质的思想方法或者工作作风不加分析。在《局外人》这部小说中,形式的荒诞性与虚无感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母亲下葬的形式才能证明母亲死亡的事实,二是社会把追求形式作为判罪的关键。
社会性死亡才能宣告这个人真正的死亡。小说的第一部第一章在叙述母亲葬礼的情节中向读者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要等到母亲葬礼结束母亲死亡这件事情才算确实发生。在母亲葬礼准备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丝不苟而烦琐的程序、形式,形式的重要性甚至压倒了事实的确切性,这种观念的桎梏显示了其形式的荒诞性。
真正的默尔索在小说中是其他人物难以理解的、无法言说的,是社会公理规训所不能理解和容忍的。社会规训和默尔索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隔膜,前者作为社会公理的代表竭力以生命形式的存在以及表现为关键:默尔索在母亲的葬礼上到底有没有哭?默尔索在母亲的停尸房有没有喝咖啡、抽烟?葬礼之后默尔索有没有和他的女朋友玛丽游泳、看喜剧电影和做爱?后者把追求生命个体的真实性和存在性作为真谛,默尔索希望律师理解他对诚实原则的遵守,对个人逻辑和存在方式的理解,他希望得到的是自然而然、通情达理的辩护。但社会中的其他个体不能容忍作为感性的爱没有以一种具象的形式出现在社会场面,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惯性地认为没有带上社会规训外壳的人是应该被驱逐出人类群体。默尔索被判处死刑不仅是因为默尔索开枪杀了人,而是对默尔索不遵守形式的惩罚。
这种形式的荒诞性已经入侵了现实生活的角落,而加缪的伟大之处,就是将这种习以为常的事物以巧妙的陌生化手法表达出来。什克洛夫斯基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习以为常”会忽视很多美丽的“遇见”。作家的创作需要打破人们欣赏的习惯,打破日常思维表现被遮蔽的真实生活、观察、感受,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在本无区别的素材中重建区别,进而达到陌生化的效果。
(三)关系的陌生化——个体关系的荒诞感以及关系的转换
如果把主人公默尔索当作一个圆心,那么可以把他的人际关系辐射为养老院院长、门房、贝莱兹、女朋友玛丽、默尔索的老板、同事埃马努埃尔、小混混雷蒙、雷蒙的朋友马松、邻居养狗老人萨拉玛诺、餐馆老板塞莱斯特等。小说中主人公默尔索和其他人的交流显示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的一种真实显现,但在加缪的笔下却显示出一种荒诞感。
小说中的人物尽管相识,可是又好像没有真正了解彼此,每个人都是彼此的“局外人”。在加缪的笔下,人们不得不相互关心,为了利益或者约定俗成和社会规训成为朋友或者同盟,愚昧地遵循着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局外感”导致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也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局外感”,而这种隔阂是超越文本获得现实关照的真实状态,让读者在文本的荒诞感中寻找到现实层面的熟悉感。这是陌生化手法喚醒读者潜意识接受习惯的表现,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和震撼力。
默尔索是一个现代社会的“误入者”,遵循自己的天然逻辑,从自我的生理经验出发,表里如一地陈述自我的真实感受。在所谓的“社会规训”推导中,它们全部被遮蔽掉了,甚至因此成为将默尔索送上断头台的铁证。他一系列再平常不过的生活感受被观念、习俗的体系特别挑选出来,并被精心编织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犯罪神话。这所有的一切,都与被规训、被社会异化的“其他人物”所区别开。默尔索与他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是彼此的局外人。加缪不仅写出了其他人物对默尔索的“局外感”,还表达出默尔索不被理解的“局外感”,这种人与人之间无法相互理解的深厚隔膜,是小说关系荒诞性的重要体现。
法庭上关系的颠倒是关系荒诞性的集中体现,审判和法律理性的消解在默尔索遵循的诚实的原则中产生了,默尔索从审判者的中心形象成为“局外人”。当默尔索再次重申母亲下葬的场景,诚实地表示没有对在母亲葬礼上流泪时,检察官想当然地认为默尔索是一个冷漠的人,以至于默尔索在守夜时抽烟、喝咖啡都成了他们眼中的道德沦丧,成为故意杀人的佐证。审判庭上的中心人物、杀人嫌疑犯默尔索在法理消解的情况下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成了“局外人”,凭别人发落自己的命运。
加缪在文本层面解构了日常生活的惯性,揭露了社会关系中个体与整体的矛盾,体现了社会惯例对个人自然感受的打压。加缪以陌生化手法写出了这种约定俗成中的不合理部分,是对惯常表现形式的讽刺和否定。在创造“复杂化”的过程中默尔索的种种行为以一种非晦涩的语言呈现,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却极容易对此感到不解。当读者跳出文本时,会发现自己容易成为现实生活中“其他人物”的翻版,这也是读者在审视、观照自己和默尔索的关系,因此读者在阅读接受的过程中,会获得对社会认知新的理解和审美感受。
三、陌生化手法下人物形象在荒诞外壳下的真实感
陌生化手法在叙事层面上对人物形象的运用指的是通过将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变形和扭曲,不直接向读者展示清晰的人物角色和性格特征,让读者始终不能完整地把握人物的具体肖像、性格和体征等,只是靠感觉把握人物的特点。这种阻滞隔阂的陌生化书写诱发了对主人公人物形象的玩味和揣摩,小说表面的荒诞性和通过人物形象展现出的真实性,让文本充满了张力,进而引发对《局外人》主题的思考。笔者认为默尔索的人物形象的独特性背后有其积极意义,下面就默尔索所处的困境论述其人物形象的真实性。
(一)温和得近乎透明的静穆
加缪在为美国版《局外人》写的序言中写道:“他远非麻木,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作者看来重要的是能在世界与自我的复杂的关系中找到灵魂与心灵的自由和生命的力量。默尔索个人式的生存理念显示了对传统社会主流观念的叛逆,默尔索作为一个被误读的正常人,善良温和,热爱自然,真实坦率,不虚伪做作,能够同情他人,是具体、生动和独特的存在,他的性格是用来描述希腊雕塑的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也许在世俗的无意识的对立下,默尔索的表现就像一个与世俗脱离的局外人,但这是默尔索不虚伪做作的内心的真实呈现。面对朋友和朋友妻子的款待,默尔索并不作出客套的表现,而是大方地接受了朋友的热情,当他面对朋友雷蒙和阿拉伯人的冲突,则是给出了中肯的意见;在马松家,他面对家庭的温暖怦然心动,产生了结婚的念头,通过这些行为很难承认他是一个极致冷漠的人。习惯道谢这一行为或许让人感觉默尔索已经被社会深深规训了的错觉,遇到人就想握手、道谢,显然是被社会规训之后的结果,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惯性。但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这恰好证明默尔索本质上是一个温和良善的人,这种妥协是默尔索善良本性的一种呈现。他从来不大张旗鼓地与世界抵抗,大多数时间是安静地接受这个世界的某些不合理性,他站在自我与社会中间。
默尔索几乎不使用任何感情色彩去渲染所发生的事情,而是诚实地还原眼中的世界,他对所有涉及自己的处境与将来需要斟酌的事务,都采取了超脱淡然的态度;在面临抉择的时候,经常讲同一类口头语:“对我都一样”“我怎么都行”。他温和得近乎透明,总是沉默着、顺从着,在无可奈何的社会中寻找一个适合生活的点。默尔索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产生了一种握手言和的冲动,这是他内心善良底色的体现。他孤独而独特地温和着、静穆着,从不要求自己具有某种个性,相反,他总是认为自己和他人一样。
(二)感受的细腻与性的坦诚
一方面,默尔索感触敏锐、洞察灵敏,对事物有非凡的观察能力。他的目光像个摄像头,镜头所指每一帧都没有浪费。在默尔索的第一人称叙述下,出场了许多没有面目重复的人物,小气的老板、絮叨的门房、没有鼻子的护士、看电影的一家三口、阳刚男人雷索、养狗的老头……每个人都极富个性色彩。他对周遭世界的观察细致入微,他甚至可以注意到公用的转动毛巾被大家用一天已经全湿透了的现象,诸如此类。
默尔索的观察细腻、叙述精确,在他的注视之下,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深刻的被触动的温和,无论是周末的街道,还是夏日的海边,甚至是送殡的场景,都给我一种沉静的温柔。在默尔索眼里生活是生机勃勃的,人的状态是丰富且不断变化的,这种细腻的感受超过了绝大多数浑浑噩噩的世人。
另一方面,默尔索不怯于谈人真实的欲望,小说用了大量的笔墨书写两性之间动物性的“腥味”。默尔索和《红与黑》中于连为得到德瑞纳夫人的“英雄主义”不同,与《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伪浪漫主义”不同,默尔索的情欲是真实而不加伪饰的,没有英雄主义或者浪漫主义的外衣,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人的动物性是绝对不能因文学的“文艺”而不描写的,显然,加缪遵循了这个原则。
(三)反抗意识的爆发与面对死亡的释然
默尔索作为一个生活边缘人,在社会上寻找自我生存和社会规则的平衡点,但最终因为一场枪杀,和社会共同情感中不相符合的那部分被公之于众。默尔索不理解自己的生存方式和逻辑思维为什么会成为他被判处死刑的关键,又或者他明白,只是不想再虚伪地为此妥协,转向坚持自己内心的诚实。他作为“局外人”,在最终确认“存在”的必要时刻,所有被排斥的情感回光返照一般汹涌澎湃,在狱窗后的星辰下迸发。在临死前,默尔索觉得他第一次真正对世界敞开了胸怀。
当默尔索被判处斩首后,神父来到监狱对他进行告诫,这是我们看到他唯一一次爆发,他终于把对世界压抑已久的不满倾泻了出来。这时候的默尔索把从不理解宗教乃至社会的虚伪的愤懑倾泻而出,一种彻悟和反抗意识占据了默尔索的大脑和心灵。他不是在骂神父,而是痛斥所有让他眩晕厌烦却如影随形紧紧缠住他不放的虚伪。默尔索求生的愿望、刑前的绝望、对司法不公正的愤愤不平、对死亡的达观与无奈、对宗教谎言的轻蔑、对眼前这位神父的厌烦以及长久监禁生活所郁积起来的焦躁聚合在一起,不再苦苦压抑来应付虚伪的世界,让读者人得以看到他平时那冷漠的“地壳”下面即将喷发的状态,而这也正是默尔索对母亲去世的理解——不是痛苦,而是新生的希望。
默爾索期望世人都对他在母亲葬礼上不哭的行为进行强烈谴责,向世人宣告这是大错特错的傻瓜行为,希望世人对世俗规训的主观性强于法律规则性、严密性,公理对个性压制的愚蠢行为进行一种热烈赞颂。实际上这是一切破碎后的不屑的无奈和嘲讽,就像是鲁迅先生的那篇《复仇》,那裸着肌肤站在广漠的旷野上的两人,就好像是怀着幸福感走向死刑场的默尔索,而涌聚在两人四周的路人,则是默尔索期待的看客。
在规则长期的制约下,人们的精神会形成一种增生,与规则成为同一块血肉,变成不懂得思考的、盲目的“看客”,尽管他们本来是完全独立的个体。默尔索被判处斩首之后,他才全然从这一场全人类参与的迷局当中获得解脱,意识到生命存在的本身。他在这个过程中见证了一个新我的诞生,而这个新我就是一个全新的更高层面上的“局外人”。荒诞意味着不承认任何预设的价值,因为世界的冷漠,以死亡为代表的终极的冷漠,让个体得到了为所欲为的自由,最终趋向自我的真实。默尔索感觉到的一种幸福,那是一种终于戳穿了虚假的幻觉之后认清了现实的幸福。尽管陌生化的手法模糊了默尔索的人物形象,但是在语言的阻滞中我们却可以解读出最终指向“人”本身的这一更加清晰的真谛。
四、结束语
陌生化理论是展现小说《局外人》荒诞性和真实感的重要表现手法,它将文学作品中的世界和既存的现实世界割裂开来,在两者之间划出了一条鸿沟,这条鸿沟就是陌生化打造出来的变形了的艺术空间,我们可以从这个具有表现性的艺术空间中汲取现实生活无法带给我们的审美汁液,也正是加缪对陌生化的大胆运用,我们才可以解读出小说的荒诞感以及从中透露出的人物真实性。
参考文献:
[1]董钰.论加缪的怪诞身体书写:以小说《局外人》《鼠疫》为例[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4(2):219-226.
[2]柳鸣九.《局外人》的社会现实内涵与人性内涵[J].当代外国文学, 2002(1):90-97.
[3]陆晓芳.“毫无英雄的姿态,接受为真理而死”:解读阿尔贝·加缪《局外人》中的默而索[J].山东社会科学, 2012(2):79-83.
[4]宣庆坤.竭尽此生就是幸福:加缪《局外人》的哲学解读[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5,23(5):10-13.
作者简介:
明瑜凡(2002—),女,汉族,山东济南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外国文学、文学理论。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