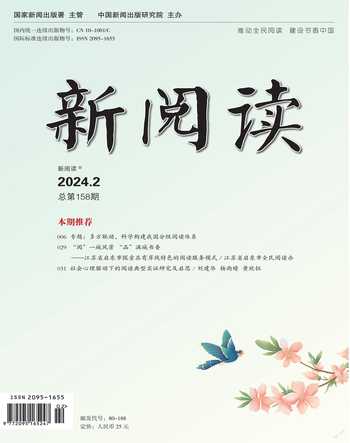重读残雪:绘画颗粒、心理变形与意识星云
谢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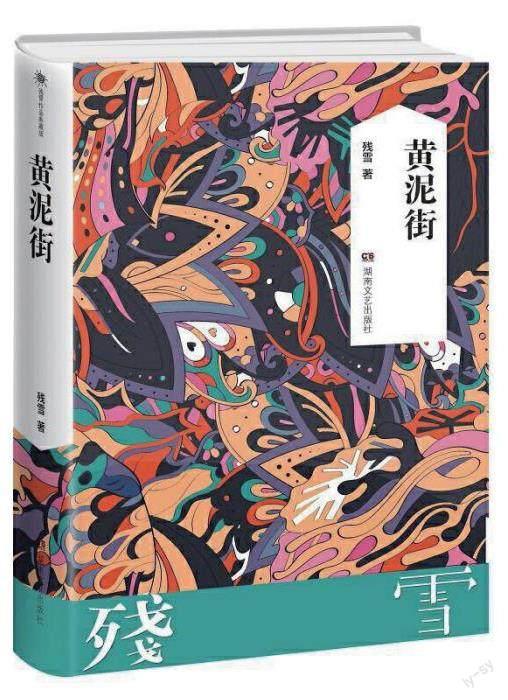
初读残雪的读者,往往有一种步入陌生暗夜的体验,模糊的人物,莫名的对话,无端而来的动物和陌生人,永远不能明晰但始终也不曾断裂的叙事逻辑……这种景象令人不解,但更不舍就此抛弃。就像欣赏浅海里的海藻摇曳,光线的变化与海水的暗涌,共同构成海藻的动态形色,迷恋于此,又何须深究?文学实验走到残雪这里,用文学去解释文学往往会力不从心,这也是残雪小说面向大众释读的艰难之处,至少得有阅读卡夫卡的基础,用其他艺术门类来说明残雪的小说反而相对容易些。
朦胧质感源自颗粒
现代绘画艺术和现代小说艺术的进程总有奇妙的呼应之处。古典浪漫主义绘画和古典浪漫主义文学本质上是一样的,基于透视法的色彩和线条,对小说家和画家是一样的创作法则。雨果笔下的巴黎和德拉克罗瓦画板上的巴黎都有合适的比例。当印象派抓住了颗粒的奥秘后,艺术的写实基础颠覆了——颗粒带来的朦胧质感,不但合乎色彩在空气中的呈现,也更适合受众微妙的心理。颗粒才是图像的本质,这一点在数字时代终于得到了科学的背书。
几乎与塞尚、莫奈同时,普鲁斯特横空出世,他找到了人类内心的颗粒,那就是意识的碎片、意识颗粒组成了色块,色块组成了图案……因为细分到了颗粒,记忆之海变得无穷无尽。当普鲁斯特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陶醉于彩窗上的光斑移动时,他欣喜地看到了时光的谜底,开始用意识颗粒来建造内心的大教堂,于是意识流得以创生。
线性的叙事进程在文学里第一次被弃置到无所谓的地步,取而代之的是意识无尽的颗粒,它们旋转、黏合、分离,制造了全新的文学梦幻。
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毕加索和卡夫卡两位同时代的巨人,再一次呼应了绘画与小说的历史进程,他们共同的创造是抛弃了“求真”这一执念,艺术家成为艺术世界中唯一的法则——他们用个人对世界的感受来为艺术立法,他们对自己的灵感有独断的处置权。
非等比变形法则
就这样,现在统一称为“现代派”的变形艺术完成了断代,完全失真的人形,荒诞为甲虫的小人物这类形象尽管远离了客观的真实,却更接近于人类心理上的真实,因为他们能把恐惧、压抑、愤怒、抗争等感受提高到极致。
这是魔术般的艺术心法,同时也有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为他们做出了理论解释:在物质世界和人的感知世界里,存在着一片广袤无垠的心理反射空间,这一空间正是艺术奥秘诞生之地,是艺术家用武之地。这一论断极大地提升了艺术的地位,也赋予艺术家以自我为核心的创作权力。
在明了这些艺术进程之后,我们不但能够更轻松地欣赏残雪的小说艺术,也可以推论她的创作在文学史上将居于何等的地位。如果说卡夫卡是将世界做了缩小变形,变形为一只甲虫的话,那么残雪则是突破了等比例的变形法则,她可以在同一部小说里采取多种比例去变形。她的变形比例是可以随时放大缩小的,无论物体的比例和心理的比例都是如此,更类似于章鱼似的随机变形。
老翁转过脸去弄他那只手表,手表戴在他的右手上,这居然听得到指针移动发出的金属声——这只表实在大得不像话。他将右手举到眼前时,我看见表壳底下有一只细小的蟑螂在来回奔跑,这景象令我产生眩晕的感觉。(《莲》)
墙壁上有一个杨处长的影子,那影子在一点一点长大。一会儿工夫,那黑影就占满了一面墙,头部延伸到了天花板上。(《莲》)
这是残雪在同一部小说里的变形魔术,同时采用了宏观比例和微观比例,将她的创作潜力放大到了极致。对于这样的小说,读者需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才能欣赏。既无须思考蟑螂为何出现在手表里,或者蟑螂在隐喻着什么,也不要去做实验,看看人的影子蔓延到天花板上到底会怎么样——我们需要的是感受人物内心一点点积累的疑惑、不安、惊惧等情绪,陷入紧张的愉悦中,这像极了我们某个被遗忘在街头的童年时刻,可以唤起久违的陌生世界和全新的人生视角。
重要的不是你在物理层面上看见了什么,而是在心理层面上看见了什么。无论作为创作者还是读者,人人都有视而不见的权利,也有对目标做心理加工的权利。
在其描述中,那个老头仅仅是“我”的邻座而已,却和熟人一样洞悉“我”的心理。残雪的小说充斥了这类无由而来又无由消失的面孔和场景,他们往往令“我”产生出无边的弃置和恐慌感。在地板上盛放的玫瑰,紧盯你不放的鹰,墙壁后面的另一个世界——他们唯一的共同特征是绝非科幻,而是日常生活里的寻常,只是他们都会换了一种古怪的时机和场合出现,用最熟悉的东西组合为最陌生而惊骇的感受。
他用如炬的目光盯着我的掌心,我跟着他看去,立刻就发现我的手掌变透明了,有细小的黑色鱼苗在掌心与手背之间活动,我感到指尖一阵阵发麻。(《美人》)
这又是一个陌生人引导出的场景,手掌、透明、鱼苗,这三种熟悉的感受换了一种方式去组合,制造出前所未有的惊奇。残雪对创新的追求执着到小说的每一句,既然弗里达画作可以让人物生长藤蔓,那么作为小说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一个人的意识星云
用熟悉的事物去创新,这可以使变形的世界亲切可见,不至于落入抽象的陷阱,她比前人更彻底地摆脱了“求真”的偏执,这是她为艺术的独立性所做出的伟大辩护。
意识永远是无真也无假的存在,意识只能用意识来解答自身,别指望用其他的手段。阅读残雪就是在阅读人类透明的意识,阅读她用文学去探索人类意识之谜的神奇。在意识这个问题上,艺术似乎总比科学更有发言权。人的意识到底是什么?为何白昼是理性、是观念、是目的和欲望,意识是有结构和层次的,也是线性发展的。为何到了夜晚就是恍惚的、梦幻的?为何梦境会是分裂的、疏离的、陌生的、有时候是流动的,带领你去白昼未完的欲望,有时候又是爆炸式的,无理性的瞬时点燃一个前所未见的场景,意识为何是没有规律的像素组合?
带着这个问题去读小说,远比读科普有趣,当弗洛伊德用心理分析向所有的梦境强行溯源,小说家们却用自己的真实体验说不。残雪的拒绝分析、拒绝求解在当代作家中是做得最坚决的——她宁愿独面这个庞大而无底的深渊,也不肯轻易地使用任何现成的答案。
残雪的变形大法是超前的,她用长达半个世纪的努力聚拢最多的空间、人物、场景,色块、声音,这意识的宏伟建造和星云一样变幻迷人,出版的二十余部小说实际上是同一部小说,是以她名字命名的这片意识星云。
这是同一条道路上后來者的荣幸,但获取这种荣幸却需要超凡的勇气和执行力,甘于去享受远居偏隅的孤独,远离圈子的自由。
她在小说集的自序中写道:“因为你必须‘心死,必须有长年累月囚禁自己的毅力,你的精神才不会迸散,身体才不会懈怠……让那些孤独的心灵更有信心,也使他们更有勇气地投入这种匪夷所思的操练。”
尽管这样的孤独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但在这个时代,独行者面对的舒适和名利的诱惑,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多,能够理解这一点的读者,也会更多。
作者单位: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产业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