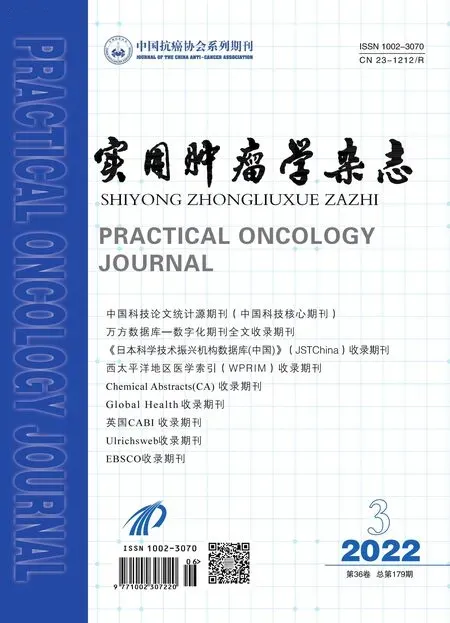肝癌共病抑郁分子机制的研究进展
唐如冰 王琪 综述 游雪梅,3 审校
肝癌作为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早期诊断率低、恶性程度高和术后复发率高的特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癌症研究署(IARC)最新公布的全球肿瘤流行病学统计数据——GLOBOCAN 2020,中国肝癌的发病例数占全球45.3%,死亡例数占全球47.1%[1]。肝癌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也使患者承受了沉重的心理压力。调查研究发现肝癌患者常伴有较高的抑郁发生率。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其主要的临床表现为持续的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甚至出现睡眠障碍和自杀念头等[2]。近年来,基于对抑郁神经生物学以及肝癌病理生理学研究的深入,发现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某些共同的生物行为机制。流行病学调查为肝癌共病抑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进一步对两者共病的分子机制进行研究和归纳,能够为其诊断和治疗提供新思路。本文将对肝癌共病抑郁的临床研究概况以及分子机制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肝癌与抑郁的临床研究概况
一项针对中国癌症患者的调查研究显示,肝癌患者抑郁患病率为68.42%[3]。在肝癌患者中的研究亦显示,抑郁的患病率分别为64.4%和65.6%,且患者的抑郁情绪与年龄、社会支持、经济状况、疼痛分级相关[4-5]。由于在不同的研究中评估方式或使用的量表不同等原因,导致对肿瘤患者抑郁发病率的调查结果有所出入,但总体来看,抑郁在肝癌患者中的发病率较其他肿瘤患者更高,可能与肝癌早期诊断率低、恶性程度高有关。同时,抑郁也是导致肝癌患者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之一。研究显示,伴有抑郁的肝癌患者生存率明显低于非抑郁的肝癌患者,且抑郁程度与无病生存率相关[4,6]。一方面,当肝癌患者伴有抑郁等精神障碍时,患者生活质量较差,寻求治疗的意愿更弱,治疗依从性更差;另一方面,抑郁作为肝癌的危险因素,可能通过免疫抑制等方式增加肝癌不良预后的风险。
癌症神经生物学的兴起使人们对心理因素在肿瘤进展过程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肿瘤本身作为一种心理应激因素常常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恐惧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同时患者的心理特征、情绪障碍和生活习惯等也会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阐明肝癌和抑郁之间的关系,但是绝不能简单地将罹患肝癌的患者出现抑郁情绪看作是单纯的应激反应,从而忽视抑郁发病的生物机制在肝癌进展中的影响以及肝癌生物环境对抑郁发病所起到的作用,促进肝癌进展的生物环境极有可能在分子水平上导致抑郁的发生,抑郁亦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影响肝癌的进展和预后。
2 肝癌共病抑郁的分子机制
2.1 自主神经功能紊乱
自主神经系统包括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在正常或应激条件下,具有维持机体内稳态的重要作用。基于对抑郁发生机制的研究,抑郁首先激活的经典神经内分泌系统包括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轴和交感神经系统[7]。抑郁症患者交感神经活动增加,将导致血浆中儿茶酚胺水平升高,并激活肾上腺素能受体[8]。
心理社会因素通过肾上腺素能受体信号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9]。研究者通过建立小鼠模型,证明应激可以显著提高脾脏、血清和肝癌组织中去甲肾上腺素的浓度,激活β-肾上腺素能受体信号,上调脾脏髓样来源抑制性细胞(MDSC)中CXCL2的表达,促进脾髓样细胞进入到肿瘤组织中[10]。MDSC可以通过抑制T细胞、NK细胞、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的活性抑制肿瘤免疫,并通过升高转化生长因子-β、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水平促进肿瘤血管生成,最终导致肝癌的进展[11]。如果将小鼠脾脏切除则可以阻止肝癌组织中髓系细胞的升高,阻断应激所致的部分免疫抑制,抑制小鼠肝癌的生长[11]。另一项研究发现去甲肾上腺素可以激活肝癌免疫微环境中的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HSCs)[12]。HSCs是肝脏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的主要来源,它对肝癌的发生进展和转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3]。升高的去甲肾上腺素通过α1A-ADR信号通路激活HSCs表达,高表达的HSCs进一步通过增强Wnt16B/β-catenin信号的自分泌反馈环而分泌一种癌基因编码的SFRP1蛋白,从而促进肝癌的进展[12]。
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对肝癌共病抑郁患者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抑郁患者交感神经活动增加,去甲肾上腺素浓度升高,肾上腺素能受体激活,进而以通过上调癌基因表达、刺激血管生成以及抑制肿瘤免疫反应等多种途径促进肝癌进展。
2.2 HPA轴功能异常
HPA轴作为神经内分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激活过程中释放的应激激素可以影响多种肿瘤的进展[7]。抑郁患者HPA轴持续激活,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加,可以抑制肝癌患者的免疫功能[14]。NK细胞作为一种具有强力溶解能力的先天性淋巴样细胞,在抵御肿瘤细胞生成的免疫监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慢性不可预知温和应激模型小鼠中,升高的糖皮质激素通过上调肿瘤微环境中NK细胞上PD-1的表达,降低NK细胞的毒性,导致肝癌的进展[15]。
众所周知,癌细胞中促进生长的原癌基因往往发生过表达,而抑制生长的抑癌基因则出现缺失。激活的HPA轴可能通过抑制抑癌基因p53的表达促进肝癌的发生发展。p53可以启动DNA修复、细胞周期停滞、衰老和凋亡,这些都与人体抑制肿瘤形成以及肿瘤对治疗的反应能力有关。通过动物实验研究发现,升高的糖皮质激素通过蛋白激酶SGK1引起p53结合蛋白Mdm2磷酸化,Mdm2从细胞质转入细胞核中,并在细胞核中与p53结合,启动其泛素化及蛋白酶体介导的降解途径,增加p53的降解从而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16]。因此,在肝癌合并抑郁的患者中,HPA轴亢进,糖皮质激素水平升高,导致p53功能受损或缺失可能是抑郁介导肝癌进展的重要通路。
2.3 炎症因子比例失调
细胞因子是由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等分泌的免疫调节信号分子。另一种将抑郁与肝癌进展联系在一起的机制可能是由炎症细胞因子介导的。肝癌细胞与肝癌基质中的HSCs、巨噬细胞和内皮细胞相互作用,可以产生多种炎性因子,这些炎性细胞因子与肿瘤基质环境构成了肝癌炎性微环境[17]。
心理-神经免疫学认为抑郁患者存在免疫系统紊乱,外周髓细胞和脑内小胶质细胞失调,导致中枢以及外周细胞因子释放增加[18]。多项关于健康人群与抑郁患者炎症因子水平的研究提示抑郁患者炎症细胞因子TNF-α、IL-6和IL-1β的浓度更高[19-21]。另一项针对肝癌合并抑郁患者的研究证实抑郁组患者血清TNF-α、IL-6浓度显著高于非抑郁组,且在肝癌抑郁以及复发中具有一定的诊断学价值[6]。IL-6、IL-1β和TNF-α均为促进肿瘤血管生成的关键因子[22-24],可以诱导肝癌细胞发生侵袭转移行为。同时,抑郁也可介导激活肝癌组织中FOX、CXCR4、CXCL13和CD40表达,下调CXCL12表达,调控肿瘤浸润淋巴细胞表型,加剧炎症因子分泌失调,进而减少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浸润,促进肿瘤免疫逃逸,导致不良预后[25]。因此,抑郁可能导致肝癌局部微环境炎性反应加剧,以促进肿瘤细胞增殖、诱导血管生成或抑制免疫反应等方式促进肝癌进展。
另有研究表明,肿瘤发生引起的免疫反应,导致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上调,可能是肿瘤患者抑郁患病率升高的原因[26]。同时,慢性肝炎患者也具有较高的抑郁发病率[27],而流行病学及实验研究证明慢性肝炎是肝癌发病的重要原因。提示了由炎症细胞因子介导的肿瘤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双向的。
2.4 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系统调节异常
5-HT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和血管活性物质,广泛分布在人体全身的组织中。它还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有丝分裂原,具有促进肝脏再生的功能[28]。多项研究表明5-HT与肝癌的进展有关。Soll等[29]通过对肝癌小鼠和168例肝细胞癌患者的组织进行实验研究,证明5-HT通过激活HTR2B导致mTOR的两个下游靶点p70S6K和4E-BP1持续磷酸化,抑制肝细胞癌的自噬,促进肝细胞癌的进展。另有研究报道,N-亚硝基二乙胺诱导的肝癌大鼠及临床患者血清中5-HT的含量随着肝炎—肝硬化—肝癌的进展不断升高[30],小鼠脑干和大脑皮层中5-HT的含量在肝癌细胞增殖期间也显著升高[31]。
“中枢单胺类神经递质功能紊乱学说”认为中枢神经系统5-HT含量及功能异常与抑郁的发生密切相关。抑郁症患者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中吲哚胺2,3-双加氧酶的活性因受到促炎细胞因子的刺激而升高,色氨酸分解速率加快,抑制了色氨酸向5-HT途径的代谢,降低了突触间隙5-HT的浓度,从而诱导了抑郁的发生[32]。选择性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s)可以选择性抑制突触前膜对5-HT的回收,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抗抑郁药物。Zhang等[32]研究发现SSRIs通过阻断Akt/mTOR通路,抑制了肝癌细胞在体外、异种移植以及二乙基亚硝胺/四氯化碳诱导的小鼠原代肝癌模型中的生长。一项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显示,在接受干扰素治疗的丙肝患者中,高剂量的SSRIs与原发性肝癌的风险呈负相关[33]。因此,将SSRIs应用于肝癌合并抑郁患者的治疗中,或许能够为患者带来更多获益。
根据目前的研究显示,5-HT在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中主要体现为突触间隙5-HT浓度过低,而在体外细胞及小鼠实验中以升高的5-HT抑制癌细胞自噬或者促进癌细胞增殖的方式最终导致了肝癌的进展。5-HT系统在抑郁症和肝癌的发生机制中发挥作用时,依赖的受体、转运体和信号转导通路都有所不同,因此,肝脏与大脑中的5-HT如何交互发挥作用,最终影响肝癌进展的详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5 肠道菌群失调
正常情况下,人体内肠道菌群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当肠道菌群出现失调时,例如肠道微生物丰度或组成发生变化,肠道内的生理环境被改变,这种变化将通过各种途径对人体其他组织器官的生理状态产生影响。肠道菌群在精神疾病领域中的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失调和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且这种影响是相互的[34-35]。肠道菌群失调可能通过引起炎症反应、激活HPA轴、改变神经递质水平等方式诱导抑郁的发生[36],抑郁也可能通过连接大脑和胃肠道的迷走神经影响肠道的微生物组成及其免疫功能[37]。
肝脏和肠道在解剖学和功能上密切相关,相互影响。肠道菌群失调也被认为是促进肝癌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38]。因此,“肠道菌群-肠道-脑”轴可能是抑郁与肝癌相关联的重要途径。抑郁患者肠道中有益菌的数量明显降低,革兰阴性杆菌增加,内毒素合成基因过表达[39]。而肠道菌群失调能够导致肠道通透性增加,产生的内毒素将进入体循环,通过门静脉系统转移到肝脏[40]。有研究发现内毒素通过与小鼠肝细胞上的受体TLR4结合,启动LPS/TLR4途径,引起炎症反应,阻止癌细胞凋亡,促进肝癌的发展[41]。
基于以上研究,研究者们提出了关于治疗抑郁和肝脏疾病的新方法。通过服用益生菌以及粪便微生物群移植等治疗方式,促进肠道微生物菌群恢复,降低肠道通透性,从而减少内毒素血症,减轻肝脏炎性环境,延迟或阻止疾病向“慢性肝病-代偿性肝硬化-失代偿性肝硬化-肝癌”的疾病轨迹发展[42-43]。另有证据表明益生菌在肝癌和抑郁患者的治疗中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44]。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针对肝癌共病抑郁的临床研究,以肠道菌群失调为切入点,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
2.6 氧化应激反应
氧化应激指机体“氧化-抗氧化系统”失衡,活性氧物质浓度升高,导致细胞和组织损伤。氧化应激和抗氧化防御系统之间的失衡被认为是抑郁发病的重要原因。抑郁患者大脑及外周血中的主要抗氧化剂谷胱甘肽以及某些非酶类抗氧化物水平下降,诱发促炎症通路的激活和其他凋亡介质(如Caspase-3)活性增加,导致神经元死亡[45]。
氧化应激也与肝脏疾病的发生有关。据报道,氧化应激可以通过刺激巨噬细胞活化、诱导DNA损伤等途径,引发肝细胞坏死以及肝组织炎症,最终导致癌症的发生发展[46]。此外,氧化应激可以激活多种转录因子,导致超过500种基因的表达,其中包括生长因子、趋化因子、细胞周期调节分子等相关基因,而这些因子与癌细胞增殖、存活和迁移能力密切相关[47],提示了氧化应激可能会通过其他通路影响肝癌的进展和转归。抑郁症与肝癌的发生均涉及到氧化应激反应,这为两种疾病共病的中间“媒介”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其三者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3 小结与展望
肝癌与抑郁之间密切相关,二者可能通过多种途径产生联系,相互影响(图1)。深入了解肝癌共病抑郁的分子机制,能够为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潜在靶点,为患者复发及预后的预测提供新思路。本文从自主神经功能紊乱、HPA轴功能异常、炎症因子比例失调、5-HT系统调节异常、肠道菌群失调和氧化应激反应六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期能够勾勒出肝癌和抑郁之间相互影响的生物学通路的大致轮廓,但肿瘤以及抑郁本身发病机制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了我们理解的难度,导致我们对两者共病的机制仍然知之甚少,未来仍然需要对肝癌共病抑郁的发病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及验证。

图1 肝癌共病抑郁的分子生物学通路Figure 1 Molecular biological pathways of comorbid liver cancer and de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