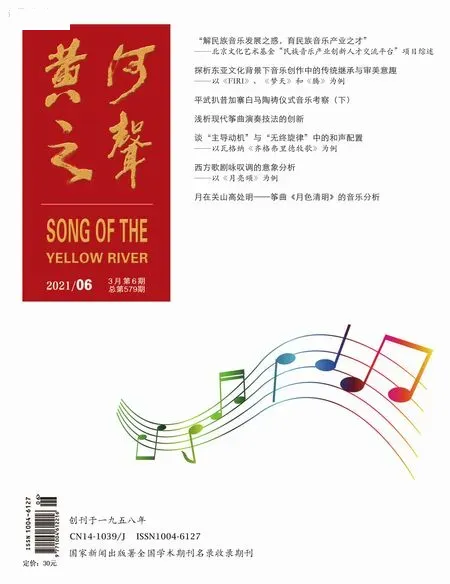二度创作及其演绎对于指挥民族交响乐作品进行的重要性
——以姜莹《丝绸之路》为例
郭立信/王鹤/杨千禧龙
一、何为二度创作
在音乐领域中,“创作”一词是指音乐家或者作曲家将自己脑中的情绪或某种思想抒发出来,以乐谱的形式记录在纸张上的一种行为,简而言之,也就是作曲家编创曲谱的过程①,即所谓“一度创作”;英国著名指挥家亨利·伍德曾在他的《论指挥》一书中写道:“音乐是写下来的没有生命的音符,需要通过表演来给予它生命。”而二度创作相比一度创作而言,其主要的区别则在于其发起人,二度创作的发起者是拥有一定能力将作曲家的作品演绎出来的演奏家等(如钢琴家、声乐演唱者、指挥等),故而音乐表演其实就是对一度作品进行二度创作的结果。②如果在作品的演绎中缺乏二度创作这一过程,那么整个作品将会十分生硬且千篇一律。要知道,音乐作品之所以从其诞生始直至当代经久不衰,二度创作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且在不同的演奏者手中创造出来的同一首乐曲可能大不相同,在文学中尚有“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更何况在不同的音乐演奏者眼中呢?在本文中,笔者将以姜莹女士的作品《丝绸之路》为例,以其作品的曲式脉络为基础,逐步对其段落进行分析。
二、《丝绸之路》创作背景及简介
丝绸之路广义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指起源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在古时是不可或缺的中西方交流的交通枢纽,而到了现代,随着时代的变化、科学的发展,它的意义已不止存在于这一条通道,包括我国现在重点的“一带一路”建设也是基于此诞生出来的,因其广泛而深远的重要性,也影响了生活中其他的方方面面,而姜莹女士的《丝绸之路》便是应运而生的这么一部作品:《丝绸之路》是由中国当代青年作曲家,中国交响乐团驻团作曲家姜莹女士所作的一部充满西域风情的民族管弦乐合奏作品,其前身是姜莹女士创作的室内乐作品《丝路》以及《敦煌新语》,作品从曲式方面可大致分为四个大部分(即1-14小节的散板段落、15-84小节的4/4拍的Moderato段落、85至233小节Bpm80逐渐加快的段落以及234-246结尾的presto急板段落),其旋律乐器以曲笛、唢呐、琵琶和板胡为主,在和声方面采用了和声小调、弗里几亚调式以及阿拉伯等富有中东地区风情的调式,西域风情特点鲜明;在配器方面则是使用新笛这一色彩性乐器引入,利用板胡模仿特色乐器西塔尔琴的音色等,西域风情十足,而且作者在此还创新性的使用了新疆手鼓,音色独特的打击乐器使得整部作品更加神似。
三、《丝绸之路》的二度创作
作为一名指挥者,在拿到总谱时就应对其进行研读,并且在相关细节处要做好明显的标记,以便指挥排练演奏时方便查阅浏览。以下段落便是从笔者的视角进行的研读以及相关的画面思考,以便其他同行进行理解:
第1-14小节(即开始的散板引入部分)新笛、唢呐、板胡三段独奏仿佛将我们带入丝绸之路中的大漠,空旷而苍凉;吊镲的滚奏仿佛呼啸的风声循环往复,指挥者在指挥时要注意将三位独奏队员的情绪调动起来,并在关键处(如第4.6.8小节的古筝刮奏与定音鼓以及7-8.10-11.15小节的吊镲滚奏)给予明确的指示。
第15-20小节(速度92)仿佛画面由远而近,在苍凉的大漠中显现出了一行人,他们一深一浅地走着,脚步坚定;由于此段的开头部分进行了速度变化,所以在开始前的速度暗示便极为重要;在进入本部分后,要向队员传递出坚定的意识,拍点明确,重音务必要像谱上标记一样突出演奏,尤其注意古筝的琶音。
第21-40小节,节奏由琵琶主奏的连续方整的八分音符转为中阮主奏的连续切分,仿佛画面一转,从商队的最前方开始,采用近景逐个从人们面前略过,钟琴和碰铃的搭配仿佛驼铃一样,清脆而高远,胡琴声部拍琴筒的声音如同骆驼身上货箱中货物相碰的声音;本段的旋律声部为弹拨声部-中胡声部-弹拨声部,所以主次强弱对比必须明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钟琴与碰铃的配合,必须要清脆但却不致尖锐。
第41-56小节,悠长的笛声仿佛突然平地的一阵风,将绝大多数声音都掩盖了起来,只剩下驼铃的声音还依稀跌跌撞撞的传来;注意在41-48小节处,大提琴的声音应稍弱,体现出风沙中人们的身影若隐若现的感觉,而从49小节开始,旋律转至胡琴声部,队员的演奏需要极强的线性,用以体现人们在沙中寸步难行的感觉。
第57-75小节中,速度记号为piu mosso,意为更快的,Bpm为96,故而指挥者在此应将速度向上增加,用以表现人在愈发汹涌的风沙中坚定不移地前行;此处需要注意第64、68小节的柳琴、扬琴的演奏片段,应有些许的渐强渐弱。
第76-84小节表现了与风沙抗争后的人们已经精疲力竭,在风沙远去之后,竟发现目的地已经近在咫尺,84小节最后两声清脆的蹲杯鼓体现出出人们惊喜内心的开端。在此处值得一提的是,在笔者学习时所观看的国内各位优秀指挥家所指挥的该作品时,虽然在其他片段的阐释各有说法,但是在84小节结尾与之后蹲杯鼓衔接的处理却鲜明的分为了2种:第一种主张将二者连接起来作为同一部分演奏;第二种则主张在84小节的两声过后稍作停顿再进入85小节;笔者在此从个人的二度创作方面来看更加认同第二种主张,因为在人们筋疲力尽之时,即使看见了远处的目的地,也会稍作停顿,或揉眼或呆滞,只有稍作停顿才能更加符合此情景。
第85-93小节,速度从此处变为Bpm80,但是因为蹲杯鼓节奏型的原因(见谱例1),给听众带来的听觉感受则更像是速度160的感觉,
人们打起精神鼓足劲冲向了目的地,准备为度过了这艰难的路程庆祝一番;在此处应注意至87小节扬琴主奏的旋律进入后,蹲杯鼓应稍弱些。
第94-131小节,高音唢呐进入演奏,嘹亮的唢呐与笛声的错落交替仿佛城中的人在迎接商队的到来,吹起唢呐将商队迎入;而后琵琶、柳琴以及铃圈的演奏仿佛将人们带入了迎接商队的宴席之中;此处应注意112小节的piu mosso处应再将速度向上提。
第132-155小节,高音笙主奏旋律,仿佛演奏者与舞者稍歇,主人与商队开始互相攀谈,在欢快的气氛中宴席达到了第一次高潮(此处应注意将空拍以气息的形式给出);而后大家拍起手来,将歇息许久的演奏者再度迎回。
第156-174小节,琵琶在拍击琴板及琴桶的伴奏声中开始演奏,表演再度开始,在逐渐激烈的乐曲中,大家载歌载舞,陷入了狂欢的气氛之中,在后几个小节中,镜头逐渐拉远,来到了室外。
第175-233小节,悠长的唢呐与吊镲相合,仿佛风在远方再度吹来,然而却丝毫无法掩盖室内欢快的气氛,欢快的气氛越来越强,盖过了外面苍凉的风声,而后风声完全被欢乐的气氛盖过,欢快的气氛开始蔓延,越发宏大。
第234-246小节,速度变为全曲最快的presto,Bpm184,整个宴席达到了最后的高潮,觥筹交错之间,全曲结束。
四、作品的相关分析及诠释
在首先,笔者认为《丝绸之路》这一作品的速度类似于唐代大曲散序、中序、破的形式,故而演奏中每段的速度应是每一个大段落加快一些,而非每过一节便加一些速。在指挥排练该作品时,指挥者应提前在在自己的心中将自己置于荒凉的大漠上,并且在排练时就应通过形象的文字表述(如上文第三节所述)让队员能够跟随指挥融入其中,在指挥乐手演奏时,柔和的旋律部分应以线的形式打出,幅度较小,而在较为强烈的部分应打点明确,令乐手整齐一致,如在76小节前几小节应以柔和的线条打法为主,而至第76小节就应转换成较为明确的打法,此处以74-77小节梆笛、柳琴、扬琴、二胡声部为例。(见谱例2)

谱例2
而在14-15、84-85小节这类速度变化极为明显的地方,动作务必要干净利落,提前给出速度暗示,从而保证乐手能够整齐的进入;在处理相似的乐句时最好不要有完全一致的动作,因为相似或完全相同的指示会导致乐手的视觉疲劳以及令其产生不跟随指挥也可以将乐曲演奏好的意识,如124-128与129-132小节就应有较为明显、先强后弱的对比。而在第一节笔者就已提到在不同的指挥者手中,因其二度创作的不同将会导致同一作品的最终呈现方式多种多样,在众多指挥家的演绎中,就笔者所见,有以下几处不同:首先最为鲜明的便是速度的差异,在刘沙先生于中央民族乐团的手中,15-84小节的速度约持于108bpm(原谱要求为92bpm),而在吴强女士于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的手中则达到了118-128bpm,结尾的presto部分二者分别达到了180bpm和200bpm(原谱中为184bpm);而在于乐器方面,前者则是将散板solo中模仿西塔尔琴音色的板胡直接用西塔尔琴替代,西域风情更足。从这些方面我们也不难看出二度创作及其演绎的独特性了。
五、个人感悟
民族交响乐是将我国的民族器乐与乐器创新性的与西方交响乐融合产生的灿烂瑰宝,在国内指挥家的手中,它绽放出了如此绚丽的花朵,其中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形成的二度创作观念及手法功不可没,它与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而在诸多二度创作的同一作品中,笔者最为喜好的便是基于原作的各种标记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二度创作,这并不是说二度创作要咬定前人的经验、完全效仿前人,而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远方眺望;并且,如果完全不按照作者的观点进行所谓的“二度创作”,就笔者所见,这并非二度创作,而是所谓的“改编”之说:二度创作应是将他人的创作或观点延伸,而非将其改向或是完全变形。故而在此我们在对于作品进行二度创作时务必做到量力而行,以作者原意(即谱面文本)为本,而后再对其进行延长,生长成为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这样,演奏者的二度创作才拥有了其独特性。
结 语
作为乐队指挥,对于乐谱的研读不可仅仅只停留在谱面,务必要向更广、更深的范围挖掘,如作品的创作背景、社会环境等,进而将作品的感情以及风格的演绎更加贴合当时的时代特点;如果演绎的作品时代较为久远,还需考虑当时的演奏习惯与乐器差异等。而在指挥对于作品处理演绎中,如果只是为了演奏而演奏,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在这里其实便是个人的二度创作)的话,那指挥于乐队的作用便只是一个节拍器、陪练工具而已,就失去了指挥家存在的应有涵义,就笔者之所见,一个合格的指挥家应在其保证所有乐手演奏整齐的基础之上保证能够以一人之力带动整个乐团的情绪变化,而此处所说的情绪变化包括但不限于感情,声部平衡等,而这些都应囊括于指挥者的二度创作中,而在管弦乐这一范围内,二度创作作为作者与演绎者共同作用于乐手的一种手段,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使得指挥不仅需要遵循原谱上已有的标记,更应站在作者的肩膀上,将其进行更深一步的演绎;当然,对于指挥来说,不同的经历及性格会导致作品演绎上的差别,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差别还会是巨大的(比如说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前5小节在巴伦博依姆手中相较其他知名指挥家就会更加缓慢且沉重),故而指挥的主观能动性在不同人的不同生活阶段中也是不一样的,而这些经历通常也会使得演绎更加有深度,发人深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将传统与创新结合起来,将音乐作品阐释的更加鲜活,引人入胜。■
注释:
① 赵阳.谈器乐表演的二度创作[J].大众文艺,2020,(15):131-132.
② 李洋.浅谈音乐表演的二度创作[J].北方音乐,2020,(0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