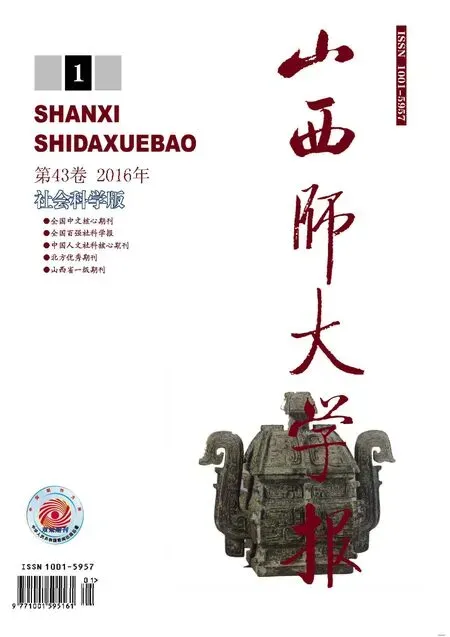晚清西学东渐中的特殊传播者
——以教会报刊中的传教士报人为例
姚 彦 琳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序幕,随之中国近代报刊的先河也被开启。 在华创办教会报刊的传教士不仅是西方宗教的传播者,也是西学的传授者。传播者的主要职责就是利用传播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信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份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1]78。作为传播活动的主体,这些远在异国他乡,以传教为己任的布道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会报刊内容的走向,而信息的选择又与他们所属差会的政治取向及其个人的价值观念、文学素养等因素有关。
一、政治属性决定的办报动机
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传播内容起主导作用的传播者无法摆脱个人身份属性的限制,因为“传播主体总是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去看待他者文化,因此,传播者的观察和结论往往受到某个人和所属种族或文化取向的影响”[2]171。综观整个传教士报人群体,鲜明的政治属性及文化差异是他们区别于华人编辑群体的重要特征。虽然其中有诸如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此种愿将西方科学介绍给中国的文化使者,但仍无法超越传教士群体致力于传教的根本使命。
在这些传教士报人群体中,马礼逊曾任职于东印度公司,郭士立、李提摩太等人也都同本国的殖民当局关系密切,更是受雇为领事、议员等多种职位,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广学会和《万国公报》的主事者“都是和列强在华高级官员常有密切过从并极受赞誉的人”[3]。在报人与殖民者多重身份的制约下,他们很难摆脱所属差会、国家的政治要求,甚至会寻求一定的经济后盾来满足本国商人的经济利益。“媒介所有者的政治倾向决定媒介的政治倾向”[4]157,因此,关于整个报刊的宣传思想、内容选择与编辑,或是关于某些新闻的评论发表,都会尽力去符合其所属差会的意愿和政治集团的利益要求。
熊月之先生将传教士传播西学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两点:首先,西学先进。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都比中国先进,中国人应该乐于接受这些先进的东西。其次,西学有用。通过传播西学,可以在中国人面前树立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获得中国人的好感,为传教打开通道。[5]传教士借助报刊将西方文明呈现在中国人眼前,希望消除他们对西方人尤其是基督教的敌意,从而形成有利于基督教传播的大环境,最终为顺利传教创造条件。简言之,即传学为传教服务,传教则永远是第一位的,力图实现在华利益的最大化,是传教士被赋予的政治使命。
1834年10月,美国基督教差会美部会派遣伯驾来华,他也成为基督教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医生。在其临行前几个月,美部会曾当面对他提出要求:“你如遇机会,可运用你的内外科知识解除人民肉身的痛苦,你也随时可用我们的科学技术帮助他们。但你绝对不要忘记,只有当这些能作为福音的婢女时才可引起你的注视。医生的特性决不能替代或干扰你作为一个传教士的特性,不管作为一个懂得科学的人怎样受到尊敬或是对中国传教有多少好处”[6]28,由此不难看出,传教是传教士永远的第一要务,不仅对伯驾如此,也是对整个传教士群体的共同要求。在传教士出版的众多报刊中,《格致汇编》算是宗教性最弱,科学性最强的刊物,即便如此,其主编傅兰雅也曾表示,中国人与西方人“只有通过共享科学领域的成果,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7]237。
报刊是进行文化传播的优质媒介,报刊媒介又凭借文字承载其传播内容,具体到教会报刊,其本身就是传教士进行“文字布道”的工具,而“文字布道”的前提是可以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对跨海而来,身处异国的传教士来说,“风土人情之不谙,语言文字之隔膜”[8]207,异国的语言交流障碍是他们要攻克的重要难关。早在1807年马礼逊来华时,伦敦布道会就对他的活动做了原则性的指示,让其将学好中文作为首要任务。
中文学习的困难程度早已被世界所公认,英国传教士米怜曾说:“要掌握这门知识(中文),只有经过高度勤奋,专心致志和顽强不懈的努力才能做到。”[9]不可否认,传教士群体中有许多学习能力超强的人,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时就进行了《圣经》的翻译以及《华英字典》的编纂,也一再感慨汉语翻译的困难性,他说:“这项翻译工作是在遥远的中国,使用欧洲极少人懂得的最艰难的文字进行翻译的。如有人要对这部中译本圣经提出批评,请不要忘记这种困难。”[10]154此外,《六合丛谈》的主编,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也是自学成才,仅凭借拉丁文的《汉语札记》和《新约全书》中译本来学习汉语。1846年,他被伦敦布道会派往上海协助墨海书馆工作,同为传教士的面试官理雅各对他的汉语水平非常惊讶。
但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和口头语都比较多,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语言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其中包含着特有的语言规范、语言内涵甚至是特有的表达方式,要真正领会运用并非易事,也绝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做到的。一些传教士虽然能够运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但所编译著并不一定能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语言规范。在大众传播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交流往往具有延迟性,尤其在当时传播技术并不完善的条件下,受众对传播信息的接受程度与反馈情况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报刊是否能准确表达传播者的意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魏源就曾对《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表达过不解之意:该刊“或录古语,或记邻藩,或述新闻,或论天度地球,词义不甚可晓”[11]。梁启超也曾这样评价西人的中文水平:“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12]56可见,语言作为“布道”的工具也是传教士报人首先需要攻克的一道难关。
二、价值取向影响下的传播技巧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传播活动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与其所使用的传播技巧密不可分。具体到传播技巧的使用,又体现在对传播内容的把握与选择上。根据传播学的理论,“选择与受众注意中心和实际需要相关的信息,使信息符合特定媒介和特定传播环境的要求,有利于信息顺利地到达受众”[13]260。从整个19世纪来看,为顺利进行传播,教会报刊所呈现的特色性内容设计主要体现在对下面两种传播技巧的运用。
(一)“孔子加耶稣”。中国是一个非基督教国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儒学占据着统治地位,传教士在异国传教,面对的是异质文化之间固有的阻力,加之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以及中西方政治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传教士的形象在中国人眼中并不友好。如何改变中国人的态度,打破中西方之间的心理隔阂,是传教士思考传播技巧的重点。
早在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就已经懂得调合儒学和基督教的关系,并在皇帝和官员中取得良好的信任。到了19世纪,一些传教士主动对自己进行中国化的包装,如名字的改变:麦都思化名尚德者,郭士立化名爱汉者等等。1930年代,传教士米怜认为应借助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家来进行传教,他说:“面对当地的评述和责难,让中国哲学家们出来讲话,对于那些对我们的主旨尚不能很好理解的人们,可以收到好的效果。”[14]“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在70年代得到深入贯彻,即将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尽力抹杀二者之间的区别。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曾在1869年12月4日至1870年1月8日的《中国教会新报》上连续5期刊载《消变明教论》,试图找到基督教与儒学之间的相通之处,用基督教教义来阐释儒家学说,他认为,“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基督教亦重五伦”,完全可以“证以《圣经》”。他并逐一印证道:儒学将“仁”列为五伦之首,《圣经》中虽然找不到有关“仁”的论述,但“爱即是仁也”;儒学强调“义”,“耶和华以义为喜”;儒学重视“礼”,《圣经》也要求人们处处“以礼相让”;儒学推崇“智”,《圣经》中也有“智慧之赋,贵于珍珠”的说法;儒学讲究“信”,《圣经》中所说的“止于信”就是要将“信”作为最高美德。[15]因此,有学者认为,林乐知“是把‘孔子加耶稣’系统地从理论上加以鼓吹的第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7]268。
此外,在报刊的内容设计等方面也尽量体现出汉化的特点。如尽量出现一些“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彰显中西方友好的词汇,或是大量引用孔子语录。在表达方式上,有些报刊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线装模式,有的则在语言修辞方面使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的套式。
(二)“科学辅教”。关于宗教的定义,著名宗教学者吕大吉先生这样解释:“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16]37,而科学则可以解释为是对客观世界的性质及运动规律的正确反映,二者似乎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怎样处理好宗教与科学之间关系,是传教士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米怜在谈到《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时指出:“其首要目标是宣传基督教;其他方面的内容尽管被置于基督教的从属之下,但也不能忽视。知识和科学是宗教的婢女,而且也会成为美德的辅助者。”[17]72可以看出,利用科学来传播宗教,即“科学辅教”成为教会报刊所采用的另一个策略技巧。
从1833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开始,教会报刊就已不局限于单纯的宣扬基督教,报刊的宗旨与侧重点都有所改变。1853年《遐迩贯珍》创刊时,有关西方科技的文章已大大取代了宗教文章的地位,到1872年的《中西闻见录》、1876年的《格致汇编》,几乎就成为完全不涉及宗教的报刊。《万国公报》在1889年复刊后,也成为“只字不提宗教”的综合性报刊。传教士认为:“中国诚然需要西方学者所能传播的哲学和科学,但它必须从基督教传教士的手里来获得这些哲学和科学的知识。”[18]288在中国变法图强时期,教会报刊还故意迎合中国人渴望西学以及迫切需要救亡图存的心理,如《万国公报》就大量刊载了介绍西学以及西方民主政治的文章,以最大限度地符合中国读者的心理。
“科学辅教”的方针并未始终被奉行,1877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对是否出版非宗教性报刊进行了讨论,结果是出版宗教性报刊获得了教会更多的支持。此后,“科学辅教”的办报方针受到一定影响,也直接导致了《格致汇编》的停刊,《万国公报》所刊载的西学文章也有所减少。
三、多重身份制约下的内容把控
如前文所述,教会报刊内容的大方向及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是同本国政治集团及所属差会的利益和要求相一致的,也是传播技巧在每个时期的具体运用。但报刊具体内容的选择与编写则是由报刊的主编或主笔决定的,在这一点上,传教士报人无疑起着主导性作用。然而,传教士并非是纯粹的西方文化传播使者,他们的主要身份还是基督教文化的代言人,或如前文所提到的报人与殖民者身份的统一体。传教士超越其本身的宗教职能而承担传播西学的任务,在多重身份的制约下,必然会使报刊的内容显得不那么真实、客观。
首先,传教士不具备职业新闻工作者的素质,难以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可靠性。1899年,《万国公报》第121期发表的《大同学》第一章中首次出现了马克思的名字:“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19]由此可明显地看出,报刊中错把马克思说成了英国人。当时的中国社会传播手段还极不完善,国人更是缺少对西方社会的认知,对于报刊中出现的错误信息,受众根本无法证其真伪,间接导致了一些不实信息的再次传播。
其次,传教士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他们并不具备理解和阐释近代科学的文化素质。作为“科学辅教”的手段,教会报刊的内容会随着策略的改变而进行一定的取舍和发挥,这就使报刊内容,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很难做到准确无误。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有一篇讨论万物“引性”和“向性”的文章:“问:万物本来自然有这性,又自会常存之否?答曰:非也。神至上者,原造万物时,即就加赐之以此性,又神之全能常存之于万物之内也。若神一少顷取其全能之手,不承当宇宙,则日必不复发光,天必不复下雨,川必不复流下,地必不复萌芽,四时必不复运,洋海之潮汐必不复来去,人生必不复得其保,又世界必离披,万物必毁乱也。”[20]诸如此类在自然科学等方面渲染上帝神力的文章不在少数。《万国公报》也曾多次刊载文章宣扬上帝的权威,“西国之日益富强者,惟因事事务求真实,日进不已,一变而至于斯也。然其变也,耶稣之福音始也”[21];“耶稣教,荡荡天道,非授自人,乃传自天,巍巍乎充塞宇间,诚系亿万百姓闾关之安危、千百世邦国之兴废”[22],如此等等。
最后,与帝国主义和西方教会的密切关系势必会影响到报道态度的倾向性,特别是在报道一些政治事件时,其所属政治集团的利益需求会被附加其上,以致出现不实的报道。《万国公报》曾刊载过评论鸦片战争的文章:“两国俱皆有过,彼不能尽归罪于此,此亦不能尽归罪于彼也。”认为林则徐对英商利益的侵害是导致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并为殖民者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英主以其越分悖理,强夺国民之货,遂至不得已用兵”[23]。这些报道大多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传播其奴化思想,严重地影响了受众了解事实的真相。此外,对中国的一些改革、变法事件,教会报刊也表现得格外热心。《万国公报》于1897年9月刊载《中国度支考跋》一文倡言:“今敢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不行新法则已,欲求新法,非先假手于西人不为功也。”[24]将西人或是基督教的帮助看作中国变法图强的关键,在每个方面都极力渲染基督教的神力。
综观整个晚清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教会报刊不管是在宗教宣传还是西学传播上都是收效最明显的。传教士群体已很少再被扣以“文化侵略急先锋”的帽子,教会报刊所进行的西学、文化传播得到更多的认可。但传教士报人受限于个人身份、自身水平以及时代条件等种种因素,使教会报刊的内容及效果都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传教士报人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将一种近代的传播媒介引入中国,如学者所言,近代中国人“能够通过这一具有近代意义的传媒去看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25]60。
[1] (美)梅尔文5L5德弗勒,等.大众传播通论[M].颜建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 黄晓钟.传播学关键术语释读[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3] 李明山.广学会编辑策略略论[J].南都书坛,1992,(12).
[4] 徐耀魁.大众传播新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5] 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价值取向[J].社会科学,2010,(3).
[6] 嘉惠霖.博济医院百年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7]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8] 范约翰.清心书院滥觞.载于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会参考资料(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9] 米怜的生活和工作[N].中国丛报,1835- 12,(45).
[10] 马礼逊夫人.马礼逊回忆录[M].顾长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1] 魏源.海国图志5英吉利国[M].上海:上海书局,1895.
[1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 段京肃.传播学基础理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14] 米怜.圣经[N].中国丛报,1835- 11,(44).
[15] 林乐知.消变明教论[N].中国教会新报,1869- 12——1870- 1,(64- 65、67- 69).
[16] 吕大吉.宗教学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7] 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18]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6.
[19] 李提摩太.大同学[N].万国公报,1899- 2,(121).
[20] 论地周日每年转运一轮[N].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6,(20).
[21] 林乐知.论真实为兴国之本[N].万国公报,1896- 8,(91).
[22] 圣道有关国家盛衰论[N].万国公报,1893- 8,(55).
[23] 英东力除鸦片贸易告白[N].万国公报,1876- 1,(370).
[24] 林乐知.中国度支考跋[N].万国公报,1897- 9,(104).
[25] 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